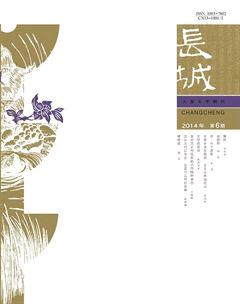你,许个愿吧
毕亮
杨晓琳和王朗把孩子送到老家江西,返回深圳他们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偶尔家里会响起一两声叹息。
又到周末了。
杨晓琳的周末比平时上班更忙,她要参加各种培训班“充电”,家里还有抹桌、拖地、刷马桶、伺候花草等乱七八糟的活儿等着她干。交代丈夫王朗帮把手,他更忙,成天不见人影。杨晓琳盘算歇一歇,脚步又不愿停下,整个人带电陀螺似的转。
礼拜六清早,杨晓琳潦草地吃完三明治,再给客厅的绿萝、文竹、平安树浇水,拎起手袋匆忙赶往培训现场。一路上,她惦记下午的课程安排,谋算提早回家,跟在江西赣州老家的儿子视频聊天。每周六下午五点,是杨晓琳固定的亲子视频时间。亲子活动接近尾声,若是王朗站身旁,杨晓琳就语带怒气跟自己过不去似的低吼,赶紧,赶紧换套大点的房子,把儿子接过来!若王朗不在,她就在心里对自己狂喊,奋斗,拼搏……反正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要换房子,大一点的房子。
步入阔大的培训室,讲座尚未开始,杨晓琳瞥见讲台上方LED显示屏滚动六个醒目的汉字“敲开成功之门”。那些学员三三两两在交谈,和交换名片。杨晓琳寻了个靠后排的位置,坐定,目光扫视一圈,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年龄跟她相仿,多是三十岁出头。她在心里自嘲,成功,这把年纪还来得及么?
上午两堂课下来,杨晓琳收获了一堆名词:执行力、时间管理、情绪管理、空杯心态、资源整合……
中午,杨晓琳在窄街的榕树下徘徊,对考虑的许多事举棋不定。走去就餐,授课老师的箴言仍在她耳畔回响:“这些习惯坚持下来,你就能一步一步从平凡迈向卓越,敲开成功之门!”轻握米白色竹筷,杨晓琳拨弄碗里的农家小炒肉,清点,数量少得可怜。另一张台坐的恰巧是上午参训的学员,一男一女,他们在谈论成功学,聊比尔·盖茨、乔布斯,聊马云、马化腾。
杨晓琳一阵恍惚,她和王朗来深圳十年了。
十年前那个阳光柔和的早晨,他们一人拎行李袋一人拖行李箱,迎着暖风走在罗湖火车站广场。那时的他们似两只雏鸟,带着好奇、渴望、向往,也带着一夜未眠的疲惫,来到味道新鲜的深圳,打算在这座城市扎根。
那对男女喝的冰镇港式奶茶,他们还在畅谈成功,且聊得更为具体,别墅、游艇、豪车,爱马仕服装、手袋。随后他们话锋一转,交流起成功后如何控制贪欲、灭减自我膨胀。
杨晓琳瞄了两眼侃侃而谈的男女,夹起碗里的小炒肉,就着东北米饭嚼食,感到味重,肉咸。她忆起过去的“幼稚”,大概是结婚前两年,她暗自制订“逃跑计划”,计划的一部分是独自去西北远游,栖身戈壁、胡杨林,不上班、不拼搏、不奋斗,放弃一切压身的束缚,不用对任何人、任何事负责,当一个人生的叛逃者。
杨晓琳没来得及实施“逃跑计划”,就结了婚,又意外地生了孩子。她琢磨过她自己为何不逃,大概是牵绊太多、缺乏逃跑的勇气。后来,她干脆连这个事都懒得想,挣扎只会更痛苦,就过多数人认同的生活吧!
嗥叫着从噩梦里醒来,杨晓琳后背的冷汗浸湿棉质睡衣,她摸黑吞下一片阿司匹林,喝了半杯茶色玻璃杯里的凉水。床上她的一侧寂寞地空着,散发着荒凉的气息。
深夜,王朗未归。
杨晓琳猜测王朗还在应酬,在酒局上一杯接一杯给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超市负责采购的经理敬酒。或者在光线黯淡、空气浑浊的娱乐休闲城,陪客户浴足、松骨……除了这些,王朗还能干什么,她不知道。有好几次,半夜,王朗进门就栽倒在地,似轰然坍塌的老墙。他趴伏在冰凉的瓷砖地板上,打完酒嗝,唇齿翕动,念念有词。杨晓琳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潮热的腐气,连拖带拽将眼前那堆油腻的肉体搬运至沙发。怕冷似的,王朗高大的身躯蜷缩成一团,眼窝溢出潮湿的泪水。看上去,王朗似一枚枯萎缩了水的苹果。杨晓琳的心脏似给谁猛踢了两脚,痛得难以名状。她用指尖帮王朗揩净眼泪,指头闹地震似的颤抖、悸动。清早醒来,杨晓琳盯着满脸倦意的王朗看,预备问他为何流泪,想好的措辞滑到喉头,又强吞下去。她忍住没问,体内脏器弥漫着忧伤,不去戳穿那层薄纸片。
窗外传来泥头车喧嚣的笛鸣声,尖厉,刺耳。
杨晓琳哈欠连天地躺回床上,灰色条纹床单尚存余温。她想起那个梦,身体似被施了魔咒,关节僵硬、浑身麻痛,旋即睡意若潮水般消退。在梦里,杨晓琳上司幻变成一只肥硕的黑猫,猫身有几块醒目溃烂的白色皮癣。她则变成一只奔入死胡同无处可逃的幼鼠,任由黑猫伸爪调戏、玩弄,却又不取性命,一切悬而未决。幼鼠退缩墙角,无路可退,埋头哀鸣,鼠灰的身体瑟瑟发抖……杨晓琳想起白天,在办公室格子间,上司跟她沟通工作,他的脏手似有意又似无意地在她脊背摩挲,那张脸笑得轻佻、古怪。她浑身泛起鸡皮疙瘩,找了个借口,携一身冷汗逃离办公室。
钢质防盗门响了。
王朗回来了,他似个沙袋,沉沉地压在床榻。他拿指尖轻捏杨晓琳臂膀,嘀咕说,等这个单签下来,能挣不少,到时我们出去玩一趟,你想想,去哪里?
杨晓琳说,我想换工作。
王朗说,你上班不是挺好吗?待遇不错,福利也好。
杨晓琳说,想换个环境。
王朗说,找好下家了?
杨晓琳说,没。
王朗说,我们得还房贷、车贷,跳槽你可想清楚,要不再考虑考虑。
睁开眼,又闭上,杨晓琳想到银行催款单、信用卡账单、物业管理费等各种名目的缴费单,她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感觉有块巨石压她心脏,令她喘不过气。她想告诉王郎,财务部同事林琳换了套140平米的房子。不等她开口,身旁响起如雷鼾声。
杨晓琳想起噩梦前另一个梦:她一个人孤寂地坐在地铁车厢,地铁载她沿铁轨飞驰,她想下车,地铁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深圳北站、少年宫、市民中心、会展中心,她错过一站又一站,煎熬、焦急、不安。她用头猛撞车门,砰砰响,头顶溢出乌黑的血,可地铁仍然烈风一样前行……
黑暗中,杨晓琳挪动躺床上的身体,情绪一步一步陷入沮丧的深渊,即便王朗口头邀约的旅行,也不能令她脱离苦海高兴起来。现在杨晓琳哪儿都不想去,就想把钱攒着,把孩子从江西赣州老家接来深圳,实实在在过日子。
三年前,杨晓琳和王朗在龙华新区购置一套公寓房,开始了房奴生活。
每天清晨七点,杨晓琳准点出门,坐龙华线地铁上班,傍晚五点半下班,她再挤地铁回家。王朗在一家贸易公司任业务经理,工作需要,他贷款购了台代步小车。有了房子、车子、孩子,他们对生活一时充满无限希望,觉得什么都唾手可得,直到每个月初收到还款账单,目视那一串串数字,他们又感到丧气,盘算熬到何时才是个头。
某个周末,天阴沉沉的,杨晓琳坐梳妆台前照镜子,镜中人瘦骨嶙峋,呈现早衰的迹象。不经意间她发现发丛中藏匿两根白发,仔细择出来,连根拔起。她将白发环绕食指间,走了神,回想大学毕业从江西赴深圳后的生活,没有太多意外,也没有多少惊喜,完全是程式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初入职场时,作为“菜鸟”时常加班加点,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刚适应职场生活,就步入婚龄,开始想着结婚、购房、育子,一刻也停不下来。她的生活轨迹完全偏离了最初设想的轨道,至于最初预想的生活是何等模样,她也是不清不楚。
有一段时间,杨晓琳计划离开深圳,哪怕只是短暂几天。她记得那个出逃的夜晚,巴士在暮色中驶离深圳。那是杨晓琳和王朗唯一一次出门远行。周末两日游,去的是阳朔,费用不贵,可以说便宜。五百块一个人,从深圳体育馆出发,坐一夜巴士,囫囵睡一觉,第二天清晨就抵达目的地。
杨晓琳和王朗十指紧扣,并排舒服地靠在椅背。杨晓琳说,终于要离开深圳了,再呆下去,我人会发霉!
王朗说,别高兴得太早,也就两天。
杨晓琳说,两天就两天吧!
大约想到离开时间短暂,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们聊天的兴趣一下没了,闭了眼,却没睡。等再睁开眼时,杨晓琳透过车窗,瞥见远处黑暗中闪烁零星的灯火。她想起早前搭乘夜火车南下深圳那些往事,温暖又惆怅。她捏了两下身边王朗的手掌心,他睡了。她感觉后背痒,弓身蹭椅背。她又闭上眼,再一睁开,天已微亮。
目的地完全不是杨晓琳期待的样子,可说落差巨大。阳朔那一条传说中的酒吧街,艳俗不堪。杨晓琳逛到一半,兴致全无,拖着王朗回住地。歇脚地是个农家旅馆,进屋杨晓琳闻到一股霉味,她不悦地打开滑道窗通风,闷坐床头。王朗忙前忙后,将背包内的洗面奶、沙宣洗发水腾出,里里外外收拾,装模作样拍打被褥、床单,除尘。
杨晓琳说,赶不走,还是有股霉味。
王朗说,五百块钱玩两天,将就点吧!
杨晓琳说,本来是打算来阳朔洗脱身上的霉气,倒好,还要带一身霉气重返深圳。
王朗不搭腔,伸出双手,从背后环抱杨晓琳,箍紧。他说,我先洗澡,然后……他干笑了两声,松开杨晓琳。
轮流洗浴,花了老长时间,他们像是要举行某种隆重的仪式,沐浴更衣。两人裸身相拥在旧得发灰的床单上。王朗似条饿狗,想干点什么,谄媚地笑,献殷勤。杨晓琳警惕地推他,盯着王朗看。她说,当心点,我可不想现在要孩子!
赤脚跳下床,王朗从背包里寻找事前备好的杰士邦安全套,返回硬邦邦的床榻。性急,他试图扯开安全套包装塑料纸,用力过猛,套子落入枕头与床头板间的缝隙。他伸手够进去摸,摸到套子,但不是他们的,是一枚以前旅客使用过的安全套。
王朗目视杨晓琳沉默着下床,利索地穿好暗紫色内衣,再套上米奇睡衣,赌气似的抓起一瓶娃哈哈矿泉水,一口气喝掉大半瓶。
时间凝固了。
杨晓琳的声音传过来,赶紧去洗手!
王朗好不容易反应过来,将二手安全套扔进洗手间下水道。他说,真他妈煞风景!又说,杨晓琳,后悔了吧你!
杨晓琳说,很多事我现在都后悔!
王朗说,跟我一起,让你吃亏了、吃苦了。
杨晓琳说,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差点吵起来,幸好王朗忍了脾气、示了弱。王朗说,我是一堆牛粪,我愿意你这朵鲜花插上来,愿意你一辈子插在我这堆牛粪上!
杨晓琳说,真不该出来,若是在深圳,我周末加个班,那份珠宝文案就能赶出来,现在我就想回去、回深圳,去公司加班。
王朗说,我们真是犯贱,舍得花钱,去丽江肯定会好一点。
杨晓琳说,别说了,只要跟你在一起,在哪里都没关系、都无所谓!
他们拥抱在一起,脸贴脸,两人似饿坏了的孩子,肆无忌惮、无声无息地哭泣。他们眼泪水交织在一起,哭完,彼此抹干泪水,又呵呵大笑,只有他们清楚笑声中有多少无奈和酸楚。
孩子的到来完全是个意外。
杨晓琳和王朗结婚五年,迟迟没生孩子,两边父母急了,问他们是不是有毛病,若有的话赶紧治,治好了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反正迟早要生。他们意见一致,等条件成熟再添孩子。两边父母问,什么叫条件成熟?他们说,生活能自如一点、压力再小一点。王朗父母说,生个孩子能碍你们多大事,大不了生了搁老家养。他们跟老人无法沟通,只好口头依了,好,尽快生。
对父母,他们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做爱时他们小心翼翼,生怕有半点闪失。卧床头,两人对话通常如下:
“套子呢?”杨晓琳说。
“戴了。”王朗说。
“检查好了,别有针孔?”杨晓琳说。
“嗯,好了。”王朗说。
“那你来吧!”杨晓琳说。
“好,来了!”王朗说。
……
一再小心,结果杨晓琳还是怀上了。杨晓琳眼瞅验孕棒,表情看不出是喜悦还是沮丧。她掐指算,转眼就快三十岁,既然有了,那就生吧。又想,正是职场奋斗期,去做个人流,迟两年再生,也是可以的。她跟王朗商量来商量去,纠结了一礼拜,还是讨论不出结果。
他们决定抓阄。
王朗郑重地制作两个纸坨,一个写“生”,一个写“不生”。杨晓琳抖手抓了三次,一次“生”,两次“不生”。抓完她长叹一口气,两只手互搓手心的汗。她说,天注定,生不了!她眼窝湿了,惆怅地望王朗。又说,到底怎么办?
王朗将皮球踢回来,双手捂脸。他说,你拿主意,你看着办吧!
杨晓琳舍不得子宫里孕育的生命,指尖直抠眉毛。她说,生吧,反正有过一次不信命。
王朗说,不信命?
杨晓琳说,跟你在一起,就是不信命,我相信我们能把日子过得更好!
眼泪水无声地流出来,王朗哽咽说,晓琳,实话……实话告诉你,我心里特别想要这个孩子!
做完决定,他们协商好生男孩由王朗取名字,生女孩由杨晓琳取名字,再分头打电话给老家母亲。他们听到那边老人幸福的哽咽声。
夏天就要过去。
过完暑假,国庆节不到,杨晓琳就盼着过春节。九月到春节,当中隔一大截日子,杨晓琳想直接跨过去,春节可以回家,回家就能见到儿子。
她想儿子了。
儿子在深圳出生,不到一岁,为集中精力工作,努力奔几年,换个大点的房子,杨晓琳和王朗合计,万般不舍把儿子送回江西老家,由爷爷、奶奶带。每次杨晓琳跟儿子视频,看着儿子在电脑显示器里欢跳,转眼两年过去,孩子都快三岁。
视频通话时,杨晓琳跟孩子也就唠叨那么两句旧话。
杨晓琳说,想不想爸爸、妈妈?
儿子说,想!
杨晓琳说,爸爸妈妈也想你!
他们的谈话在这里基本结束,接着就是杨晓琳含泪看儿子摇晃手中的玩具,过去是拨浪鼓,现在是塑料手枪。
这次她们母子完成固定模式的对话,儿子冷不丁来了一句:“妈妈,你什么时候接我去深圳?”杨晓琳震呆了,好半天才回过神,她说,快,快了!杨晓琳的话说得没一点底气。为何没底气?他们夫妻虽然买了房,但只是个50多平米的公寓房,老人和孩子一来,显小,拥挤。
杨晓琳回味孩子的话,陷入沉思,神情也由愉快变得沮丧。王朗说,走吧,再晚吃饭就得排队了!杨晓琳想起孩子似乎又长高了,手臂也长长了,衣袖短了一截。她说,不去了,就在家对付吃,能省一点是一点。
这一天是杨晓琳三十二岁生日,本来她心情不错,答应王朗去吃顿西餐。他们已经很久没好好过二人世界。
孩子稚嫩的声音讲出“妈妈,你什么时候接我去深圳”将庆祝生日的好气氛给搅坏了。厨房传来锅碗瓢盆的碰撞声,王朗避开杨晓琳这座活火山,躲厨房忙活。杨晓琳像是想起某件事,处在后悔、懊恼中,她坐在梳妆台前拨弄发丛,看有没有新长出来的白发,发现一根,她愤怒地将它拔出,放手心用力搓,揉成一团,龇牙狠狠地将一团发丝扔进垃圾桶。
一碗热气腾腾的长寿面摆在杨晓琳面前。王朗说,吃了吧,手艺不怎么样,将就着吃!
杨晓琳干脆地说,不吃,走,我们去万象城,别开车,晚上咱俩喝点酒,你陪我!
杨晓琳和王朗坐上地铁,车厢挤满比他们年轻的男女,相互依偎,或是手牵手。杨晓琳漫不经心地盯着那些人看,有喜悦的面孔,有不安的面孔,有冷漠的面孔,……杨晓琳和王朗站着,保持约一尺远的距离,似两个不相干的陌生人。他们似乎同时发现自己老了,表情尴尬,但彼此心照不宣。
地铁把他们送到万象城,他们打算吃意大利面、披萨。坐在餐厅,他们没一点说话的欲望,跟眼前的食物有仇似的,吃得狰狞、凶狠。
接下来他们去了东门本色酒吧。
坐在靠墙的幽暗角落,他们摇骰盅猜色子,渴了似的喝红酒。杨晓琳说,好久没醉过了,现在连喝醉酒我都不敢,怕第二天起不了床,上班迟到!又说,自从来深圳,我身上所有的勇气都在一天一天丧失,总是患得患失,连换个工作也瞻前顾后。
王朗说,换就换吧,有我!
杨晓琳说,那天晚上你可不是这么讲。
王朗说,我忘了,哪天?
杨晓琳说,那晚流眼泪,到底怎么了你?
王朗默不作声,将一杯酒喝见底。他不敢抬头看对方,低眉,夹紧膀子。他说,有时候我会莫名地感到恐惧,一想到明天,我一点底都没有。我害怕其他同事业绩做得比我好,我害怕掉队,害怕失去,也害怕得不到、害怕得到的比别人少!
酒吧的客人逐渐多起来,杨晓琳望着那些面孔模糊站在舞台上蹦迪的年轻男女,多像十年前初闯深圳的自己,充满激情、活力和改变世界的愿望。她想起公司那些洒脱的90后,想去西藏就去西藏,想去尼泊尔就去尼泊尔。她呢,从农村出来,靠不了父母,只能靠自己,花一点钱都得精打细算,一项一项开支列得清清白白。她想起离家前夜,母亲从一钵炖鸡里夹出鸡爪、鸡翅,对她说,出去打工,做人要脚踏实地,祝你展翅高飞,做出点样子。她眼窝潮了,悲伤地说,王朗,喝完这杯,我们走,我想去罗湖火车站逛一逛、走一走。
他们坐地铁抵达罗湖火车站。
火车站广场携带行李的旅客来来往往,那些疲惫的面孔大概是准备离开深圳的旅客,那些带着好奇和向往的面孔大约是初来乍到者。杨晓琳、王朗并肩走走停停,然后在花坛边安静地坐下,彼此沉默,各怀各的心事,各想各的心事。
远处传来轰隆一声巨响,可能是哪个造地铁的路段正实施爆破,或是别的,发生意外事故。他们从沉思中醒来。瞥手表,王朗伸手握住杨晓琳冰凉的右手。他说,我们得走了,赶最后一班地铁。
杨晓琳心事重重地站起身,扬手拍打裤腿上的竹节爬虫。她说,走吧,回家!
他们从地铁罗宝线转至龙华线。
白天形色匆匆、忙碌的人们一齐消失了。杨晓琳和王朗坐的那一截车厢,只有他俩。空荡荡的车厢显得阒寂、冷清。他们相互依偎,杨晓琳有好多话想对王朗倾诉,但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她说了那些能说的,其中有“逃跑计划”。她一个人滔滔不绝,像是要把一辈子要讲的话全部讲完。
王朗说,晓琳,曾经我也暗自想过当一名隐士,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但我没敢跟你提,怕你误解,认为我是个不顾及家庭、不负责任的人。又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们来深圳十年了,你都三十二岁了,祝你生日快乐!
杨晓琳嘴里突然蹦出一句,我们,还来得及吧!
王朗扬手比划,画了一个圆形,是生日蛋糕的形状。他说,你,许个愿吧!
杨晓琳说,过去我以为自己是缺乏逃跑的勇气,才不走,其实要在深圳这座城市好好活着,认认真真地活下去,需要更大的勇气。她配合地努嘴,摆出吹蜡烛的动作。她说,你也许个愿吧,我们一起!
王朗注视双手合十的杨晓琳,她郑重地闭眼,满脸的虔诚,唇间翕动,嘴里念叨着、嘀咕着。那个瞬间,杨晓琳希望他们搭乘的地铁永远不要停下来,就像梦中那一列飞驰的地铁,行驶在黑夜里、行驶在永恒中。
责任编辑 王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