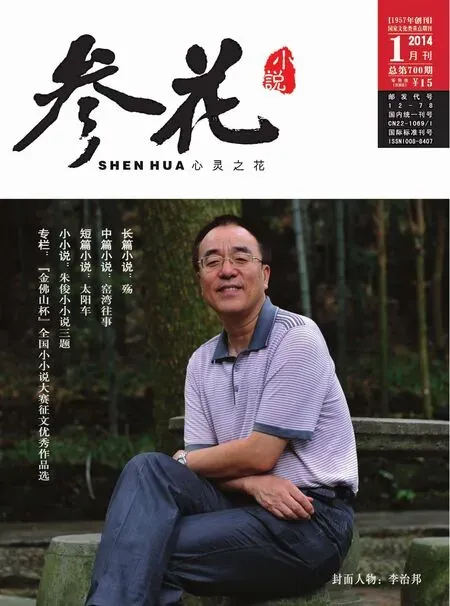田埂边上的老奶奶
◎李占海
田埂边上的老奶奶
◎李占海
那时,我正在镇上读初中,小镇离家近。从镇上到家,有一条由砂子铺成的路,虽比不上镇上的街,倒也算得上平坦。但为了节省时间,人们不惜从砂路旁的田埂上经过。
这条田埂长约千米,细细的,又弯弯曲曲。经过这里的人,除了早晚往返于学校的学生,还有走集的路人,使原本应该绿草繁茂的田埂,俨然形成一条土白色小路。田埂旁,是条用于灌溉农田的水渠,里面的水清澈见底,像是婴儿的眼那样,一尘不染。如果低下身,认真地观察,就可以看见水底白洁的小砂砾在水流作用下缓缓浮动,不像镇上街道边排水渠里沉寂的污水那样,发出刺鼻的臭味。水渠里的水,在田埂边形成了一条“天然”小溪,它缓缓地流淌,时而在拐弯处发出哗啦啦的流动之声,碰击之音。每到春天,水渠两边会长出两道绿带,看起来一派蓊蓊郁郁的景象,水中肆意飘摆的绿草,像是劲风中飘荡的旗帜一样,和清水中碧绿色的苔藓,在透明清凉的水中逍遥地飘荡。
上初一的一个星期五,我得了重感冒。因为次日是周末,学校即将放假,所以强忍着重感冒发作时带来的种种痛苦症状,度日如年般的在教室里苦苦坚持了一个上午。感冒带给我的疼痛,却丝毫未让我变得轻松,我的头脑里似乎都是被刺痛了的神经,一阵阵从大脑涌往全身,并发出剧烈的痛觉。鼻腔里充满了如珠如流般的涕液,像九千落瀑一样,一大把一大把地流淌在试图遮蔽的手中。因为实在难忍,我向班主任请假。班主任见我面目发黄惨白,批准我的请假。我飞快地走到我的书桌前,高兴地从书桌内一把撕出书包上的背带,然后拿起它,斜着头,便套在了颈上,把二十多斤重的书包摔在后背上,然后匆匆忙忙地朝教室的后门阔步走去。带着喜悦的心情,一跨步,便踏出了教室的门槛。想到马上就可以到家了,我的心里异常兴奋,但肩上的书包随着步伐,变得越来越沉重。夏季烈日炎炎,我的额头上、脖颈上、胳膊上……都沾满了湿漉漉的汗水。对于十三岁刚上初中的孩子来说,肩上书包的重量实在太过沉重,双肩上的背带,快要捋进皮肉里似的。我走在看不见尽头的田埂小路上,倍受身体的痛苦与煎熬。终于扑通一响,跌倒在田埂边上的一棵树下,躺在清凉的绿荫下和软绵绵的绿草上。趁着无与伦比的凉爽和舒畅,随着迎面而来的柔风,我缓缓闭上了眼。
当我沉睡好几个小时的时候,隐隐约约地听到亲切、熟悉的叫喊声,这声音像是我过世的奶奶。我立马雀跃起身,望着她。只见她右手拄着拐杖,左袖上打有一块显眼的浅色补丁,她身着一件黑色上衣,两只袖子上,沾满了黄色泥巴,一副矮小的身材,瘦若干柴。我抬头看到她灰暗的脸上,已经纹迹斑斑了,眼眶显得很深,一双大大的眼睛,却显得精神饱满,在我看来,她少说也有七十多岁了。她的头发似乎都变白了,如果不接近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她的头上,还长有几根黑发。她伸出粗糙得快要裂口的双手,靠近我,然后把粗糙的手放在我额头上抚摸,没等我说话,她诧异似的对我说道,“你这尕娃,怎么这么烧啊,一定是因为这地阴凉,你着凉了!”她一手搀扶着我,一手拄着拐
杖,“起来,跟我去我们家,前些日子,我这把老骨头闹毛病,去西关诊所买了些药,现在还有剩。”她看到我能平稳地走路,便一把从我的肩上取下沉重的背包,因为她个子矮,所以是踮起脚的,她吃力地扛在自己肩上,身体稍微一颤,像是快要倾倒。我急忙抢过手:“奶奶,还是我背吧。”她朝着我慈祥地笑了笑,伸出左手,牵住我的右手。此刻,我感觉到她的手,像是我奶奶的一样,厚实而让人倍感踏实。在和她缓步行走的时候,我发现这块辽阔的耕田里,已经长满了散发着芳香味的黄色油菜花,摇晃不定、波澜起伏的碧绿色麦浪。我们闻着从田间传来的麦香味和油菜花味,看着眼前由绿黄两种颜色交织而成的美好风景,一步步沿着田埂,走出了这块耕田。
走出耕田,便是那条砂路。只见路旁两块荒芜的草地,长满了繁茂的野草,几尺高的五颜六色的野花,草地上摆放着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老奶奶指着路边,说:“我们暂且去这儿休息一下吧!我走不动了。”我朝她点点头,她慈祥的脸上,露出了阳光般的微笑。
我走到一块石头旁将要坐下,她急忙拉住我。我的力气比她大,几乎把她给拉倒,她吃力地站稳,对我说,“孩子,这石头晒得太烫,坐了容易生痔疮,你还是坐旁边的草地上吧!” 我点了点头,她指着几百米远处的村庄,说:“那儿,就是我的家了,很快就要到了。”我问她:“奶奶,那不是伯什村吗?”她黯淡的脸上,又露出一丝慈祥的微笑,口中的牙齿几乎所剩无几:“是啊!走吧!孩子。”
到了伯什村,我看到一座座破旧的民房,和一堵堵断垣残壁的土墙。对于我来说,这儿不算陌生,我曾来过这里拜访同学。从这个地方往南走,也可以到我们家。老奶奶终于停下脚步,指着村口的一户人家,说,“这就是我们家。” 我看到由木头和土墙垒成的平房,已经破旧不堪,木头是柳木,变了形,被虫蛀得直掉白粉。屋檐上长满了狗头草、蒲公英,屋檐严重下垂,变成波浪形。栋梁之上,有几道黑色痕迹,像是陈年旧水留下的。
我跟着她走进了房间,看到房间里干净整齐,老奶奶拿出一只干净的碗,摆放在炕桌上,然后转身拿起一个陈旧的桃红色暖瓶。朝放在桌面上的碗中倒水,边朝着我说:“喝一口开水吧!你的嘴皮都快裂了,我听邻居家的大学生说,感冒了应该多喝水。”她朝我笑了笑,走到面柜前,揭开长方形的柜盖,从中拿出几个发黑的小馒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摆放在瓷碟里,“虽然是红面做的,也合我们老人家的胃口,你凑合着先吃几个,在田头里睡那么久,你肚子一定饿了。”我示意地点了点头,拿起一个小馒头,咬了一口,心想,这年头怎么还有人吃这个,红面是旧时代穷人填肚子用的。现在这么好的年代,每家每户都有耕地,即使收成不好,也有政府救济,怎么还会有人吃这个呢!正当此时,老奶奶说:“老家只有我一人,政府救济发下来的白面,我吃着可惜,就留给我儿子。”我问她:“您还有儿子吗?”“有,他在附近的镇上做生意,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了。” 怕惹她难过,我不再问及她儿子的事了。她出了房门,没过一会,把几片止痛片递到我的手上,对我说:“大学生还说,吃了馒头,就可以吃药。”
在她家待了一会,天已渐黑,天际边,悬挂着一片通红的彩霞,像老奶奶脸上的高原红一样,美丽而又温暖。我向老奶奶辞了行,就回了家。
我是住宿生,每一个周五都要回家一趟,每次步行经过田埂小渠边那片树荫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停下脚步,然后,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老奶奶亲切的微笑。我的心里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再去老奶奶家坐上一会,再亲热地叫她几声奶奶。之后三年,在别的镇上上高中,不得空,所以这个心愿一直没能实现。
直到大二的暑假,我再去拜访同学时,才发现老奶奶家的房子不见了,只看到院子里种上了油菜。我向同学打听情况,他说,老奶奶入土已经有好几年了,就埋在院子里的墙角下。看着一片黄色油菜花海,我闻到从油菜花里散发而来的温馨味,使我想起田埂边上的油菜花和麦香味,我的眼泪顿时湿润了。
同学带我从坍塌的院墙处跨进院子里,只见一堆长满杂草的小土丘位于墙角下。我心想,这一定是老奶奶的墓堆吧!我深叹一口气:“物是人非,短短五年时间,多好的奶奶!好可惜啊!”同学随后也叹了一口气,说:“唉,这样算是比较好了,如果是活着,那才叫委屈,才叫可惜呢!她儿子不待见她,不肯养她,才把她抛弃在这样的旧房子里,她的衣食住行,几乎都靠政府救济。她儿子抛弃她的这件事,我们全村人都知道,但老奶奶却似乎什么都不懂,她只相信有一天,儿子一定会来看她。她儿子别说好好赡养她,孝顺她,连老奶奶去世,他都不愿回来,都是邻居们帮忙,才办完丧事。”停了良久,他继续对我说,“有一天,一个来我家化缘的道士跟我妈说,老奶奶去世后,被老天爷封为娘娘山的菩萨了。”
我听着同学的话,眼角顿时变得更加湿润了,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看着眼前荒芜的坟冢上,已经长出了半米高的杂草。按照我们那儿老人的说法,如果坟冢上长满了杂草,那么坟墓里的人就已经投胎转世了。我想,老奶奶一定如那个道士所说,被老天爷封为娘娘山上的菩萨了吧!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