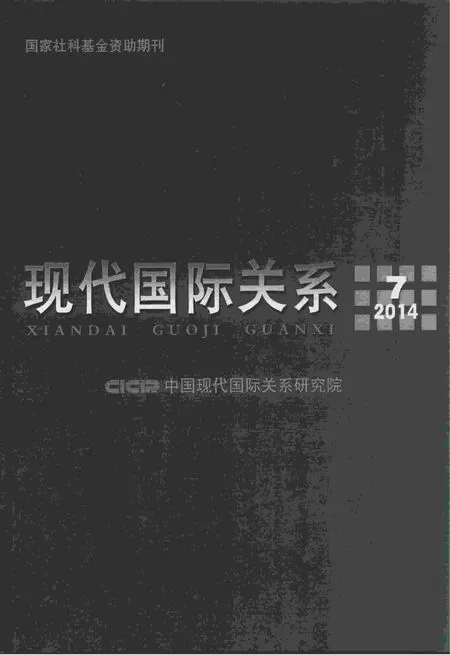国际体系仍然处于多极化进程中
吴志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国际体系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以大国为主要代表的各种国际行为体彼此互动和联系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整体框架,因此,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相互依赖日益增强、大国关系更加复杂的当今时代,观察和分析国际体系的变化、特征与形态,应该不为一国一域所宥、不为一时一事所扰,必须保持理性冷静和战略定力,立足于较长时段的国际全局、整体、主流和大势,综合考察国际力量对比、国际制度安排、大国关系变化和主要国家战略意愿等因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体系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深刻变化,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导致冷战体系的终结,由此也引发全球范围内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对体系大变革及新体系建构的持续探讨。本世纪以来,新兴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而既往一些西方大国实力相对下降,其国际地位相对弱化。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上述两类国家力量消长态势凸显。一些学者认为,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传统西方大国的经济发展遭受严重冲击,实力地位受到削弱,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了大松动;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的连续剧变加速了中东北非地区格局的深度调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中日领土争端、南中国海的岛屿争议等引发亚太地区局势紧张,这些都对传统国际格局构成巨大冲击,国际体系正朝着有利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也有一些人看重国际体系演变的短期态势、局部变化和即时现象,缺乏长时段历史观察和战略分析,突出和拔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作用,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变化表现出“对我有利”的理想化、乐观化判断,认为多极世界已经成为现实,中国已经成为其中一极。从总体发展趋势看,这种判断确有道理,但从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客观变化看,随着两极体系崩溃和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国际体系确实出现了某些阶段性变化和转型态势,在经济和金融等低政治领域的变化更为明显。然而,国际体系整体架构和政治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实质性变动并未发生。目前,国际体系的表象和形态既非单极也非多极,而是整体上处于向多极化转型的进程之中,新的多极体系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渐进、复杂的历史过程。
首先,国际力量对比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全球金融危机确实加速了原本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格局调整,使得全球力量与权势对比出现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根据IMF报告,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几乎全部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金砖五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10%提高至2008年的18%,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则提高到25.7%。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在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低迷的状况下,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经济降速、增长乏力和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就连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开始趋缓。发达国家在经济、产业、科技、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并没有全面丧失优势,特别是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是其他国家短时期内难以超越的。由于当今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着深度的相互依存性,发展中国家甚至更加依赖发达国家,新兴大国短期内难以扭转国际体系由守成大国主导、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基本面。因此,国际力量对比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变化的大趋势虽然是确定的,但是变化速度和步伐可能是缓慢起伏的。
其次,国际制度整体架构特别是国际政治安全架构的根本变革步履维艰。八国集团曾是发达国家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经济和金融制度也操控在美欧手中。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开始出现调整,G20很快成为讨论国际经济问题的主要平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在金融危机中运转不灵、暴露出根本缺陷。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投票权也开始变化。在G20匹兹堡峰会上,各国做出改革世界银行和IMF份额与投票权的承诺。IMF的改革方案2010年获得通过,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欧洲国家让出2个执行董事会席位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份额从3.72%升至6.39%、成为第三大股东国。在世界银行改革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中国投票权则从2.77%提高到4.42%,成为第三大股东。但是,国际制度安排的调整既有连续性,也有滞后性,不是国际力量对比的每一次变化都必然能改变制度安排。尽管金融危机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权势分配格局正在发生重要调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在增大,但其话语力仍然不够,其国际制度设计、提供和实现的能力仍然有限,其在国际政治议程中的权力和能力有待提升,继续争取和扩大自身权益的任务仍很艰巨。而且,国际经济制度的变化只是国际体系变化的基础和表象,国际政治安全制度的变化才是实质和关键,而这一领域制度变革的阻力更大,变化进程更为艰难和缓慢。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安全制度安排并没有太多变化,比如联合国的架构和作用依然故旧。
再次,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总体上依然维持良性竞合关系。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互动和竞合关系构成全球大国关系重组的主线,大国关系的分化组合则凸显出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复杂性。在国际力量对比调整加速的背景下,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开始改变国际关系由西方守成大国主导的局面。面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既存在诸多的利益汇合点,需要相互借重、谋求合作,又无处不在竞争,双方对国际政治主导权和利益分配格局的现状都不满意,相互矛盾和斗争也体现在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治理、网络安全规范、核安全准则等诸多领域,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围绕话语权和主导权展开竞争。在利益交织、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条件下,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组合也呈现出比以往更加复杂的情势。守成大国内部在保持基本合作的同时,分歧频现,美国在西方阵营内部的盟主地位和主导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意愿和趋势则不断强化,其在贸易谈判、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等议题上结成了各种不同的集团与合作伙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竞合相间,维持良性发展,还没有出现冲击国际体系框架的严重冲突与矛盾。
最后,主要国家改变国际体系现状的共识性战略意愿不明显。国际体系的变革不仅有赖于国际实力对比变化和大国关系变动,而且与世界主要国家推动体系变革的战略意愿直接相关。守成大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和受益者,它们均极力维护既有国际体系,没有主动变革的意愿和积极性。伴随综合国力的壮大和既有国际体系公正性不足的凸显,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势必要求对国际体系进行适度调整,从而诱发国际体系变革。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与交往。中国虽不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积极维护者,但总体上仍然重视和强调对现有体系的参与,在参与中扩大有所作为甚至大有所为的战略机遇和战略空间,谋求国际权力分配格局的渐进调整与改革,争取国际体系的变化更多地反映中国愿望、体现中国利益、吸纳中国话语。近年来,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努力成为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并在积极参与中促进国际体系的渐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