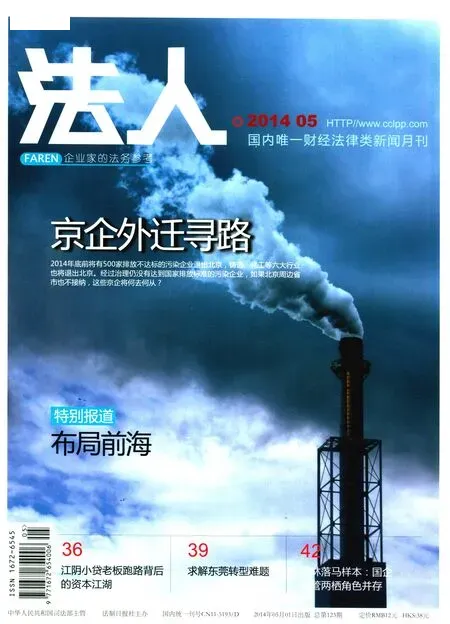专访日本著名建筑师、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坂本一成
河西:你眼中的筱原一男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
坂本一成:我是1965年进入筱原一男研究室的,那年我还在读大学四年级。在东京工业大学,研究室是老师指导学生的教学制度,现在中国很多大学也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我在四年级进了筱原一男研究室之后,在研究室待了六年。东京工业大学有三位非常著名的建筑专业老师,除了筱原一男,还有谷口吉郎和清家清,最后我选择了筱原一男老师。在这六年中,我跟随老师研究建筑。硕士毕业之后,我离开了东京工业大学,到武藏野美术大学建筑学任专职讲师。20世纪80年代初,老师希望我回到东京工业大学,我就以副教授的身份回到母校继续任教,直到2009年退休。在这段时间中,我和老师也有共同教学的经历。也许我很难表达我和老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但在我看来,筱原一男老师是我自己所知道的,整个日本(也许可以说是整个世界),表达精神性最为强烈的一位建筑师。也许别的建筑师也能用艺术性的手法来设计建筑,但是筱原一男却与众不同。他艺术性的表现,或者说精神性的构筑,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筱原一男认为,对于建筑来说空间是重要的,在建筑的空间当中有精神性的内容。象征的世界怎么去表现它,在消费社会中,已经被我们遗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吧?我们需要重新把它找回来,在空间当中获得某种崇高感。
河西:筱原一男非常注意人与都市、建筑的关系,住宅成为他抵抗都市公共空间的工具,你的“非日常的日常性”是否也是在筱原一男基础上提出的建筑理念?
坂本一成: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筑的空间是和日常性相关的,但是除了日常性之外,建筑空间是不是还有非日常性的内容在里面?如何将日常的建筑空间变得不那么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是我在老师的基础上思考的问题。
在所有建筑类型中,住宅是能将空间形式表现得最为纯粹的一种方式。我们通常会认为住宅是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服务的,正是因为这种司空见惯的习惯,让我们把住宅变得简单,恰恰是这种简单忽略了,在小规模的空间构成当中,它能表现出复杂的意义。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思考,所以筱原一男希望通过住宅这种建筑样式,能够表达最纯粹的人类复杂概念和意义。
河西:1969年,你完成了你的处女作“散田的家”,在这个住宅项目中,有一根让人印象深刻的柱子,这让我想到筱原一男的“白之家”里那根抛了光的杉木圆柱,这样的手法是受到老师的启发吗?
坂本一成:“散田之家”是当年我在筱原一男研究室刚开始学习时做的第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当中有很多筱原一男的影响。“白之家”是筱原一男早期作品当中的代表作,在“白之家”诞生之后没有几年,我完成了“散田之家”,尽管早期我这个作品受到了他非常大的影响,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有很多共通点,但是从我的第一个作品开始,我已经有和老师不一样的对于空间的理解了。
从平面图来看,两者共通的部分比较清晰,首先是正方形的平面;其次,在正方形平面中间都有一根独立的柱子。还有,这个平面具有两分性,大空间当中有小箱体的植入,也就是盒中盒的方式,这两个手法也是有共通性的。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筱原一男的两分性表现得非常纯粹,但是“散田之家”在两分性的同时又有某些连续性、暧昧性,这和筱原一男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
其实从我第一个作品当中的确能看到老师对我的影响,以及我是如何吸收、同时又拒绝这种影响的。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在建成44年之后,我进行了重新的扩建,这又拉大了我和老师之间的距离。
河西:“筱原学派”和一般的学派不同,一般的学派,学生和老师的风格总是比较接近;可是“筱原学派”,学生却在背离老师,走属于他们的道路,这种差别是怎么造成的?
坂本一成:筱原一男先生有非常强烈的意志和非常自信的表现,特别追求建筑的精神性和艺术性,表达建筑的一种力量感,他和社会处于一种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之中。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建筑和社会能更加融合、更加连续,以这样的状态走自己的建筑发展之路,我们生活的社会已经和筱原一男活跃的时代不同了,今天这个时代并没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对立,社会更加融合,社会的变化提示我们,建筑也应该有所转变。在今天作为建筑师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什么是社会性,在这种社会性当中建筑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个人化存在。
坂本一成:1943年生于东京,1966年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师从筱原一男。1971年在武藏野美术大学建筑学任专职讲师,1977年晋升为副教授,1983年至今任教于东京工业大学,身为教授并开设自己的事务所——坂本研究室。他是日本当代在建筑设计、建筑教育与学术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建筑师。1990年凭借HOUSE F获得日本建筑学会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