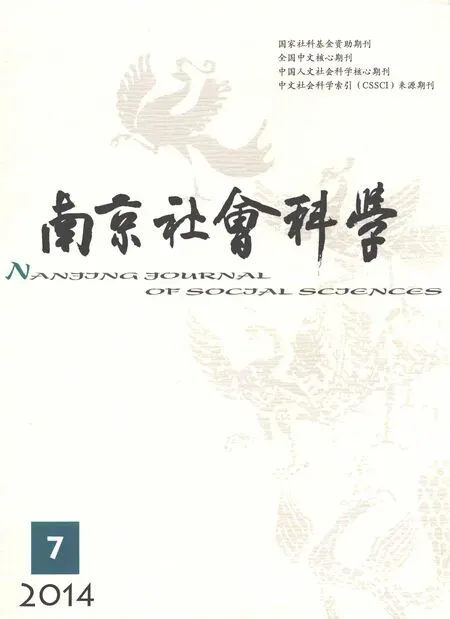在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城市景观*
童 强
在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城市景观*
童 强
(学术主持:南京大学周宪教授)
视觉文化不是视觉加文化,而是文化由外到内的高度视觉化。在人的认知性感官中,视觉无疑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所以,进入视觉文化研究,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便彰显出来,那就是视觉如何塑造我们的社会认知和自我意识。这就是晚近以来视觉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视觉性。具体说来,视觉性可以转化为两个命题:视觉的社会建构与社会的视觉建构。
刊载于此的这组笔谈,集中于视觉性问题的研讨。《在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城市景观》从“店招”这一典型城市形象入手,通过这一视觉符号的解析,对城市的视觉印象和视觉构成作了类型学的考察,进而提出城市公共视觉建构需要注意的问题。《从民间信仰仪式到视觉化民俗仪式艺术》立足于民俗学研究视野,基于民间信仰仪式的认知论转型,讨论了现代仪式向视觉公共性转变中的诸特征及其问题。《论沃尔海姆“看进”观的视觉注意双重性》则从当代视觉再现研究的视野出发,通过评述分析美学家沃尔海姆的视觉注意二重性的观点,提出对视知觉综合性的把握,视觉经验固然会受到文化惯例的影响,但视知觉也具备一种以非惯例化的自主方式把握构型的能力,从而介入了视觉建构之进程。
在当今景观时代,景观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装点美化城市的含义,成为城市情感认同、社会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部分城市推出的“店招统一出新”式的景观生产模式显然不能契合时代的需要。在城市景观的发展进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文化自身的作用,这将是比行政直接干预更有效、更持久的促进手段。
景观;权力;文化;美学
城市景观是人们城市生活的总体景象。我们不仅需要街心花园、广场雕塑点缀城市,让人赏心悦目,同时还需要上海陆家嘴这样的景观,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象征而起着鼓舞全民的作用。总体上,景观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但目前的城市行政仍然倾向于直接支配、管理景观生产。无论是理论,还是历史实践经验都告诉我们,权力需要借助文化的作用来更有效地实现自身的目的。避免权力直接介入城市景观发展,应该是城市文化战略的切入点。
一
城市景观最重要的就是建筑以及各种基础设施,当然也包括自然景象。它既指外物构成的景象,也指人们主体性的、有意识的活动、表演和呈现。景观,通常起着城市的装饰美化作用,但深层次上,景观是占主导地位观念的外化。
城市展现出来或将要展现出来的各种形象,既包括它努力想呈现的东西,又包括它努力想从城市中删掉、掩盖的东西。景观不可能离开人、离开观看来单独加以定义,它是某种话语体系、特别是权力与资本的话语体系有意、无意引导人们注视的景象,它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景观将自己展现为社会自身、社会的一部分,抑或是统一的手段。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景观是全部视觉和全部意识的焦点”。①景观作为生活世界的表象,通过人们的观看、注视甚至忽略而内化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正因此,外在的景观成为内在最隐秘的东西。景观能够影响到我们对城市的情感、生活态度和理念,甚至直接就是我们的情感、态度和理念。
景观已经取代现实而成为现实。费尔巴哈认为基督教神学语境所处的就是“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的被颠倒的时代。②居伊·德波则认为,当今资本主义世俗基础已经将自身分离出来,在茫茫的总体性景象群中建立了一个与基督教上帝之城一样虚幻的“景观社会”。“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③景观与现实、观念之间这层关系,我们尚未有足够的理论关注。
进入现代社会,景观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此时的景观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于刷新漆、种花草、兴建市民广场,而是需要纳入到文化自律发展的轨道当中。文化发展总是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对此城市行政有时理解并不充分,景观发展几乎等同于治理“脏乱差”的行动,出现了行政直接干预的景观“统一出新”的模式。如某市近年为了“美化市容市貌”,由政府支付费用,对于沿街店铺门头做了统一出新。有关方面强调“免费更换店招可以达到视觉上的统一,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提升部分商业街的视觉感受”。④
各大城市都存在微小商户的招牌广告破旧、杂乱、缺乏规范等问题,政府“统一出新”,可以在很短时间里,取得视觉上明显的效果。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难以长久,更关键的在于行政干预式做法并不能真正促进城市景观文化的发展。
一是,只要“统一”的举措是行政的、行政化的,那么它就无法真正介入艺术和美学领域。当然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凝固的、每次可以进出的艺术或美学领域,只存在各种艺术实践活动。只有通过这种实践行动,依据艺术与美学的法则、延续它的传统、开创一种新传统的实践活动,艺术的或美学的领域才随之成形。只有依据诗的方式来表达、言说、阅读、理解诗的时候,诗歌的领域才存在;一旦我们试图用朗诵诗歌来治疗某种疾病时,诗歌及诗歌的领域就消散了。“统一出新”店家的招牌,虽然在字体、颜色、形制上有所变化,但它们仍是同一时段、同一制作的结果,是源于同一句法的写作。这既不是美学的方式,也不是美学可以接受的方式,就像抱着治疗疾病的目的来读诗一样,“出新”不免使城市景观失去了美学意味。
二是,改善商铺店招状况、提高街区的视觉形象需要更多地借助文化自身的运作,而不是行政化的统一。“统一出新”阻断了城市形象自身的历史。
城市形象有它自身的发展历史。理论上讲,店招广告是与艺术、美学、市场相关联的一种设计,不论这种设计究竟如何,设计制作活动本身总是保持在商业与文化交织的领域当中,延续着行业内部的运作机制,保持着基本的艺术审美的法则。也就是说,在正常的商业竞争环境中,广告公司为了生存,总是会使广告设计看起来更像艺术。这构成了店招广告的形象史。形象在自身的创造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自己的词汇,变换句法,并且形成自身的标准与运作法则。正是这种历史积累,形象的制作和创造才有了自身的“文化基础”。从这方面来说,“统一”不仅会使商家的形象化失去可能的创造性、个性化发展的机会,更关键的在于,它阻断了城市形象的历史。“统一出新”的目标就在于“新”,目标决定了它更多的是、甚至只能是某种“崭新化”的、翻新的操作:通过行政上的集中整治,在短时间里使市容有一个整洁翻新的面貌。这与城市形象的历史延续变得没有太多关联。
在“出新”行动中,设计行为更多受到行政意图的支配。这里如果还有美学原则的话,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原则:整齐就是美。整齐美观的视觉效果确实可以给人一定的美感,但如果美学原则仅仅体现权力意图时,其自身也就消解了:“整齐”的美学原则完全转化为行政操作的“出新”原则。此时,如果美学、艺术的领域还在,那么,权力就像入住的新主,已经下令要把破旧的画廊翻新为亮堂的马厩。
二
权力需要通过文化更加深层、有效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目标。
但显然,“统一出新店招”的例子中,权力却以文化话语代理人的角色直接干预景观的生产。此例虽小,却颇为典型,它反映了目前行政权力与景观生产之间普遍的关系形式。如果说,城市在本质上是权力的节点,城市形象最终必然体现权力意志的话,那么“统一店招”似乎确实最直接地做到了这一点:原本标识混乱、残缺、破旧、五花八门的小店铺,一夜之间有了美观统一的崭新面貌。但这种整齐划一的视觉形象,只能使人联想到整个“出新”行动背后的行政力量。街区店招景观直接成了权力支配的产物,它除了鲜明地表示最近的一次雷厉风行的行政整治之外,似乎不能让人体会到景观的历史文化韵味。
严格说来,权力体系并不是一个表意系统。“隐蔽的权威自己不能是实体化的,因为它本身不是一种文化,而是文化之可能性的特殊条件”。⑤它对整个表意系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詹姆逊所说,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都是以政治、权力作为其绝对视域,⑥但就权力本身的实践而言,它与铺设下水管道的行动没有太大区别。即使承认权力的支配与强制可以成为一种表意行动的话,那也不是让人乐意接受的形象。所以任何明智的政治,权力不是隐身,就是躲藏在文化背后,通过文化表达意见。这比它自己直接出面更具有持久的动员力量,也就是说,权力只有变得不那么绝对支配时才更能支配;权力只有通过文化的转换变得不那么权力时才可能产生更深刻、更有效的强制力量。
这一点中西方早有认识。《老子》第七章曰:“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第六十六章亦曰:“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权力主要体现为支配,但它往往需要通过一个看起来与行动方向相反的举措来实现自身的目标。欲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就要言辞卑下;欲保全其身,就先要把自身置之度外;欲实现自己的目标“私”,就先要做到“无私”,先考虑他人的利益。正是“后其身”,才能“身先”;“外其身”,才能“身存”。只有“不争”,才能实现“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局面。当权力把自身推向绝对时,就毁灭了自身的领域,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力量,⑦正如《汉书·陆贾传》中所说“极武而亡”。所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德国学者卡尔·施密特对国家主权的分析也能帮助我们理解权力的本质。国家的最高权力——主权,并不是在一般常规状态下动用的权力,而是在它所认定的某种特殊状态下,拥有的绝对支配,即:对非常状态、无法以概念规定的状态、涉及国家存亡的极端危险状况的决断。他说:“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⑧正因此,主权才保持了自身至高无上的本质。但常规状态下,国家主权总是被悬置起来,正所谓“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最高权力的这种状况其实也是一般权力的普遍特征,即强制总是作为随时可以动用的力量而尽量保留在那里。
社会学家同样注意到权力的这种特征,“社区在决定某些事务时,最有权力的人往往不行使其权力”。如美国某小镇上一家公司行使自己的权力反对一项颇得人心的政策,“其结果是镇上的公众对公司的支持程度就会下降”。⑨可见,最大化地发挥权力的效能就是不直接使用权力。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权力总是通过某种间接的措施、迂回的路径,特别是通过文化达到自身的目的。古人的概括极其准确:“逆取顺守”、“文治武功”。
不同于权力,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情感、感性、欲望的产物,它更了解、也更善于处理人的难以整齐、一切的内在问题,而权力在这方面往往束手无策。权力一旦仗恃自身强大的力量以及政治领域的成功,就会在这片复杂的感性领域中显得无能。
就权力本身而言,它只是实现自身意志的强烈冲动而已,正像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理性一样。理性起初不屑于了解那令人捉摸不透的感性领域。理性“除自身概念之外,便一无所知,还拒绝探索情感和知觉的本质。如果康德所称的‘混乱的感觉’永远处于理性的‘绝对王权’的认知范围之外,理性的‘绝对王权’怎么可能保持其正统性呢?”。⑩萨义德也认为,人类经验的核心领域仅仅依靠强权是无法触及的。有一种“最主要的东西”,“人类经验有个无法缩小的主观的核心,这个经验是历史的、尘世的,也是可以加以分析和说明”。但“它不能被强权的理论所囊括,不能以教条来划分,以民族来画线和限定,也不会永远束缚于分析的构架”。(11)
高高在上的权力不屑处理众人纷乱无绪的感情、感性问题,而理性也毫不关心人们的感知活动。但是,权力如果不触及到人的最内在经验的核心时,也就不能真正实现统治。权力固然可以发号施令,但却无法使人心悦诚服。令行禁止的方式在面对复杂微妙的感性领域时,那种缺乏差异性的“一刀切”、无甚美感的整齐和统一,实际上是放逐了人们内在的感受性。游离的感受性自我飘荡,完全逃逸在权力与理性的视野之外。权力失去了赢得人的内心、深层情感认同的机会。事实上,任何统治,正像理性一样,为了自身的目的,必须重新审视感性的生活,把情感、感性纳入自身视野,“不理解这点,什么统治也不可能是安稳的”。(12)任何政治权力都不可能仅仅通过行政强制而长存下去,(13)中国传统政治主张的“以德服人”,强调的正是德行在人的内心普遍激发的感激之情所形成的政治基础。
正因此,理性开始将感性吸纳到自身当中;权力开始通过不同于自身的礼乐、文化和艺术实现自身更强有力的统治。
在黑格尔哲学那里,理性不再与感性对立,而是包含了认识、实践和情感在内新的观念。“它力图改变我们的肉体倾向,目的是为了使肉体倾向达到与普遍的理性原则自发一致的境地。人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自我实现的实践就成了理性和经验之间的中介”。(14)鲍姆加登所定义的“美学”正是试图以全新的姿态开拓整个感觉领域,并且实施“理性的殖民化”。对于鲍姆加登来说,审美认识介于理性的普遍性和感性的特殊性之间;(15)“感觉和经验的世界不可能只起源于抽象的普遍法则,它需要自身恰当的话语和表现自身内在的、尽管还是低级的逻辑,美学就是诞生于对这一点的再认识”。(16)
杂乱正是通过审美过程达到整齐;难以规范的情感、感性正是通过艺术、文化实现规范。只有审美、文化才具有能力处理那些微妙而复杂的感受、情绪以及难以名状的感觉。它们是穿梭于理性的普遍性与感性的特殊性、规律与例外之间的针线,具有缝合两者的能力。经典美学认为,审美既带有几分理性的完美,又显出混乱的状态。此处混乱(confusion)的意思不是杂乱(muddle)而是整合(fusion)。孤立地划分单元乃是概念化思想的特征,而在有机的相互渗透中,审美表象的各要素都不再是各自独立的单元,它们越是“混乱”就越趋向于“多单元的统一”,表象也变得更加生动、鲜明和完美。(17)
新理性、新美学为的是打造人类全新的主体性。中国传统时代,礼教的努力在于造就“君子”;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实践则是明确地培养“全新的人类主体”,都是针对人的主体性。君子修身主要在于道德层面,道德不是外在的律令,而是“慎独”,一种完全源自内在的道德自觉;而现代西方则强调通过艺术审美的形式培养“全新的人类主体”。这个主体性同样不是依靠外部强制性的力量催生出来,而是从人的充满自由的内在深处产生。这是既高度自律、又具有充分主动性的个体力量。启蒙思想家卢梭《爱弥儿》说:“心灵只从自身获得法律;人们想要约束心灵就得放松心灵;只有让心灵获得自由的人们才能约束心灵。”后来的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也认为,现代个体不再是与社会、政治对立状态下的自我压抑,自律成了“政治社会正常的延续活动和有机的补充”。很显然,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最根本的力量不是权力的强制,而是习惯、虔诚、情感和爱。这意味着,制度里的强制力量被审美化了。(18)
只有通过文化,权力才可能将人的那些复杂微妙的内容纳入自身视野,并真正实现持久深入的内在规范。这正是中国传统时代“礼乐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西方“美学”诞生的现实背景。中国的传统社会,始终有一个庞大的以礼教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礼教承担着约束人心、规范行为、增强凝聚力的作用。一个王朝可以覆灭,但传统的礼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着。新的王朝总是通过延续前朝的礼教文化实现社会的再度凝聚和生活秩序的修复。可以说,礼乐正是王朝的权力冲动与小民狂野无知之间架设的桥梁。
礼教之于传统中华帝国,就像文化之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在萨义德看来,“帝国主义意味着对不属于你的、遥远的、被别人居住和占有了的土地的谋划、占领和控制”,与所有的征服一样,这个过程包括了一系列残酷的镇压,但是帝国主义“不仅是关于士兵和大炮的,也是关于思想、关于形式、关于形象和想象的”。包括了“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帝国主义与文化由此形成了直接的联系,“对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公民来说,帝国是个不会使自己难堪的重要文化议题”。帝国主义不仅是政治事实,更是一种文化存在。“维系帝国的存在取决于‘建立帝国’这样一个概念。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文化中做的。反之,帝国主义又在文化中获得了一种协调一致,一套经验,还得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即使在今天,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基本结束时,它仍然像过去一样,“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19)所以,帝国主义既包括了战争、残酷的镇压手段,也包括了人们头脑中扭曲的观念,一种殖民主义者的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帝国持久存在。帝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从其自身的视角、历史感、情绪与传统出发,对它们的共同历史所做的一套解释”。帝国主义“作为共有的记忆,作为充满矛盾的一整套文化、意识形态和政策,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所以,帝国主义的存在当然依赖它的军队,但更有效、更持久的统治不是帝国的权力本身,而是它的文化。萨义德说:“我们必须认真地、完整地看待那孕育了帝国的情绪、理论基础、尤其是想象力的文化。”(20)历史上,成熟的政权都表现出对文化系统足够的倚重。
三
建国以后,传统的文化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契合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美学、文化体系并未完全建立并完善起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美学热”,直到今天城市店招的“统一出新”,都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与当今社会政治体制相契合的美学体系。美学作为一种文化体系,此时主要的目标不仅在于指明什么是美的,更在于作为一种引导、规范、组织的系统,将个体的情感、感受纳入自身能够协调统一的框架当中。
红琴问道,小和尚,别的和尚头皮上都烧有很多疤痕,你为什么没有?风影告诉她,那叫受戒,就是用香火烫十二个洞,受了戒就名正言顺了,可以云游四方,走到别的寺庙都管吃管住,不用花钱。不受戒只能是个野和尚。她又问他为什么不受戒,他说自己年纪还小,师父说了须等几年才能受戒。说到底他现在还没有争取到编制,不能算是个有身份证与通行证的正式和尚。
当传统的地方性、情感共同体正在消散之时,人们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归依,而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剧人们情感的离散。在人口流动性的条件下,城市很难作为传统意义上共同体的载体,为人们提供归宿感。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城市所提供的功能服务,人际交往越来越多地偏向工具理性的、功能性的操作,而情感、感受游离出来,成为城市体制难以吸收的能量。城市生活及文化形态的错综复杂,正表明人们的情感、感受性正在成为现代城市的难题。
在这种背景下,城市景观成了重新整合现代人情感及感受性的重要手段。在当今“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表象”的时代,(21)景观变得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塑造现代人价值观及生活模式最普及的学校。景观已经不再满足于给新房外墙贴上瓷砖的工作了,而是要给予眼睛以及整个感官、欲望一个充分满足的安置。
这种安置需要交给始终处在“绝对视域”当中的文化、美学机制。在这一点上,文化比权力更能够胜任权力的工作,因为它诉诸更内在、深层次的因素。正像我们在香港街头看到的缤纷广告一样,景观通过富有吸引力的视觉形象实现对杂乱的感知、感受和情感的组织,已经参与到社会秩序的建设当中。
香港的一些商业街区,各种店招横跨街道,铺天盖地。初看起来,颇有些混乱,但作为景观,它们无疑是成功了。它们已经成为当地颇具代表性的街区形象、香港标志性的景观。无论是从影视作品中,还是在照片上,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来,“那就是香港”。店招虽然杂乱、混乱,但却有着自身复杂的内涵和逻辑,那些不同风格、不同档次、源于不同公司、有着不同时期印迹的制作混杂在一起,呈现出景观自身的历史和独特的美学原则。
它们显然不是基于“整齐就是美”的原则。如果说“统一出新”的门头仅仅只是一种符号的汇集,那么,香港街头的广告则是不同类型符号构成的复杂句子。当人们走过这些街道时,不同时期的招牌聚集在一起,就不再是一个一个彼此没有关联的单一符号,而是以某种空间形式结合在一起能够传达某种蕴含的句子。句子的构成既在于符号之间的差异性,也在于历时性的结构。符号的意义源于符号之间的差异,“木”与“本”,这两个字的含义是通过字形上的区别以及声音上的区别获得的。句法结构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些不同时期制作的店招在彼此保持共时性差异的同时,都遵循着基本的句法。
从图片资料来看,香港起初的招牌常常设在店家的门头门柱上。但有的店家将门柱上的招牌转过90度,面对着街上的行人;门头招牌不仅设在门头上,也挂在街道上,迎着行人。这样,街上的行人在行走时就可以看到店招。从店铺门头上挂出来的招牌越挂越远,越来越多,最终横跨整个街道,由此形成香港街区店招特定的写作句法。
很显然,街头广告本身已经形成自身鲜明的传统——历时轴的句法结构。它有自己的边界,有自己的经典样式,典型字体、颜色,它有自己包括各种商标、图案以及使用材料上缓慢变化的历史。它形成了自己的品味。尽管理论上讲,一幅新增设的街头广告完全可以忽略这一传统的影响,但从不同时期街头广告可以看出,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广告之间存在着一种至少是宽泛意义上的协调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广告中的中文与英文都能保持基本的协调。新广告的设计者并不是凭空设计,所有的设计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此时此地的表述句法,与既有的传统进行呼应、协商、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业街区的景观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传统,景观的生产以及再生产受制于这个区域的文化氛围,而不是外在的行政干预。
大体来说,街头广告是一片自由表达的区域。作为商业广告,尽管有一些广告可能更大、更醒目,但它们不可能排斥其他数量众多的小广告。这意味着这里是保持着某种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各种廉价的小型广告都拥挤在街头,反映该区域以中低端商业活动为主的特点,广告密集的程度表明这些地区的商业充满活力。正是这种多样性、多元性使得景观保持着吸引力,也显现出城市的个性。
显然,所有这些解释都源于街头广告由于自身历史的延续而形成的内在的美学机制和文化蕴含,然而最终决定景观根本性质的是其背后的与资本以及资本主义体制相关的一整套话语机制。
就景观根本上作为资本的缩影、资本主义体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言,香港街头广告充分实现了它的目标。它成功地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景观出现在街头,在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时候,以具有吸引力的视觉形象完成了它的使命。显然,透过文化话语层面的装饰,历史与美学蕴含的丰富性仍然无法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城市景观本质上的贫乏。所有街头广告都指向一个目标:商业利润。景观的丰富多彩不过是被商业控制着的真正意义上的一元景象。“景观……以一种将活生生的价值颠倒为纯粹的抽象价值的凝结状态的东西来加以占有,在这些迹象中,我们认出了宿敌——商品”。(22)景观作为商品的影像,自己也成为了商品。“商品化不仅仅是可见的,而且那就是所见到的全部”。(23)这种一元性正是现代城市生活趋于不可挽救的无聊与平庸的最直接因素,而这种无聊与平庸又是以生动有趣、新奇繁富的视觉景观为表征。也就是说,文化话语层面上的审美多元与历史延续,已经成为服务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手段。在这里,景观内在的文化蕴含已经被资本主义体制拦截,并不必然地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上与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建构相关,景观作为精神解放表征的同时,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解放。“经济增长已将社会从强迫他们为了生存同其进行直接斗争的自然压力中解放出来,但至今他们并未从他们的解放者手中解放出来”。(24)在文化话语层面上,景观与资本主义的总体进程紧密联系,因为“从整体上理解景观,它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其目标”。(25)
显然,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景观正是以其文化特征实现了资本的目的。资产阶级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取得革命成功的阶级,它在景观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功”同样值得借鉴。新的城市化进程中,景观的创造与发展恰恰应该伴随着新型的城市文化的兴起而实现。
注:
①③⑦(21)(22)(23)(24)(25)【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3、10、46、3、13、15、14、3 页。②【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第二版序言”,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页。
④中国江苏网http://js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3/08/23/018343797.shtml。
⑤(13)【英】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53、57页。
⑥【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⑧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2页。
⑨【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⑩(12)(14)(15)(16)(17)(18)【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3、9、3、4、3、8 页。
(11)(19)(20)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0—41、6—12、13—14页。
〔责任编辑:青 末〕
The Cityscape between Power and Culture
Tong Qiang
In the present era of landscape,the urban landscape has far more meanings than just to decorate and beautify the city.Landscape has become a crucial part of the city’s affec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connection.Yet some cities have presently put forward a landscape production model of“unified renovation of shop sign”,which apparently cannot correspond to the demand of the times.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scape,we need fully stimulate the function of the culture itself,and this will be a more effective and enduring method than direct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cityscape;power;culture;aesthetics
G05
A
1001-8263(2014)07-0103-07
童强,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 南京210093
*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视觉文化研究”(12JZD01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