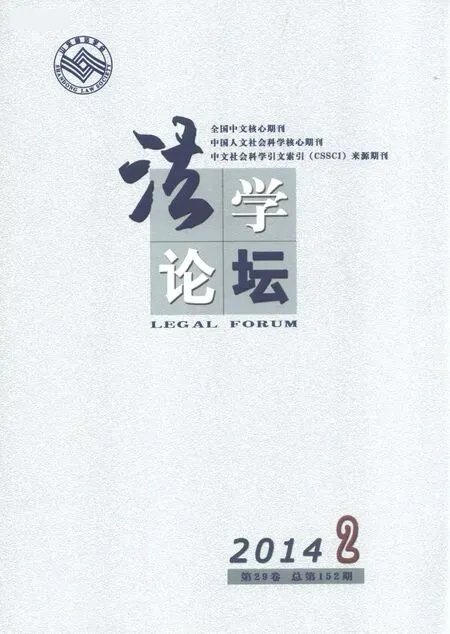城镇化视阈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收回之类型化研究——基于案例和规范的分析
杨 蕾
(山东大学 法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城镇化视阈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收回之类型化研究——基于案例和规范的分析
杨 蕾
(山东大学 法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我国目前的宅基地法律制度呈现出最明显的特点是公有但私用,即宅基地的所有权为集体组织拥有,而宅基地使用权为农民私人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不仅是农民重要的私人财产权,更事关农民适当生活水准权的维系。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是宅基地管理制度之一,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强制性剥夺或者限制。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可以归纳为公益性收回,处罚性收回和身份性收回三种类型。由于对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关注比较缺乏,实践中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做法也差别极大。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类型化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现行的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弥补现行制度缺陷。
城镇化;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
根据我国1982年《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为公有制,具体而言即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为集体组织所有。宅基地的使用制度与国有土地制度同样采取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制度构架,即宅基地的所有权为集体组织拥有,而宅基地使用权为私人享有。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土地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由此引发的土地和房屋拆迁纠纷日益受到公众和学界关注。集体土地使用权收回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涉及到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剥夺或者限制。但对该制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注度较少。最近几年,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纠纷经常见诸报纸和其他媒体,从以下案例中可以管窥豹。
案例1:2008年山东省某县因修建公共道路收回宅基地引发纠纷(以下简称:案例1)。随着县城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修建横贯县城的黛溪五路,因此要占用南范村村民的宅基地。该县政府要收回7名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注销其宅基地使用权证。7名村民因对安置补偿标准不满意,拒不搬迁,并向某市中级法院提出了行政诉讼。法院认为县政府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从而驳回了村民的诉讼请求。随后案件上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7名村民败诉,房屋被拆除,宅基地使用权被收回。*根据李文亮的报道进行编写。参见李文亮:《到底是政府项目还是村庄工程?民众应有知情权———听证会缘何中途“变脸”?》,载《山东法制报》2008年11月24日A01版。
案例2:2008年8月广州市海珠区某村因旧村改造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引发纠纷(以下简称:案例2)。该村被列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的重点区域,改造的范围涉及众多的农村宅基地。其中2户村民拒绝与该村联合社及改造合作方保利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纠纷诉至法院,经过法院的审理,最后2户村民败诉。法院依法启动强制执行程序,2户居民的宅基地使用权被强制收回。*参见曹志明:《我院强制执行三宗琶洲村“三旧”改造案件 两“钉子户”宅基地使用权被依法收回》,http://www.gzhzcourt.gov.cn/display.jsp?
除因旧村改造、建设公共设施等情况外,宅基地使用权被收回的情形还包括宅基地闲置、户籍迁入城市、升学就业、外嫁女、以宅基地换房、以宅基地换户籍等等多种情况。宅基地使用权收回所引发的纠纷和诉讼案件,应当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同时深刻反思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并提出有效的改善路径,为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打造和谐的制度环境。那什么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制度?与城镇化的关系怎么界定?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类型化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城镇化背景下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
“宅基地”一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我国土地制度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居者有其屋的观念,“宅”也被中国人赋予“家”的涵义。“宅基地”不仅扮演着为农村居民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角色,成为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支持,更维系着人们对“老家”的特殊情结。
(一)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是城镇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城镇化所带动的经济社会转型将会给我国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带来极大冲击。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城镇化不仅成为扩大内需的最重要来源,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器。同时城镇化建设还承载着改变城乡二元分治体制,以及农民对于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强烈愿望。我国推动新型城镇化所依靠的两大制度改革分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环节是宅基地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等农民土地权益的维护和保障,这成为城镇化改革成败的关键。
之前学界对于宅基地使用权性质的争论,随着《物权法》的出台而尘埃落定。宅基地使用权既有财产权利的共同特征,同时又具有非常强烈的福利性质和社会保障性质,与农民享受适当生活水准权密不可分。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以及《物权法》第125条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属于用益物权,农民依法享有宅基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成为农民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重要保障。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明确规定了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内涵,该条约规定适当生活水准权是人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权利,即维持自己和家庭适当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穿着和住房的条件,同时生活水准能够不断改善。国家有义务来保障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实现。*参见Bourquain, Knut. Fresh water access from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a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water and human rights law.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8. pp.137.因此,“适当生活水准权”是指人们所享有的维持相当生活水准的权利,具体而言包括获得足够的食物,获得合适的衣着以及居住条件三项内容。在我国城镇化的背景下,数量庞大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但是他们的身份却被绑定在农村户口上,未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这些人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迁徙的“候鸟”和社会福利“边缘人”。由于城市房产价格高涨和对购房者的诸多限制,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对“家宅”的浓重情节,宅基地实际上成为“农民工”享有适当居住条件的重要保障。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2款对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规定来看,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主要包括三项内容:(1)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宅基地使用权的获得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紧密绑定,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身份限定为本集体组织内部成员,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2)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划拨取得类似,也是无偿的。(3)宅基地使用权的使用期限。宅基地使用权的使用期限没有时间限制。正如学者总结的那样,宅基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的无偿性以及使用期限无限制这两大特征,决定了宅基地使用权“具有福利性和社会保障功能”。*李翔,徐茂波:《〈物权法〉不应限制宅基地流转》,载《中国土地》2006年第2期。宅基地使用权因此突破了财产权利的范畴,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权利属性。
(二)城镇化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之间复杂纠葛的关系
一方面,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为城镇化提供了重要的稳定机制,维持了宅基地使用权的低流动性。将城镇化分为中心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城市化、去城市化和再城镇化4个阶段的观点,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目前普遍认同。*参见klaansen L H,Molle W T M,Paelinck J H P. Dynam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Aldershot: Crowth. 1981.pp. 57.这四个阶段被诺瑟姆用“S”曲线来描述。根据这一曲线,我国处于城镇化的发展中期(即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的起步阶段,但发展速度在加快。*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发展路径》,载《改革》2008年第7期。这一阶段人口的流动是单向的,即从农村或郊区向城市中心区迁移。*参见王学峰:《发达国家城镇化形式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年第11期。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规模,就称为判断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巴曙松研究员认为,未来我国城镇化的核心内容是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包括目前6.9亿城市常住人口中的2.3亿非城市户籍人口,以及1.5亿新增农业转城市人口,共计3.8亿人。*参见巴曙松:《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是城镇化核心内容》,载《东方早报》2013年4月12日。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将有3.8亿农民将转变为市民。而目前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同样庞大惊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字,我国目前的农民工数量超过2亿。同时增长速度非常迅速,每年新增农民工人数高达1000万。*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号)》,http://www.stats.gov.cn/ tjfx/jdfx/ t2011 0428_402722253.htm. 29, 2011-04-28.
我国城镇化所带来的巨大的流动人口,城市难以及时容纳。无法被城市容纳的农民如果聚集在城镇边缘地带,就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由于我国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局限,“进城”农民难以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大部分未被城市接纳的农民仍然拥有宅基地使用权。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存在充当了流动人口的“缓冲筏”,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过程中形成城市贫民窟的风险。因此,有学者强调如果开放宅基地使用权的流通环节,应当态度慎重,步骤谨慎。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民适当生活水准权的维系对宅基地有很高的依赖程度,一旦失去宅基地,农民将很有可能居无定所,成为城市流民。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的解禁,将很有可能危及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参见孟勤国:《物权法开禁农村宅基地交易之辩》,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4期。也有学者通过对宅基地使用权特征的分析,得出应当维持宅基地使用权限制流转制度的结论。在我国的土地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宅基地使用权担负着部分社会保障功能,对于维护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和保障农民的适当居住条件的价值难以替代。因此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仍要继续维持限制流转制度”。*参见丁晶:《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维护农民利益的最佳选择》,载《特区经济》2010年3期。
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公共设施建设和工业建设对土地的需求量快速增长,宅基地使用权的限制流转反而成为增加土地供应的障碍。面对人多地少的土地现状,我国的城镇化面临着既要守住耕地面积红线,又要解决建设用地的供应的双重压力。宅基地使用权收回成为增加土地供应的重要途径。相对宽裕的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成为增加土地供应的重要来源。学者对山东等省份的宅基地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后发现,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出现大量的闲置宅基地和房屋,农村“空心化”情况严重。如果能够实现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土地供给潜力非常巨大,将为城镇化注入新的发展活力。2012年3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一份关于农村空心化的研究报告,题目是《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我国农村空心化整治潜力约1.14亿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远景理论潜力约1.49亿亩。*参见黄文山:《填补“空心村”整治政策空白》,载《中国土地》2012年第11期。
同时,宅基地使用权在流转方面的严格限制,更加剧了宅基地的闲置状况。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和政策均禁止宅基地使用权向本集体组织以外的人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只能在本集体组织有限范围内流动,难以实现宅基地的集约利用。《物权法》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但是未规定可以对宅基地进行转让、抵押等处分权利。原国土资源部在2008年7月发布的《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46号禁止城市户籍的公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或者在宅基地上建设住宅。并强调一旦购买就视为违法,各地的土地管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登记手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07〕71号,简称“71号文”)再次重申宅基地只能分配给本集体组织成员,城市户籍的公民不得购买农村地区的宅基地使用权,也不得购买农民所有的住宅。
最近几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向前推进,土地供给的压力不断增大,开放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呼声很高。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的严格限制开始松动,有些地方政府开始对宅基地的有偿流转进行有益的尝试。如安徽芜湖市、江苏苏州市等地对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改革进行试点,但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仍然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架构起来的“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二元土地管理体制,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两者间泾渭分明。目前而言,集体土地转变为可以在二级市场自由流动的国有土地,必须转变为国有土地。即通过征收程序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性质,从而成为国有土地。土地征收法律规制严格,程序审批周期长。而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不仅符合目前土地制度的法律政策框架,而且程序规定相对简单。在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下,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没有发生改变,因此规避了“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二元土地流动的制度限制。不仅如此,宅基地使用权收回过程中,集体经济组织在收回和补偿程序占据主导地位。集体经济组织对当地的情况更为熟悉,并能够采取民间调解、协商等柔性手段,避免运用行政强制权力,防止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再加之宅基地收回的补偿比征收补偿实行的标准低,能够解决更大数量的土地供应,满足城镇化的土地需求。
二、我国的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制度构成
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平衡分配土地利益将成为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面临的挑战之一。只有完善的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以及该制度获得良好的运行实施这样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平衡好农民、农村集体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复杂利益。否则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阻滞城镇化进程。因此,必须要关注城镇化过程中宅基地的收回制度构成和实践运作。
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将所有居民区分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同时根据不同户籍而分配社会资源。农村的宅基地制度的制度构成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宅基地的产权制度,用以确定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第二是宅基地的使用制度,主要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期限以及使用方式等问题。第三是宅基地的管理制度,主要规范行政管理机关对宅基地的行政管理方式和内容,如宅基地的登记制度、宅基地使用权的回收制度等。宅基地收回制度属于宅基地管理制度的内容之一。
我国宅基地的产权制度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制度,即宅基地所有权为集体公有,而使用权为农民私人享有。《宪法》第10条规定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有制。在国有土地之外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组织,集体所有的土地范围涵盖了农村和郊区的宅基地以及其他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3条的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村建设用地的范畴。因此,宅基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组织。同时由于宅基地使用制度的无偿化和使用主体仅限于本集体组织成员,宅基地管理制度则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限制流转,管理体制上实行村——镇——县三级管理。
对于什么是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法律法规和学术界缺少规范及明确的界定。一般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收回是指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法律规定的主体,依照法律程序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应当包括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的含义和法律性质,由收回主体、收回的客体、收回条件和收回程序及收回补偿等内容组成。目前,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中,散见于《土地管理法》和部分地方法规和规章中,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除此外,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等发布的政策和文件也是重要的非法律渊源。
三、我国现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类型
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的法律依据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土地管理法》,第二个层次是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其中,《土地管理法》第65条明确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具体情形,包括建设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违法使用宅基地使用权、停止使用宅基地三种情况。而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则针对当地的城镇化程度,确定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类型。由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各地的规定不尽相同。在北方,由于当地的农村人口较多,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情形往往较为具体和多样。而在南方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收回的情形较少,收回的条件也非常严格。对法律法规进行整理分析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将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归纳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宅基地使用权的公益性收回;第二种类型是宅基地使用权的处罚性收回;第三种类型是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收回。
(一)宅基地使用权的公益性收回
宅基地使用权的公益性收回,是指享有宅基地使用权收回权的法定机关,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在收回条件符合法律规定时,启动宅基地使用权的强制性收回程序,同时对原宅基地使用权人给予一定补偿的制度。判断宅基地使用权的公益性收回,关键因素是对“公共利益”进行判断和甄别。然而在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的法律依据中,准确界定“公共利益”内涵的实体性规范极为罕见。与此同时,确定“公共利益”的规范性程序则近乎空白。*参见刘向民:《中美征收制度重要问题之比较》,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和“旧城改造”等情形更加剧了“公共利益”判断的复杂程度。
《土地管理法》第65条第1款的规定非常原则和简单,而且未使用“公共利益”这一术语。《土地管理法》第65条第1款仅规定为了“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可以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如果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公共利益”是狭义的,仅限于建设集体公共设施(如修建村内公共道路)和公益事业(幼儿园、敬老院、集体休闲场所等)两种情况。根据该条的规定,“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可以进行两种解释。第一种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意味着,必须由集体组织作为公共设施或者公益事业的建设主体,进行立项、规划、取得选址意见书、进行道路等工程建设等。第二种解释则外延更广,只要属于村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就可以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收回,而对于建设主体没有限定。《滨州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就采纳了第二种解释。在该办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中,只要建设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就可以进行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上述工程的建设主体不局限于村集体组织,任何主体都可以,扩展了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土地管理法》属于国家土地管理的基本法律,而《滨州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属于地方规章。在法律效力的位阶上,《土地管理法》的法律效力要高于《滨州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但是,《土地管理法》对于“公共利益”的模糊界定,加之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有着强烈的利益驱动,难以防范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对“公共利益”进行扩大解释。
不仅如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在实践中也会引发纠纷。在案例1的审理过程中,县政府和村民争议的焦点就在于“黛溪五路”的性质。“黛溪五路”属于公共通行的道路,在性质上无疑属于公共设施,但是是否属于村庄使用或者主要由村庄使用这一问题各执其辞。被占用宅基地的村民坚持认为:“黛溪五路”不属于乡村公共设施,而是县里的公共设施。主要的理由是道路建设的土地手续是县政府的立项批复文件和县建设局出具选址意见书。而县政府则认为:“黛溪五路”项目是村里的项目,项目的拆迁由村委负责组织,确定安置补偿标准,具体实施补偿安置等。而案件审理终结,本案的调解书对该项目的性质也未进行清晰的界定。诸如此类的“公共利益”的内涵之争,常见于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以宅基地换楼房、换城市社会保障,以及对集体土地整理收储或者各色新农村建设等情形中。
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对于宅基地使用权收回中“公共利益”的判定,仅有《土地管理法》第58条的规定可以参考。《土地管理法》第58条规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益性收回,明确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的前提必须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该条法律规范虽然使用了“公共利益”一词,但没有明确“公共利益”的准确含义,也未对“公共利益”的具体情形进行规定。《土地管理法》第58条还将“旧城改造”归入公共利益的范畴。那么宅基地使用权在强制性收回时,出现的“旧村改造”与“旧城改造”情况类似,“旧村改造”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实践中倾向于认为旧村改造属于“公共利益”。例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案例2的终审判决就认为“旧村改造”属于公共利益,法院认为“旧村改造”不仅关系到村民的个人利益,同时也是对于全村的共同富裕和生活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旧村改造”有公益因素,属于公共利益。有些地方法规明确将“旧村改造” 列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公益性收回的情况之一,如《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12条。《滨州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类似,只要进行旧村改造,没有正当理由不退出原有宅基地的农民,可以依法收回其宅基地使用权。旧村改造被确定为“公共利益”,已经远远超出了《土地管理法》第65条“公共利益”的范畴。因为旧村改造中大量的商业房地产开发项目,难以简单的界定为乡村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
要警惕宅基地使用权的强制性收回中“公共利益”工具化的倾向。否则如果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就难以排除商业运作甚至个人利益挟持“公共利益”,从而无法保证宅基地收回的公益性质。因此,清晰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已经迫在眉睫。所谓的公共利益必须满足追求利益的公众性,或使用目的与“公众有关”这一基本标准。*参见莫于川:《判断“公共利益”的六条标准》,载《法制日报》2004年5月27日。尽管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界定标准,但什么是“公共利益”仍是法学界和土地管理实践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有学者提出更现实的解决路径,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内容来完善“公共利益”的判定。这需要在立法时详细规定“公共利益”的具体情形。判断某事项是否出于公共利益首先要看其是否属于上述列举情形。同时,如果该事项在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立法机关独立享有“公共利益”判断权,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批,针对每个个案的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参见郑传坤、唐忠民:《完善公益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处罚性收回
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第二种类型是处罚性收回,是为了防止宅基地使用权人闲置宅基地或违反法律规定的用途使用宅基地,需要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强制性收回。宅基地使用权进行处罚性收回除了防止违法使用土地外,主要的目的是实现农村闲置宅基地的有效利用。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迁移,导致出现大量的空置和闲置宅基地。虽然农民已经迁入城市生活或者工作,但其农村户籍仍未改变,仍合法拥有宅基地使用权,但宅基地不再使用或者地上房屋不再有人居住。宅基地闲置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地方宅基地闲置的时间甚至能长达数十年。宅基地长期闲置,是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影响到农村新增人口的居住条件。以湖南省为例,2007年刘彬等学者选择该省200多个村庄为调查样本,对宅基地闲置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调查结果让人触目惊心。在上述200多个村庄中,由于各种原因而被闲置的宅基地共3000多处,而闲置宅基地的面积统计超过49万平方米。*参见刘彬、郭迪跃、许兆军:《204个重点村“宅基地问题”调查》,载《国土资源导刊》2009年第5期。
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是宅基地集约利用的重要制度保障。这种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类型一般有时间限制,即需要宅基地经过一定时间的闲置才能收回。《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34条第4款规定如果宅基地连续两年闲置的,应当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实际上只规定一种情况即连续两年未使用的宅基地可以收回。类似的规定如《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33条第4款,明确宅基地使用权批准后,超过两年不建设使用,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无偿收回。《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也只规定了一种情况即超过两年未使用的宅基地可以收回。建设农村公益事业或者旧村改造等情况在上述地方法规中均规定应当按照土地征收程序进行审批,而不适用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
此外,宅基地使用权的处罚性收回还针对其他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宅基地使用人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如将宅基地作为工业生产或者其他经营场所;第二种情况是对拥有两处或多处宅基地或者宅基地面积超过法定标准的情况。山东和山西等省份的地方性法规也规定可以收回多余宅基地的使用权。《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46条规定,农村居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多余的宅基地应当收回,并注销宅基地使用权证。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收回
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第三种类型可以称为身份性收回。身份性收回的原因在于宅基地使用权人因去世、撤销、迁移等原因而丧失集体组织身份,停止使用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收回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城镇化带来的“农转非”、升学就业、外嫁以及集体经济组织融入城市等原因都会引起农民身份的丧失,导致宅基地使用权被收回。
宅基地使用权身份性收回的第一个原因是农民的户口迁移。城镇化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密集型工业和第三产业在城市集中,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生活工作。他们因升学或者就业、婚姻等原因将户口迁走,成为城市居民,他们原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被收回。例如,《滨州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由于户口迁移到城市,宅基地不再使用的,可以启动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程序。《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规定村民迁居后腾出的宅基地,必须退还集体组织,对于集体组织是否有权收回则未进行规定。从理论推理和实际情况来判断,集体组织有权收回宅基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身份性收回的第二个原因是集体经济组织消失。在城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农业的依赖程度减弱,乡村逐渐与城市融合。原有的集体经济组织被合并、撤销或者转变为城市社区,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农民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转变为城市社区居民。因此,他们原有的宅基地使用权随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丧失而归于消灭。这种情况下应当进行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如《苏州市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即使宅基地未使用不满两年,但是如果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城市社区的,宅基地使用权应当收回。
还有一种情况是宅基地使用权无人继承。这在城镇化过程中也很常见。经过长期的城镇化发展,很多农民的子女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他们的父母一般在农村都拥有宅基地使用权。一旦这些老人去世或者迁入城镇,他们的子女却因为属于城市户籍而无法继承宅基地使用权。该种情况下宅基地使用权能够收回。此外,如果宅基地使用权人去世或者迁居,但没有宅基地使用权继承人的,也应当进行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例如,农村的“五保户”无继承人,如果他们去世或者离开居住地,其所有的宅基地将无人继续使用,就可以进行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中就规定了这种情况。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能否继承,学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目前尚未达成一致。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持否定态度。我国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对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的规定,仅是对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条件的限制,并非针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参见姜红仁:《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继承的法律思考》,载《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可以说,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收回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中的烙印。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身份截然不同,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权利性质亦差异颇大。“这两对范畴和土地权利性质和归属深深地交织在了一起。这种财产和身份的错误捆绑,导致城市化背离了它的真谛。”*湛中乐:《我国土地使用权收回之类型化研究》,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
四、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其他理论问题
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类型可以总结为公益性收回、处罚性收回和身份性收回三种类型。这仅是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研究的一个起点,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者们对该领域的关注。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涉及到的其他理论问题很多,例如,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性质、宅基地使用权收回中“公共利益”的甄别、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程序和救济等等,亟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同时,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应当设计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主体制度、程序制度、补偿制度和救济制度。目前,无论是《宪法》、《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政策文件对于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主体、程序;是否进行补偿,补偿标准和补偿原则;救济途径均缺乏具体规定。
首先,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主体缺乏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宅基地使用权收回涉及到三方主体:收回申请人、被收回人、收回批准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5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在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中,原来的宅基地使用权被收回的农村居民是被收回人。提出收回申请的主体是宅基地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提出宅基地收回申请后,宅基地使用权的原批准机关经过审查后进行批准。因此,宅基地使用权的原批准机关与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批准机关是同一机关。同时,宅基地使用权被收回后,宅基地的所有权仍属于集体组织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再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收回的宅基地重新分配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使用。因此,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的补偿的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是收回申请人,同时又是补偿主体。而《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则在宅基地收回程序中增加了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程序。
其次,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程序缺乏明确规定。在案例1中,因为缺乏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县政府对于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程序是参照2001年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程序由集体组织提出收回申请——发布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公告——进行评估——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偿安置5个步骤组成。同时,程序立法上的缺失,导致农民被排除在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决定和实施的整个程序之外。例如,《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收回时,先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由乡镇主管土地管理的机构接受申请,并将申请报送县级土地主管部门审查,最后由县级政府审批。纵观宅基地使用权回收的整个程序,与宅基地收回制度的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农民,竟然任何一个环节都无法参与。此外,宅基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原则和补偿标准无法律规定;救济手段和救济方式也缺乏明确规定。
五、结语
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法律规定的粗疏和缺位,导致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制度运行极不规范,甚至成为某些地方政府规避较为严格的征地补偿制度的“灰色地带”。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类型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总结城镇化过程中的宅基地收回制度的运行状态,审视宅基地收回制度的缺陷,归纳提炼宅基地收回制度的完善之路。唯有此,才能减少因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引发的社会纠纷和矛盾,保障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维护农民的宅基地权益,为城镇化的推进提供条件。
[责任编辑:王德福]
Subject:The Categories of Mandatory Restoring the Usufruct in Rural Housing Land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ases and Legislation
Author&unit:YANG Lei
(law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100,China)
The most obvious feature of the chinese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s the public ownership but private usufruct. The usufruct in rural housing land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of farmers, but also a matter of the right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for farmers to maintain. The system of mandatory restoring which means the deprivation or restriction of the usufruct in rural housing land is the component of the residential land management system. Mandatory restoring the usufruct in rural housing land can be summarized as public levy, punitive restoring and identity restoring. Because it’s lack of enough attention to this field, some judicial practices and the government actions need legal specification. The research will help to re-examine the existing system of mandatory restoring in rural housing land, and propose practical measures.
urbanization;usufruct in rural housing land; the mechanism of mandatory restoring
2013-12-20
本文系司法部法制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构建和谐社会与优化行政执法环境》(05SFB5005)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我国绿色建筑政策法规体系研究—以山东省为例》(13CFXJ06)以及山东省信息化战略研究专项《山东省电子商务的法律政策体系研究》(2013EI156)的阶段性成果。
杨蕾(1979-),女,山东滨州人,山东大学法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山东建筑大学法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学、宪法学、建筑法学。
D912.1
:A
:1009-8003(2014)02-01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