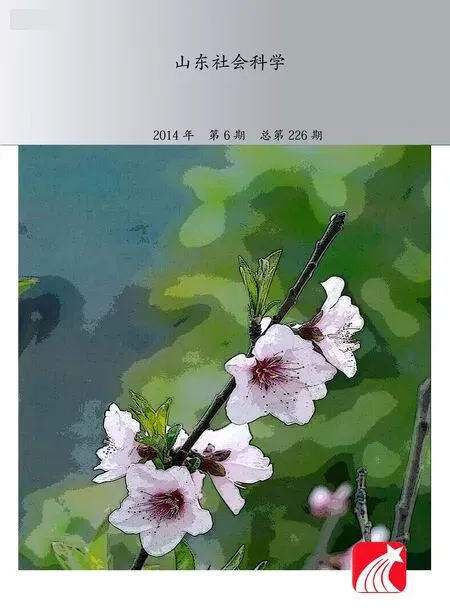论萧红小说信仰缺失状态下对自我和艺术境界的展示
吴竟红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学部汉语进修学院,北京 100083)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的女作家。她以最后十年的生命拼搏,为人们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然后如流星闪过夜空,生命也陨落在她所描绘和展示给人们的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与无垠的时空融聚在一起了。她以《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为代表的小说中有许多悲惨的生活画面,内里蕴聚着作者对生命消亡的怜悯和悲哀。正因为萧红写出了对生与死的悲剧性体验,因此有人视其为悟者。不过,从宗教的视角来看,单单觉得生命本身是一场悲剧,而未找到让生命复苏的药方,只能说是初步的感悟,却不是彻悟。摩罗先生曾在评论《生死场》时说,萧红是以温馨的悲悯之情书写了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生老病死的状态,但这些意象本身所具有的悲惨、寒冷气息带给读者浸入骨髓的寒凉。他认为可能信仰和与之相关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是解决心灵重压的方式之一,而“越是把人生的虚无写到顶点的作家,他离信仰可能就越近”,比如鲁迅和萧红,因为他们至少是达到了为苦难的世界担当情感痛苦的一个作家的精神底线,而“就直接面对人的生存层面说话这个角度来说,萧红比鲁迅走得更远,体验得更深”。[注]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载章海宁主编:《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缺失信仰,但又以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对生命和人生价值的思考距离信仰很近的确是萧红文学世界的宏观环境。这个环境和她所处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科学主义的西方反教浪潮在中国兴起,宗教失去地位。至于基督教,它的所谓‘奇怪’而‘不科学’的神学教义,加之与西方帝国主义不清不楚的关系,使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接受。”到了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关怀的是“寻求抵抗日本和强国之方”,他们认为宗教当不了救国济世的良方。[注]邵玉铭:《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载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6-287页。另外,还有文化遗传的影响,即便像冰心、巴金这样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作家也是在文学创作中建构了一种向“人—人”关系的中国文学传统倾靠的语境,即他们各自“爱”的哲学和“爱人类”的信仰。社会环境和文化遗传因素该是鲁迅、萧红做不到以“人—神”关系消解生命虚无感的主要原因。但是,鲁迅具有极其强大的人格力量,他以坚强的姿态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注]鲁迅:《野草·希望》,载《鲁迅全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页。的美学境界,这个境界虽然让他始终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消解生命的焦虑”[注]徐麟:《鲁迅的生命意志及其人格形式》,载一土编:《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但也强大得足以与温暖的天堂和“恶”的人间分庭抗礼。而萧红是“脆弱的器皿”,她一生渴望爱,期待爱,又缺失爱,其实有着一颗需要宗教之爱的别样的灵魂。
本文意在探讨萧红小说“信仰缺失”的艺术个性:在“以人为本”的范畴中,她对“自我”的展示、她跟中西文化价值的关系、她走向的艺术境界。我们以为,萧红多元复杂的“自我”在她对现实世界的描写过程中作了介入;她建构了悲观主义顺其自然的艺术境界,这个艺术境界取材于“缺失信仰”的人文环境和“接近信仰”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生命情结。
一、自我的展示
(一)动态的自我与传统思想文化的矛盾
在《生死场》中,萧红用她的艺术之笔描绘了芸芸众生的悲惨命运,这些人自生自灭,看不到光明的未来,也未认真思考、探求造成他们生活悲剧的原因,只能茫然地、不停地像动物一样生殖,又像动物一样地死去。不单是《生死场》,还有其他许多小说,萧红在有关生命本体的思考中,都“通过她创造的形象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虚无、绝望意识”[注]秦林芳:《鲁迅小说传统与萧红的小说创作》,载章海宁主编:《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页。。虚无是一种信仰缺失状态下生命的困境,没有信仰支撑的生命自觉者对于生命不觉者和自我的处境都可能心生虚无的感觉。《后花园》中的主人公冯二成子就是萧红小说人物中独特的“这一个”,他发出过“人生意义的怀疑性叩问”[注]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萧红为这叩问提供了“渴求爱”的动因。
孤苦伶仃的磨倌冯二成子爱上了邻居赵姑娘,但谦卑而善良的他压抑住了自己的渴望,只是“偷着对她寄托一种心思”,后来姑娘嫁了人,甚至姑娘的母亲也搬走了,这断了他最后的一点念想。在送别姑娘的母亲回来的路上,他陷入了极度的虚空和失望中,直至趴在一片小树林的地上哭了起来,这时空中响起了心灵的画外音:“这样广茫茫的人间,让他走到哪方面去呢?是谁让人如此,把人生下来,并不领给他一条路子,就不管了。”此后他和寡妇老王的婚姻是彼此的救赎,但后来那救赎过他的妻子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也死了,又回到原点的冯二成子却永远平静下来了,每日照旧在破磨房中打着筛罗,摇着风车。这个追问过生命根据的磨倌代表作者发出了“人”的共性询问的自我,但他“顺其自然”地沉寂下去了,这不是道家的逍遥超脱,而是无路可走的沉默。而从另一个磨倌形象——《呼兰河传》中的冯歪嘴子的故事,我们看出作者仍希望生命负有意义,她尝试以中国传统思想的生命观消解她所感到的生命虚无的境遇。冯歪嘴子和王大姐是打破封建婚姻习俗自由结合的,因而遭到周围人们的歧视。后来王大姐死了,“扔下了两个孩子,一个四五岁,一个刚生下来”。这些人就觉得“冯歪嘴子算完了”,都准备看他的热闹。但是冯歪嘴子“并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的绝望”,“因为他看见了他的两个孩子,他反而镇定下来。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他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他看看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做”;“于是他照常的活在世界上,他照常的负着他那份责任”。这样写,诚然是为了批判那些愚昧的看客,但不也和杜甫诗中那“鬓已苍”或“为鬼”,但儿女却已“成行”[注]杜甫:《赠卫八处士》,转引自胡晓明解读:《唐宋诗一百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的悲中有喜的“希望之感”有共鸣吗?用“生殖”的价值来诠释人生的“希望”,自然是源于写实主义所忠于的人生观察,或许也有着文化传统的无意识沉淀的内因,但却反映了萧红文学世界内部的矛盾性,因为她的小说还有着生殖和女性死亡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母题。
在阶级压迫、恃强凌弱的人性恶和民族压迫的框架中,女性能够受孕的宿命使女性比男性又多了一层生命的恐怖和危险。在《王阿嫂的死》中,拖着沉重身孕在田地劳作的王阿嫂支撑不住,坐下来喘两口气,恶毒的张地主就来踢了她一脚,致使她几天后因早产悲惨地死去。在《生死场》中,因为物质的贫穷和精神生活的贫乏,男女都沉溺在物质和生理的低层次需要中,无休止地追求生理满足,加上贫穷和无知,不断地受孕、生育,女人沉沦在无尽的生育的刑罚中。金枝出嫁后,也同别的村妇一样,“渐渐感到男人是严凉的人类”,丈夫甚至在她产期将至时只顾发泄自己的性欲,让她险些丧命。在文本的后半部,怀孕的村妇面临着更大的死亡恐惧:日本侵略军破开孕妇的肚子去破“红枪会”(义勇军的一种)。即便是《呼兰河传》中婚姻幸福的王大姐,生命力也是因生殖而衰亡的。萧红看待生殖如看待死亡一般的意识跟她个人的痛苦经历有很大关系。纪实散文《弃儿》中怀孕的芹(萧红本人)肚子疼得“在土炕上滚成个泥人”,她“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件从肚皮挤出来,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肠子像被抽断一样。她流着汗,也流着眼泪”。多年以后,萧红又怀着近九个月的身孕,孤身一人逃难,她“在天还没有放亮的码头上,为纵横的绳索所绊倒”,她挣扎不起来,躺在那里,感受到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死亡一般的平静。[注]骆宾基:《萧红小传》节选,载章海宁主编:《萧红印象·记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对于上述叙述,我们诚然可以说,正因为萧红有过自身痛苦的经历,所以才能深刻感受到生命的无助以及人类对生命重生的期望,既写女性生殖之痛或生殖的无意义,又写生殖的意义是萧红小说“两面结合性”的艺术特征的一个例证。但女性肉体的“自我”之痛与中国传统思想“生殖的意义”的矛盾却也无法被否定。倘若不以“生殖的希望”化解生命的虚无感,那就只有借助“死亡”的力量。下面就说说萧红那以“死亡”来裁定人生的独断的“自我”的影响。
萧红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是《小城三月》,临终前她又为骆宾基口述了《红玻璃的故事》,这是两个关于“死亡”的叙事。前者中翠姨的死是“慢性自杀”,后者中王大妈的死带有魔幻的色彩,可以说,萧红是以“违背自然”的处理融进自我的决断——让死亡的意义对生存的意义进行了决断。翠姨因为不愿意嫁给自己不爱的人而病倒,又因为婆家立刻要娶她(迷信病新娘能被“冲”好),“就只盼望赶快死,拼命的糟蹋自己的身体,想死得越快一点儿越好”,结果她终于追寻死神而去。而王大妈本来充满生命力地活着,却突然有一天从她和女儿童年都玩过而外孙女又在玩着的红玻璃花筒中“窥破了命运的奥秘”——玩过红玻璃花筒的两代人都遭遇了丈夫到黑河去挖金子而一去不归的孤独人生,难道第三代也将“逃不出这条可怕的命运的道路吗”?王大妈顿感穷苦、孤独和生活的可怕,于是她活不动了,很快就让自己的生命消殒了。然而王大妈只是活不动了,她并没有对令她绝望的人生进行彻底的否定,她在死前又交代她的儿子王立去黑河挖金子,走那给她带来痛苦的丈夫走的老路,表现了一个灵魂看待人生的两面性。王大妈走向死亡是灵魂的觉悟,而王大妈让儿子去黑河挖金子是生命的理性。即生命的延续是对人生的妥协,王大妈从前并非是妥协,只是还没有走到机缘——那被作者安排的生命道路上的“悟”点。翠姨和王大妈死后的境况是活着的人无从知晓的,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能看到他们坟头的景色。“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的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年青的姑娘们,她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白天黑夜的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这是对翠姨美丽生命陨落的惋惜和悼念。《红玻璃的故事》结尾也说到了祭奠和坟头:“清明节,王大妈坟前出现了纸束。有的说是她闺女来过,但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听见过哭声。”“王大妈的土坟上,生了初生的艾草和狼尾草,而且一天天蓬茂,繁密起来了。”这都是对生命死亡后的境况的描述,并将死亡转化成了对死者的回忆。所以生命不死并非因死去的人本身的信仰,而是活着的人对他/她的追忆。坟上新生的青草这“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意象依然可被理解为萧红小说“两面结合性”特征的一个例证——在书写“人生荒凉感”的同时,也书写对“生”的无限眷恋。[注]参见赵园:《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载章海宁主编:《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但这个植物生长的生命美学意象让人联想到让冯歪嘴子活下去的支柱——他的两个幼小的儿子,可以说这是一种回归的象征,无论是回归到推崇生殖的传统思想伦理这一“偏狭”的路径上去,还是回归到中国文化“道”的生命美学的语境这一“超脱”的境界中去,都显示出萧红进行生命行走时自身的矛盾性和力图解脱中的无奈和挣扎。
(二)“弱”的自我个性中的文化价值意向
虽然萧红遭遇了和传统思想文化矛盾的困境,但是她“肯定自我”的精神却体现了老子哲学“重死而不远徙”思想的现代性阐释——重视生命,不仅要“重视生命之‘形’,更要重视生命之‘神’,即重视‘我’”,“没有了‘我’,生命便失去了意义,也可以说就‘死’了”[注]参见兰喜并:《老子解读》,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1页。。而萧红的“自我”的“灵魂”就在于她对自我“弱”的生命之“神”的认知与尊重。比如在《生死场》中,萧红通过对农民自发的救国行动的刻画抒发了一种“强”的精神,但更以金枝进城及后续的故事表现出对自我生命“弱”的认知。金枝在丈夫死后,选择离开正被日本侵略者祸害着的乡村到都市去谋生。她扮成老相、丑相,又因为摔成了脏污的样子,才在路上逃过被日本兵抓去的一劫,但在都市,她却“为着钱,为着生活”,没有逃过在一个中国坏男人房舍中的一劫。羞恨把她赶回乡村,可母亲只注意她带回的票子,催她早点儿返回城去。金枝决定出家,但到了尼姑庵才知道那儿早因战争空了。萧红因此提出了“金枝走向哪里去?”的问题。其实对于处在左翼文艺阵营中的萧红来说,她所应当接受的观念是:让穷人和受压迫者具有尊严只有走战斗的道路,但是对于有极强的个性意识的人道主义者萧红来说,对金枝的命运设下的悬念反映了超越革命枝条的更高的需要。金枝固然是精神的“弱”的象征,但精神的升华只有通过精神的需要才能实现,金枝承担着对“自身存在”的诘问是在向长远的未来的时空呼唤着一个美好社会的实现,这个社会没有贫穷,有完善的法律并对生命尊重和关爱。萧红不怀疑革命会给女性的生活带来转机,但是她也在写作中没有“失去自己的本然真性”,没有“把‘我’移居到他人和他物之中”,而是立足于了“自己的切身状态”。[注]参见兰喜并:《老子解读》,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1页。
二、悲观主义顺其自然的艺术境界
萧红以其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塑造了受苦难人物的悲凄群像,她的人物都缺失明确的信仰,而萧红一生也并未走进宗教中,寻求到自己的信仰。那么,她所创造的艺术境界要表明什么呢?那就是坚持“人—人”关系的文学天地,并且走向“顺其自然”的境界。萧红小说总体上是悲观地顺其自然,《小城三月》和《红玻璃的故事》反自然的“死亡”主题——让死亡扼杀人生(苦难)及其价值,也是悲观主义“顺其自然”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顺承结局。《小城三月》中的翠姨跟萧红性格上有相似之处,如翠姨病重时对前去探望她的“意中人”——“我”的堂哥哥所说的:“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但是翠姨是一个旧式的女性(没在学堂里念过书),她虽心存意中人,却“自觉的觉得自己的命运不会好”(她因是再嫁的寡妇的女儿而受到过别人的歧视,就想“意中人”大概也是轻看她的),宁愿相信死亡也不相信希望和幻想,和作出逃婚、离家之举的作者本人又有天壤之别。在去世前半年完成这样一个在闺中(受抑)死去的青春人物的刻画,似乎隐约暗示着作者对逃婚、选择漂泊的个人人生的否定。其实作者清楚,对苦难的再认识并不表明就一定能避开人生的苦难,更不是要彻底否定当初对自由的追寻,人生的初期永远意味着自由的尝试,即使走错了,也不会白走,那么,选择“非自然”的死亡又意味着什么?翠姨和王大妈非自然的结果都意味着:有个性的生命在单纯的顺其自然中的不满足。
作者对顺其自然表现出悲观主义的态度,是其“缺失信仰”和“接近信仰”共同造成的矛盾性的表现。“缺失信仰”使其在艺术上走向“顺其自然”的境界,但“接近信仰”所包含的对生命的珍爱和人道主义思想却让她无法从顺其自然中得到满足。萧红虽因人生的境遇向苦难的生命皈依,不能自拔地皈依,这颇像基督教“受苦的上帝”的精神,但是,萧红的小说缺失让生命复苏的朝向,只有“爱”没有“信”,“爱”,就成了“悲哀”。悲观主义的顺其自然与庄子哲学的乐观主义的顺其自然有着一个对比。庄子哲学的乐观主义的顺其自然似乎有着它的“残忍性”,似乎无视时代的生灵涂炭,其实恰恰是在时代的生灵涂炭中悟出来的,是走向了避世求超脱之路。但这种避世的态度是“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
悲观主义的顺其自然的代表作是《呼兰河传》,我们不妨借张爱玲的话来观照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主体自身心灵的文学传统背景:“中国知识阶级这许多年来一直是无神论者”,“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她指的是《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说它们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得到欢悦,譬如“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注]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载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呼兰河传》对于“家”的“荒凉”反复咏叹,最后连那生机盎然的“后花园”也因老主人的死去、小主人的逃荒而“荒凉”,宏观上跟《红楼梦》的虚空悲境是相通的。在“微观”上,《呼兰河传》中主要出现了批判、同情和童心的欢愉三种笔调,萧红着重回忆了故乡人鬼交杂、闲言飞舞的精神世界,故乡人“顺其自然”的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以及作为幼童的“我”在后花园中无拘无束地玩耍,从储藏室搬出各种稀奇物件把玩等童真情态。个人的童心的欢愉没有占据较多的篇幅,文本中更多的是作者对记忆中的人生状态和现象的悲哀审视。第一章中那个屡屡害人的大泥坑是呼兰河“顺其自然”的生活的标志性象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人们任其自然地横在那里不去填平,却在争相购食便宜猪肉时,把瘟猪肉想成是那泥坑子淹死的猪的肉而自欺欺人。但作者也写这些“顺其自然”的人们“四季里,风、霜、雨、雪的过着”,“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被自然的结果“默默的一声不响的”“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这样的文字表明的是萧红个人的主观情绪,而她所批判和同情的对象,对于“生”和“死”,却不会去想,因为想多了徒增痛苦,是给自己的灵魂另找麻烦,他们有着一套套“活着”的程式,只要按程式走就可以了,对生老病死有自己的一套解释,也有与之和平相处的一套方式。萧红幼年时代故乡的居民,就是张爱玲所说的“自满的,保守性的中国人”,他们“超自然的世界是荒芜苍白的”,而“一向视人生为宇宙的中心的”。[注]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载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8页。其所谓的“宗教背景”,不过是根植在民间的民俗和迷信。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也是有声有色的,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逛庙会等“精神盛举”让人眼花缭乱。但作者首先写出了浮于尘世、没有着落、依附迷信的人生迷途中的戚然和惶然。只要跳神的鼓一打起来,男女老幼就都跟着了慌似的跑到请神的人家观看,到半夜时分,“要送神归山了”,大神唱着的词调仿佛是要把人的魂魄一股青烟般地引去那缥缈的野岭荒山。词调混合着有急有慢的鼓声,传向四周的空间,让静夜透着一股凄凉和森冷,也映照出虚空的人生,作者悲叹:“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似,为什么这么悲凉。”反映出萧红对生命沉陷于愚昧之中产生的悲凉感以及她对人生价值的悲哀的思考。放河灯和野台子戏的描绘给人以大场面之感。但盂兰会上的河灯是放给鬼的,让他们都托着个灯去投生,远去的河灯让观看的人们内心产生空虚,不知道它们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为农耕而感谢天地和龙王爷的野台子戏又可能为年轻女性的生命埋下祸根——看戏期间常有有钱的两户人家“指腹为亲”,若日后男家穷了,女方也要嫁过去,否则就说是她“妨”穷的,嫁过去后,婆家又说她嫌贫爱富而虐待她,娘家也让她认命,逼得这类女子往往不是跳井就是上吊。呼兰河的愚昧和野蛮还导演了一出荒唐透顶的惨剧——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遭受婆婆的毒打、火烙、掐拧而受到惊吓,就被婆家认为“身上一定有鬼”而被跳大神摧残(被抬进装满“滚热的热水”的大缸里“洗澡”),众人都当“奇闻盛举”一般好奇地争相观看甚至协助给她“治病”(“浇水的浇水,按头的按头”,“若是断了气”,“就赶快施救”)。小团圆媳妇被烫得生命垂危,不久就死去了。如果说整个叙事过程更多的是对“人类的愚昧”的批判和讥讽,故事的尾声则渗透出对死者极大的同情:传说小团圆媳妇的鬼魂变成了一只很大的白兔,常到冤魂枉鬼聚着的东大桥下哭,说是想要回家,若人说送她回去,她就“拉过自己的大耳朵来,擦擦眼泪,就不见了”,若没有人理她,她就哭到鸡叫天明。这个结尾让读者对小团圆媳妇,对一切在苦痛中无助地哭泣的灵魂生命,对看不到光明之途的作者,都产生某种同情,并另具浓厚的象征意味,即:美好的事物被摧残,甚至毁灭,但在作者的心灵中,她并没有死亡,而是转化为另一种存在形式,去安抚作者甚至是读者悲苦的灵魂。这使我们更加感到,就“接近信仰”来说,萧红的人道主义有着“弱势”和悲观的特色,然而,又有某些昭示着美好希望的亮点。
三、结语
萧红的小说展现了信仰缺失状态下的人生体验,其意识既是受无神论影响的现代性的,也是中国本土传统意识上的。《生死场》让我们看到在文化荒地上生存的人类的困境。他们没有任何文化价值观念,生命在不和谐状态下麻木地死灭着,无法从肉体上升到灵魂的层次。“国民们”自生自灭着,内部在互相侵蚀,整体趋于极度衰弱,直到外力侵入,使其濒临灭顶的屠戮,这“静态的生命”才猛然“摆脱了绕轴自转的运动”,“投入了进化的洪流”。[注]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根源》,转引自[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而《呼兰河传》中的芸芸众生在沿袭人生的老路,并在不可靠的人生境遇中按照生存法则走着精神的老路。萧红的主人公都是贫弱者,在那个旧时代的深渊中挣扎,只有信仰才能消除其不稳靠的生命感的危机。萧红的小说总体上缺失对信仰的观察和体验,就不免被悲观主义所笼罩。但是,她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以巨大的悲悯和同情,描绘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悲惨图画,这是其他作家难以替代的,其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