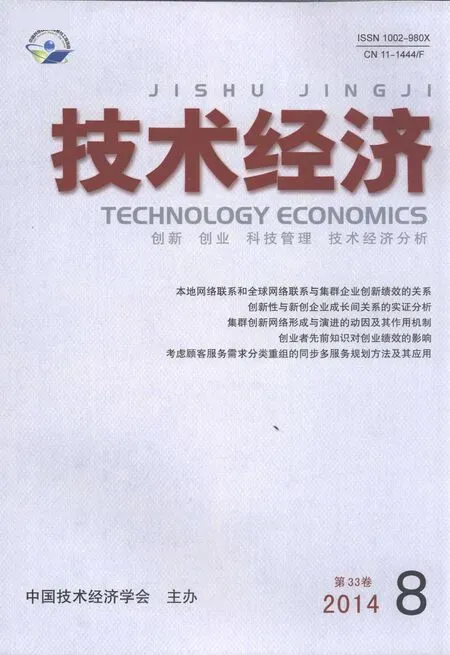本地网络联系和全球网络联系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①
王 雷,池巧珍
(东华大学 旭日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051)
集群企业在积极构建外部网络联系以获取创新资源的同时,还应努力培养和提升吸收能力,以便更好地将外部创新资源转化为自身的创新能力。
1 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集群在全球化经济中表现出的创新优势引起来自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集群创新优势的形成归因于企业空间集聚产生的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下降、信息及基础设施共享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1-2]。基于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强调集群企业网络中的知识流动产生的创新活力[3]。基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认为,在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基础上构建的集群社会网络促进了集群中的创新合作和信息交流,提升了集群整体的创新能力[4]。
飞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技术以及普遍应用的模块化管理方式正使知识创造的世界日趋扁平化,以空间集聚为特征的本地集群网络正逐渐被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网络所取代。国际商务理论认为,地方化企业能否进行新产品开发的关键取决于企业是否与跨国公司构建了有效联系[5]。国际投资理论强调了跨国公司作为联结地方化网络与全球化生产体系的桥梁角色[6]。全球价值链理论则认为嵌入全球化网络是技术后发国家的产业集群获取先进知识、实现技术升级的有效途径[7]。
上述研究强调了以下两类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①本地网络联系(localized network tie),即通过根植于本地的集群企业网络突破自身资源边界,通过网络间的信息共享、知识转移和分工协作等途径提升创新绩效;②全球网络联系(globalized network tie),即通过吸引外资或进入跨国公司的分包体系等嵌入全球化生产网络,并通过全球化网络下的知识溢出、人员流动、产业关联等途径改善创新绩效。前者强调了具有根植性的本地网络在传递隐性知识、促进信息共享、营造创新文化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后者突出了跨国公司在知识转移中的领导者地位及在地方化网络和全球化经济中的桥梁作用。两种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均得到了大量理论及实证研究的支持[2,4],是全球化背景下集群企业创新升级的重要基石。
从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维视角展开的创新研究为集群企业的创新升级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虽然关于本地网络联系和全球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文献已很丰富,但是学者们所得的结论并不一致。第二,现有研究大多从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单一视角展开,缺乏针对两种网络的整合研究。一般认为,本地网络和全球网络具有不同的组织文化和结构特征,需要不同的嵌入方式和资源获取能力,因此囿于资源所限必须对两种网络资源进行权衡选择。然而,近年来有关社会网络及国际商务的研究文献则表明,本地网络与全球网络之间可能存在较为复杂的匹配关系[5],因此仅从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单一视角难以全面、清晰地考察外部网络关系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全球网络联系与本地网络联系间内部匹配关系的重要作用。第三,两种网络联系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尚不清楚,吸收能力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未得到充分重视。
鉴于此,本文将本地网络和全球网络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构建集群企业的双重网络联系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并以跨国公司较为集中的上海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产业集群、苏州IT 业集群、杭州软件业集群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有助于认识本地网络联系、全球网络联系及其匹配关系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指导集群企业通过对两类网络资源进行整合利用来提升学习能力、改善创新绩效。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全球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理论强调跨国公司在国际知识转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嵌入全球化网络可使集群企业突破地方化资源的限制,避免过度依赖本地网络产生的知识粘性和能力刚性,从而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8]。国际商务领域的学者认为,本地企业的创新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能否与跨国公司建立密切联系[5]。Cretanello和Tattara基于所构建的开放式创新模型指出,全球化网络中无处不在的知识溢出有助于本地企业获取国际市场信息和行业先进知识[6]。在全球化网络的框架下,跨国公司不仅对产品质量、配送时间提出具体要求,而且针对生产流程、技术标准和产品设计等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技术扶持,从而对本地供应商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进行长期稳定的生产合作有助于培养内外资企业间的信息分享机制、推动关键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移——此类知识往往是决定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全球网络联系对集群创新的积极影响不断在现有文献中得到印证,如Blalock和Gertler对印度制造业集群的实证研究[9]、Gentile-Ludecke和Giroud 对 于波兰汽车业的实证研究[10]等。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全球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
2.2 本地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根据开放式创新理论,创新活动已突破企业自身的资源边界,更多依赖于与供应商、竞争者、顾客和公共研发机构的交流与合作[11]。本地网络联系显然为企业构建外部联系和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首先,根植于本地的非正式网络有助于企业获取具有粘性的隐性和复杂性知识,而这些知识往往是决定创新成功的关键技术和核心知识[12]。其次,以信任为基础的本地网络增强了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感和认同感,企业间共同的价值观念、产业环境和文化氛围将产生难以复制的知识创造和学习效应[13]。最后,本地网络中信息和基础设施的共享效应将大大降低集群企业进行知识搜寻及创新的成本,这使得网络内部企业可获得网络外部企业难以比拟的创新优势。Saxenian 对美国硅谷高科技企业集群的研究[14]、Asheim 和Isaksen对第三意大利鞋 业集群 的研究[15]以 及Gebreeyesus 和Mohnen 对埃塞俄比亚鞋业集群的实证研究均证明,拥有更多本地商业联系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创新绩效[16]。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本地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
2.3 全球网络联系与本地网络联系的匹配关系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根据战略匹配领域的相关文献[16],匹配关系主要体现为变量间的交互作用或平衡关系。前者反映了变量间的互补关系,即一种行为的实施将强化另一种行为的效果;后者反映了两种行为实施程度的平衡关系,即两者的绝对差异越小则产生的效果越好。虽然当前研究较少关注本地网络联系与全球网络联系的匹配关系,但是部分学者的研究仍有涉及。例如,Glueckler认为,集群中不同企业在能力、社会关系和产业属性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它们的网络嵌入具有多样性,而网络嵌入的多样性导致不同的知识转移效应[17]。通常情况下,本地网络有利于同质性知识的传播,全球网络有利于异质性信息的获取。同质性知识便于企业迅速吸收与应用,从而改善当期的创新收益;异质性知识有利于企业开放新产品或进入新市场,从而确保远期创新收益[18]。因此,同时利用两类网络资源来获取两类知识,有利于形成两类知识的协同互补效应,从而确保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持续提升与改善。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本地网络与全球网络的交互作用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a)。
本地网络和全球网络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知识特征,偏重其中之一而忽视另一个都可能导致集群创新出现结构性风险。一方面,本地企业偏重本地网络联系而忽略全球网络联系,可能阻碍外部创新资源的引入,导致本地知识冗余和能力刚性,从而限制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例如,浙江大量的原生型集群在发展初期虽然构建了成熟的本地网络和置备了完善的配套设施,但是忽略了全球网络联系,导致集群内部的知识结构和技术特征高度趋同,进而导致产品同质化、低价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问题出现,这严重影响了集群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升级潜力。另一方面,如果集群企业偏重全球网络联系而忽略本地网络联系,可能导致跨国公司纵向控制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形成,使本地企业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例如,东莞IT 业集群、苏州IT 业集群均是由外资主导的生产制造业集群。由于外资企业控制了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因此本地企业只能从事加工、装配等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生产制造活动,难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相反,如果集群企业既重视本地网络联系、又积极嵌入全球网络,则既可以避免本地知识冗余导致的能力刚性风险,又可以减弱跨国公司的纵向控制、减弱本地企业低端锁定的发展风险,确保集群企业实现持续的技术升级和价值链攀升。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本地网络与全球网络的平衡关系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b)。
2.4 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吸收能力表现为企业发现、获取、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19]。从企业内部来看,吸收能力与企业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管理能力有关。从企业外部来看,吸收能力与企业嵌入外部网络数量及其所处的网络位置有关[20]。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嵌入的外部网络数量越多、其网络位置越接近于网络中心,则其获取市场信息、关键知识和专利许可的机会越多[21]。本地网络联系强化了集群企业与本地供应商、联盟伙伴、竞争对手及行业协会等网络节点的联系,扩大了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全球网络联系使本地企业可从跨国公司的分包体系中获取国际市场信息和行业前沿知识,并使本地企业不断提升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地位成为可能。显然,本地网络联系和全球网络联系均有助于集群企业吸收能力的提升。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本地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的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4a);
全球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的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4b)。
此外,如前文所述,集群企业从本地网络和全球网络获取的知识在属性上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利用两类网络获取的外部资源并保持对两类网络的嵌入是相对平衡的,有利于实现本地知识与全球知识的协同互补效应,提升企业对两类知识的消化吸收和整合利用能力,最终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由此,我们推断,本地网络与全球网络的匹配关系(交互作用与平衡关系)同样对企业的吸收能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本地网络联系与全球网络联系的交互作用对集群企业的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4c);
本地网络联系与全球网络联系的平衡关系对集群企业的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4d)。
作为影响知识创造和知识利用的关键性动态能力,吸收能力通常被视为重塑企业业务能力、帮助企业适应环境的重要能力[22]。在稳定的环境下,吸收能力强的企业可以更为有效地发展和获取外部知识,拓展原有的技术基础,改善对内部知识的整合能力,并通过提炼与深化既有知识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提高吸收能力有助于企业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寻找和发展现新的技术机会,引入与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技术及产品,或帮助企业用新的方法处理现有问题,迅速改善和提升创新绩效[23]。上述推论得到大量实证结论的支持,如Chen、Lin和Chang以及Liao和Yu对我国台湾地区的高科技企业的实证研究[24-25]、Parra-Requena、Ruiz-Ortega和Garcia-Villaverde对西班牙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的结果均证明,企业的吸收能力对其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6]。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吸收能力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5)。
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本文的概念模型
3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3.1 变量测量
本文主要采用国际学者已使用的成熟量表,并根据预调研中的问题反馈及专家意见对之进行调整,以使最终量表更符合中国情境下的企业运行环境。具体的测量指标见表1。各量表的题项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非常认同”到“非常不认同”分别赋值1~5。
1)本地网络联系和全球网络联系。
延续Nahapiet和Ghoshal的研究,从结构、关系和认知3个维度衡量网络联系的程度[27]。①结构维度。以吴波和李生校的研究[28]为基础,从网络密度和网络强度两个方面设计4个题项测量结构。②关系维度。以Lane、Salk和Lyles等的研究[29]为基础,从信任和理解两个方面设计3个题项测量关系。③认知维度。以Stafford的研究为基础,从文化背景、企业文化和行事方式三个方面设计3个问题来测量[30]。本文分别从本土化和全球化两个视角测量集群企业构建的本地网络联系和全球网络联系,具体的测量指标见表1。
2)本地网络联系与全球网络联系的匹配关系。
采用全球网络联系与本地网络联系的乘积(LNT×GNT)表示两者的交互作用,采用两者的绝对差(|LNT-GNT|)表示其平衡关系。尽管一些学者对“用差值测量匹配关系”的方法提出质疑,但是Tisak和Smith认为:只有当变量量表的信度不足或变量间高度相关时才存在上述问题;如果差值代表的是有意义的构念,那么这种方法是适当的[31]。本文中全球网络联系与本地网络联系的差值具有明确的概念内涵,并且两类网络联系的测量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可采用两者的差值表示其匹配程度。事实上,上述方法已被张婧和段艳玲[32]、He和Wong[33]以 及Hogan、Hogan 和Barrett[34]等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3)吸收能力。
参照Zahra和George的研究[23],从知识的发现、获取、转化和利用4个方面测量吸收能力。
4)创新绩效。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创新投入(如企业R&D 投入经费或R&D 投入经费占企业销售收入比例、科研人员总数或科研人员数占企业员工总数比例等)和创新结果两类指标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35]。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创新绩效的改善程度,因此用创新结果类指标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具体是从盈利性、市场份额、销售业绩和竞争地位4个方面设计题项。
5)控制变量。
本文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政府支持和环境不确定性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用企业成立年限衡量企业年龄;用员工数衡量企业规模;根据专家意见及调研过程中的企业反馈,从财政和信贷两个方面设计题项测量政府支持;从竞争环境、顾客需求和行业技术3个方面设计题项测量环境不确定性。
3.2 样本与数据
本文旨在考察集群环境中的本地网络联系和全球网络联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在选择集群样本时主要考虑以下两点:一是集群具有较成熟的地方化生产网络,上下游企业间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合作关系;二是集群企业嵌入全球网络的特征比较明显,集群企业与国际客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出于对以上两方面的考虑,本文选择上海浦东ICT 产业集群、苏州IT 业集群和杭州软件业集群为研究样本。上述3个产业集群不仅具有成熟的本地网络,而且位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长三角区域:集群中有大量外资企业,本地网络相对成熟,大量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进行互动合作。上述这些使得3个集群都体现了本地网络联系和全球网络联系的发展特征,符合本文对研究样本的要求。关于具体的企业样本,本文选择了主要客户为外资企业的本土制造业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及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
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发放问卷:第一,由各园区管理委员会采取邮寄和面访的方式直接将问卷发放给集群内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第二,依靠上海、苏州和杭州3所重点高校的MBA 学员和EMBA 学员的人脉资源,选择符合要求的企业,采取面访、邮寄或发送Email的方式将问卷发放给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采用上述两种途径共发放问卷800份,实际回收问卷324份,实际有效问卷19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41%。有效问卷的地区分布为上海83 份、苏州65份、杭州48份,分别占有效问卷总数的44.42%、33.24%和24.32%。受访公司的地区分布基本合理,其成立时间大致呈正态分布。70%以上的受访者在企业中居中高级职位,90%的受访者服务于目前企业的时间超过3年,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问卷调研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估计
为避免同一数据来源可能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在问卷调查过程中采用心理隔离法和问卷编排法等程序控制方法以减小被测者的填答偏差、减弱一致性倾向。此外,本文还采用多个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分析,以避免出现严重的同源偏差问题。首先,运用Haman单因素方法进行检验,即对所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如果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的解释力特别大,即可判定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笔者对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未旋转时共析出10个公因子,且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量仅为20.93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问题。其次,运用偏相关分析方法做进一步检验,即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分离出未旋转的第一公因子,再求出控制第一公因子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偏相关系数,如果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偏相关系数仍然显著,则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问题[36]。本文的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第一公因子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偏相关系数仍然显著,因此可忽略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所用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偏差问题。
4.2 信度和效度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1。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见表2。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表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与区分效度
从表1和表2可知:各潜变量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和组合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CR)均大于0.70的临界值,平均萃取变异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均大于0.50 的阀值。可见,所有量表具有足够的测量信度。本文所用量表中的题项源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根据预调研中的问题反匮及专家意见进行了调整,因此整体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此外,各指标的载荷值均大于0.5,KMO 值大于0.7,累积方差解释量大于70%(见表1),说明整体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如表2所示,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总体来看,本文量表具有良好的测量效度。
4.3 假设检验
实证检验分三步进行:首先,检验全球网络联系、本地网络联系及两者的匹配关系(交互作用与平衡关系)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然后,检验吸收能力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后,检验本地网络联系、全球网络联系及两者的匹配关系(交互作用和平衡关系)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第一步,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将4 个控制变量、2个自变量(全球网络联系和本地网络联系)引入模型,从而形成模型1。其回归结果表明:全球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55,P>0.1),因此假设H1未获验证;本地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01,P<0.01),因此假设H2初步获得验证。分别将两种网络的交互作用和平衡关系代入模型1,从而得到模型2和模型3。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作用(β=0.077,P>0.1)和平衡关系(β=-0.056,P>0.1)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均无显著影响。同时将两种网络的交互作用和平衡关系代入模型1,从而得到模型4。模型4的回归结果表明:本地网络联系仍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27,P<0.01),而全球网络联系、本地网络联系与全球网络联系的交互作用和平衡关系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前述的分层回归结果一致。因此,假设H2获得验证,假设H1、H3a和H3b未获验证。
第二步,以创新能力因变量,将4个控制变量和吸收能力变量引入模型,从而得到模型5。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吸收能力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93,P<0.01)。随后,将2个自变量和两种网络的交互作用和平衡关系引入模型5,从而形成模型6。模型6的回归结果表明,吸收能力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81,P<0.01)。因此,假设H5获得验证。
第三步,以吸收能力为因变量,将4个控制变量和2个自变量(全球网络联系和本地网络联系)引入模型,从而得到模型7。模型7的回归结果表明:全球网络联系对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04,P<0.1),因此假设H4a获得验证;本地网络联系对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28,P<0.01),因此假设H4b获得验证。分别将全球网络联系与本地网络联系的交互作用与平衡关系代入模型7,分别得到模型8和模型9。模型8和模型9的回归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作用(β=0.136,P<0.01)和平衡关系(β=0.201,P<0.05)均对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H4c和H4d初步获得验证。将全球网络联系与本地网络联系的交互作用与平衡关系同时引入模型7,从而得到模型10。模型10的回归结果表明,全球网络联系、本地网络联系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和平衡关系对吸收能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前述的分层回归结果一致。因此,假设H4a、H4b、H4c和H4d 均得到验证。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理论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理论模型见图2。

表3 分层回归结果

图2 调整后的理论模型
5 讨论
现有研究缺乏全球化网络和本地化网络的有效整合,忽略了全球网络联系与本地网络联系的匹配关系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全球网络联系和本地网络联系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机理亦不清楚。本文利用来自长三角地区高科技企业的19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在区分全球网络联系与本地网络联系的基础上,以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构建集群企业的双重网络嵌入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关系模型,并选择跨国公司较为集中的上海ICT 产业集群、苏州IT 业集群和杭州软件业集群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本地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全球网络联系对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地网络联系对吸收能力显著的正向影响;本地网络联系与全球网络的联合均衡对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地网络联系与全球网络联系的匹配均衡对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本地网络联系不仅直接促进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改善(直接影响效应为0.427),而且通过影响吸收能力间接改善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间接影响效应为0.400×0.481=0.192)。这表明,吸收能力在本地网络联系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间起部分调节作用。其原因在于:本地网络联系通常建立在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技术基础、知识积累和文化传统的本地企业间,企业间不仅存在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而且各企业形成了以信任和承诺为基础的非正式合作网络,交易成本更低、知识与信息传播更快;同时,相同或类似的知识结构也易于集群企业快速吸收和转化外部知识,从而迅速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未能证明全球网络联系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但全球网络联系对吸收能力的影响以及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均获得了验证。全球网络联系通过影响吸收能力间接改善了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间接影响效应为0.280×0.481=0.135),意味着吸收能力在全球网络联系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完全调节效应。上述实证研究表明,全球网络嵌入虽然不能直接促进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改善,但是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吸收能力而间接改善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
上述研究成果与部分学者关于全球网络联系对本地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直接促进作用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9-10]。考虑到本文选择的研究样本是技术相对落后且处于转型国家的制造业集群,集群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能力、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而这些因素往往成为限制其知识有效转移和创新绩效改善的障碍。虽然全球网络联系为集群企业获取外部知识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是能否有效地识别、消化、吸收和利用来自跨国公司的先进知识和管理经验才是决定外部创新资源能否被转化为企业内部创新绩效的关键。由此可见,集群企业在积极构建全球网络联系以获取创新资源的同时,还应努力培养和提升吸收能力,以便更好地将外部创新资源转化为自身的创新能力。
本文的实证研究还表明,本地网络联系与全球网络联系的交互作用和平衡关系均可通过吸收能力间接改善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这意味着增加两种网络联系的总效应,并保持两类网络联系的相对维持平衡,均有助于提高集群企业的吸收能力,进而改善其创新绩效。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集群企业构建的外部网络联系越多,则获取市场信息、关键知识和专利许可的机会也越多,从而有助于提升集群企业的吸收能力,并间接改善其创新绩效。另一方面,由于本地网络和全球网络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知识特征,如果过度偏重其中一类网络联系,而忽略了另一类网络联系,则有可能导致集群创新的结构性风险,因此,如果集群企业保持两类网络联系的相对平衡,则有利于集群企业同时吸收和利用来自于本地网络和全球网络的知识,既可以避免本地知识冗余导致的能力刚性风险,又可以减弱跨国公司的纵向控制风险,确保集群企业实现持续的技术升级和价值链攀升。
因此,集群企业不仅仅要利用本地网络联系弥补创新资源相对匮乏的先天缺陷,更应通过联合开发新产品、合作开拓新市场等强化全球网络联系,整合利用两类网络资源来获取外部知识,为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持续提升奠定基础。
本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不同的网络嵌入方式(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和不同的产业类型(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可能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本文仅以长三角地区的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展开研究可能有失偏颇,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实证研究可能获得不一样的结果;第二,集群企业嵌入外部网络的不同时间期限可能导致不同的知识转移效果,从而对创新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的截面数据采集方式有失偏颇。
[1]AHARONSON B S,BAUM J A,FELDMAN M P.Desperately seeking spillovers?Increasing returns,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new entrants in geographic and technological space[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7,16(3):89-130.
[2]ROSENTHAL S S,STRANGE W C.Geography,industrial organization,and agglomeration[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3,85(7):377-393.
[3]TALLMAN S,PHENE A.Leveraging knowledge across geographic boundari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7,18(5):252-260.
[4]BELL G G,ZAHEER A.Geography,networks,and knowledge flow[J].Organization Science,2007,18(3):955-972.
[5]HERVAS-OLIVER J L,ALBORS-GARRIGOS J.Local knowledge domains and the role of MNE affiliates in bridging and complementing a cluster′s knowledge[J].Entrepreneurship &Regional Development,2008,20(6):581-598.
[6]CRESTANELLO P,TATTARA G.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the Romania-Veneto network in footwear and clothing[J].Regional Studies,2011,45(2):187-203.
[7]HALLIN C,HOLM U,SHARMA D D.Embeddedness of innovation receivers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effects on business performance[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s,2011,20(3):362-373.
[8]GEREFFI G,HUMPHREY J,STURGEON T.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5,12(1):78-104.
[9]BLALOCK G,GERTLER P J.Welfare gain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rough technology transfer to local supplier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8,74(2):402-421.
[10]GENTILE-LUDECKE S,GIROUD A.Knowledge transfer from TNCs and upgrading of domestic firms:the polish automotive sector[J].World Development,2012,40(4):798-807.
[11]ASHEIM B,GERTLER M S.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2]BABA Y,WALSH J P.Embeddedness,social epistemology and breakthrough innovation:the ca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atins[J].Research Policy,2010,39(4):511-522.
[13]Xu G N,Liu X F,Zhou Y.Effects of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 empirical study in China[J].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2012,6(1):108-123.
[14]SAXENIAN A.Regional Advantage: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342-245.
[15]ASHEIM B T,ISAKSEN A.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the integration of local'sticky'and global'ubiquitous'knowledge[J].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2,27(8):77-86.
[16]GEBREEYESUS M,MOHNEN P.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embeddedness in networks:evidence from the ethiopian footwear cluster[J].World Development,2013,41(1):302-316.
[17]GLUECKLER J.Knowledge,networks and space:connectivity and the problem of non-interactive learning[J].Regional Studies,2013,47(6):880-894
[18]MARIN A,BELL M.The local global integration of MNC subsidiaries and their technological behavior:Argentina in the late 1990s[J].Research Policy,2010,39(7):919-931
[19]COHEN W M,LEVINTHAL D A.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1):128-152.
[20]BURT S.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122-123
[21]LIU H,KE W L,WEI K K,et al.The impact of IT capabilities on firm performance:the mediating role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supply chain agility[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13,54(3):1452-1462
[22]ZAHRA S A,GEORGE G.Absorptive capacity:a review,reconceptualization,and extens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2):185-203.
[23]LICHTENTHALER U.Is open innovation a field of study or a communication barrier to theory development?A contribution to the current debate[J].Technovation,2011a,31(2):138-139.
[24]CHEN Y S,LIN M J J,CHANG C H.The positive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learning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industrial market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9,38(2):152-158
[25]LIAO T J,YU C M J.The impact of local linkages,international linkages,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innovation for foreign firms operating in an emerging economy[J].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3,38(6):809-827
[26]PARRA-REQUENA G,RUIZ-ORTEGA M J,GARCIA-VILLAVERDE P M.Social capital and effective innovation in industrial districts:dual effe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J].Industry and Innovation,2013,20(2):157-179
[27]NAHAPIET J,GHOSHAL 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2):242-266
[28]吴波,李生校.全球价值链嵌入是否阻碍了发展中国家集群企业的功能升级[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27(8):60-68
[29]LANE P J,SALK J E,LYLES M A.Absorptive capacity,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12):1139-1161
[30]STAFFORD E R.Using co-operative strategies to make alliances work[J].Long Range Planning,1994,27(3):64-74
[31]TISAK J,SMITH C S.Defending and extending difference score methods[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4,20(3):675-682
[32]张婧,段艳玲.市场导向均衡对制造型企业产品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0(12):119-130.
[33]HE Z L L,WONG P K.Exploration vs.exploitation:an empirical test of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J].Organizational Science,2004,15(4):481-494
[34]HOGAN J,BARRETT P,HOGAN R.Personality measurement,faking and Employment Selection[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7,92(5):1270-1285
[35]YANG J.Knowledge intergration and innovation secturing new product advantage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J].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05,16(11):12-135
[36]PODSAKOFF P M,MACKENZIE S B,LEE J Y,et al.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3,88(5):87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