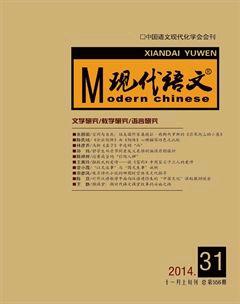先秦审美精神演变
摘 要:《诗经》《楚辞》作为中国诗歌最早的两部诗歌总集,不仅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源头,从它们的发展变化中也可追溯中国诗歌早期审美精神的演变。两部总集都善以“象”传意,但两部总集的“象”又有着明显区别,从这种区别中我们不难跟踪到先秦审美精神的演变轨迹,以及对后代文学发展趋势的影响。
关键词:诗经 楚辞 意象 审美
“古诗之妙,专求意象”[1],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楚辞》开始,诗歌的美就与“象”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中“人”的因素的发展变化正是研究文学创作演变的重要依据,所以,从对《诗经》和《楚辞》中“象”的研究可以看到先秦个体意识发展的轨迹。《大雅》《小雅》是《诗经》中创作主体表现最显明的一组诗歌,《九章》是屈原人生各个阶段的反映,因此这两组诗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创作手法上都能代表《诗经》与《楚辞》的特点,对它们的研读尤其能发掘出这两部作品中个体意识的具体表现。一、从物象到意象中国审美精神虽然要追溯到《易》,但真正体现到诗歌创作和欣赏的要数《诗经》和《楚辞》,只是这两部诗歌总集对“象”的体现不同。《大雅》《小雅》中有很多重复出现的“象”,却表达出不同含义。《九章》中不同的“象”寓意指向则常常归于一致。“四牡”作为“象”在大、小雅中出现在十二篇作品中,分别是《小雅·四牡》《小雅·采薇》《小雅·杕杜》《小雅·六月》《小雅·车攻》《小雅·吉日》《小雅·节南山》《小雅·北山》《大雅·桑柔》《大雅·崧高》《大雅·烝民》《大雅·韩奕》。《小雅·六月》中“四牡骙骙”[2]“四牡修广”“四牡既佶”与《小雅·四牡》中“四牡騑騑”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中的“四牡”雄壮威武,后者中的“四牡”疲惫不堪。而在这十多首诗中“四牡”的含义并不固定,甚至在一些诗中根本没有具体的意义,只是起到引出诗歌主题的作用,它必须上下文结合在一起才能表现诗歌的情感倾向。类似的情况还有“北山”“松”。《小雅·北山》中“北山”与诗歌怨刺王事繁重几乎没有直接的关联,这里“北山”仅仅起到引出下文的作用。《小雅·南山有台》中,“北山”不过起到与“南山”形成对举的效果,它所起到的赞美君子美德的作用是与下文“有莱”“有杨”等具体的物象结合而产生的,因此单独来看“北山”这个物象并没有特殊的含义。“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主要有两种寓意:孤傲高洁、长寿,如李白《古风(其十二)》“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3]整首诗以松柏为喻,上下文配合明澈地表达了诗人对孤傲自守境界的追求,此诗中“象”与“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但上述这两种意思在大、小雅中都没有出现。《小雅·頍弁》“茑与女萝,施于松柏”这里的“松柏”与“女萝”相对,用一种依附关系来表达主人对客人的欢迎和渴望。《小雅·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以松柏之茂喻兄弟相处之亲密。这样的“象”在《诗经》中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到其含义的模糊性和随意性,从某种角度来说很难把他们称为“意象”,只是起到了为“意象”的出现打下基础的作用。在这种模糊性和随意性的“象”向具有较为固定的含义的过渡过程中也有一些“象”具有一定的独特含义。“白驹”一词在中国文学中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喻贤才,二是喻时光易逝,前一含义就出现在《诗经》中。《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郑玄笺:“刺其不能留贤也。”由此,后代的诗歌中就有“感时歌《蟋蟀》,思贤咏《白驹》”(曹摅《思友人诗》)[4]的诗句。在《庄子》之后诗歌中“白驹”一词喻时光易逝这个含义运用的数量和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显然更加明显,如杜甫《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5]就表达了人生短暂的感慨。由此可见《诗经》中的“象”即便有相对固定的含义,但也没有达到后代“意象”的表达作用。《楚辞》“香草美人”的意象已成为无需赘言的文学特征,这个特征在《九章》中自然也不例外地体现出来。《惜诵》“梼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原春日以为糗芳”[6],《悲回风》“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茝幽而独芳”中的香草就是这种创作手法的典型代表,与《离骚》的香草意象一起构成中国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橘颂》独以橘的“深固难徙,更一志兮”来表达诗人坚贞不移的品格。虽然含义与“香草美人”不同,但手法却是完全一致的。以此来论,《楚辞》中的“象”才是“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7]的“象”,才能真正称为“意象”。意象由于有着明确的象征性,这就使在文学作品中的“象”常常有着较为固定的寓意,例如诗歌中出现“月”时绝大数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诗歌的主题理解为思念亲人,而《小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显然没有思念这层含义。所以《诗经》的时代“意象”没有形成,运用于诗中的只是“物象”。但《楚辞》中的“象”其象征性的特点就非常明显了,因此我们也就公认从屈原开始“意象”已经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产生。从“物象”到“意象”其实就是符号化的过程。所谓“符号化”,一方面,是指思维赋予外界对象以形式与概念,使对象比在纯粹的自然中更容易被认识。另一方面,是指人的活动不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的刺激,而是主动地摄取,二者的结合就是符号化过程。在符号化过程中,诗歌中“象”的运用从自发逐渐过渡到了自觉,也就是说从中可以体现出诗人主动将外在的物象内化的过程。中国文学中诗人主体意识发展的轨迹正好可以从《诗经》到《楚辞》看到。二、从阶层到个体说到“自觉”,余英时说:“惟自觉云者,区别人己之谓也,人己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愈强。”[8]关于中国古典文学自觉的起始时代,虽铃木虎雄首倡“曹丕的时代”说后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但学界仍然存在众多不同看法,例如“始于汉代、始于先秦、始于《诗经》”说。二雅中很多诗用到了第一人称代词,表达了创作目的或出现了创作者,如“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複我邦家”(《小雅·我行其野》)、“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大雅·熏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郑玄《诗谱序》云:“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而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这成为了一些研究者认为《诗经》的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证据,似乎这体现了“人的主题”。虽然得出的结论不同,但学界对于“自觉”与“人”的关系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其区别在于“人”在其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不同。认为文学自觉早于魏晋的观点都将文学自觉与文学作品是否体现“人的主题”联系起来,认为只要体现“人的主题”的文学作品就能认定为“文的自觉”。这里至少有两个较明显的困难需要解决: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文学”一词与今天“文学”的概念完全不同,概念尚且没有形成何来“自觉”之说?此其一;其二,如何理解“人的主题”,是不是只要带有人的感情的作品就算自觉?关于这一点《诗序》说得很清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感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它渗透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里而不是一部分作品里,所以这也不能作为文学自觉的依据。“人的主题”不仅仅是有“人”的活动、“人”的情感就能得以体现,它应该有“人”对自己独立性的肯定,就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人己对立”,而这点从二雅的“象”中很难看到。二雅中的“象”既然还处于模糊性和随意性中,这本身说明这些诗的创作者并没有非常鲜明的主体意识,不能认识到事物的独特性,并把这种独特性用诗歌的方式表达出来。以《小雅·我行其野》为例,这是一首弃妇诗,以“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开头,接着表达了渴望回娘家开始自己新的生活的强烈愿望。这里的“樗”只是用到了它的茂盛,并没有把它的特点与诗歌的主题结合起来,而茂盛这个特征用其他的树也可以替代,不是樗的特性。对物的特性不能深入认识其实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对人自身特性的认识的不足,也就是说个体性和阶层性没有明显划分,对阶层的认可超过对自我主体的认可。而到战国末期对人自身独立性的认识逐渐强化,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屈原的作品就能作为典型的代表。屈原在他的诗作中就常常出现“第一人称”。《涉江》一诗“余”字出现9次,“吾”字出现8次。当然并不是只有第一人称代词的出现才能突显诗人的自我意识,“第一人称视角”也是屈原诗歌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如《哀郢》全诗从作者视角出发描写了郢都沦陷的情景,并抒发了作为爱国诗人心中的激愤之情。正是因为如此,在读屈原诗歌的时候我们总能清晰地看到诗人的形象,明确地感受到诗人的悲喜,这正是因为其诗作突出了诗人的自我形象,这本身就是自我意识强化的一种表现。这种自我意识虽然并没有达到超越阶层的高度,但相对于早期的文学作品,能够直接让诗人自己站出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情感仍然是自我主体意识得到认可的初期显现。对自我独特性的认可是不是就是对自我主体性的认可呢?这也要视情况而定。《九章》中的诗人通过“香草美人”“橘”等意象表达自身与时人的不合,但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诗人是把自己放在统治阶层来表达这种思想,其不合只是与昏愦不明的统治者的不合,其独特性没有超越阶层,只是阶层的代言。所以《楚辞》的时代也不可能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但从《诗经》到《楚辞》,由集体咏唱到个人的内心独白已经可以向我们展示诗歌中主题精神发展的脉络,以及它们对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提供的可能性。注释:[1]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2]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中《诗经》作品均引自本书,不再加注。[3][5]见《全唐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76页,第2562页。[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50页。[6]董楚平:《楚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中《楚辞》作品均引自本书,不再加注。[7]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页。[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任在喻 贵州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56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