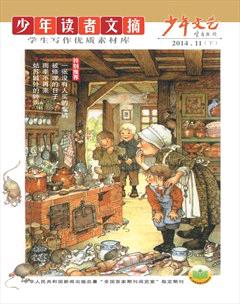被修理的日子
彭建生



一
我倒了霉,被敬爱的班主任修理了。她罚我读报课的时候到厕所搞卫生。
走廊很窄,热风吹拂,倍感炎热。我取下太阳帽来扇扇风。我得在这条靠近厕所的走廊里呆十五分钟,读报课完了才能获解放。
我不停地看表。一旦你被人修理,时间就过得特别慢。我真不知道,一个人在牢里呆十年八年,那日子是怎么熬的!我已经被修理4天啦,这几天来,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看那个戴眼镜的女孩如何躲过“敌人”的封锁线。读报铃响过5分钟,她来了,她是我们同年级楼上那个班的,我们班环境区是男生厕所,她们班环境区是女生厕所。她们要是被修理了,很显然,就得打扫女生厕所。不过看来她运气相当不错,在我被罚的这几天,她天天迟到,从没被抓住。她总是铃响后才出现在学校小食堂后门,进门前左顾右盼,侦察一番,然后沿着大樟树下面那个斜坡,鬼鬼祟祟地迂回到教学大楼侧翼,躲开教学大楼正前方的王胡子——被他或者随便哪个政教处的老师抓住都是要扣分的——看得出她是一个老手,她猫着腰,躲在冬青树丛后面,等王胡子一转身便迅速穿过走廊,好像是地下党过封锁线。
她那一副眼镜,使她看起来一脸正气。我不由得笑出声来。她绷着脸,凶恶地瞪我。我可不在乎别人朝我瞪眼睛吹胡子,我又不认识她,只要能在被修理的日子里找个乐子,咧开大嘴傻笑一阵我就觉得挺好。她是那种初看不怎么样,仔细看能给她多打几分,再仔细点,简直就是很不错的姑娘。
从她出现到消失一共3分钟,这3分钟我很快活,乐完了我就重新变得苦恼,我又想起了班主任的批评。“看我怎么修理你,”班主任是个方下巴女青年,“你是不是要处分才心甘?很危险呀,知不知道?你必须悬崖勒马!”听到这里我以为自己还有救,她可能要放我一码。但是空想破灭了,她决定罚我扫厕所两周:“第一次搞不好,罚3天,第二次罚一周,第三次,你就得扫一个学期。”
这个决定很受班上同学欢迎,他们并没笑出声来,不过我敢肯定他们心里一定乐开了花,他们巴不得我扫一个学期呢,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做值日了。想到自己已经走到悬崖边上,我就很害怕,也很忧虑。班主任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我只能努力改造自己。我认识到老师是为我好才修理我的,我下定决心把厕所卫生搞好,让班主任看了满心喜欢,不到两周就把我提前解放。
可是一到厕所,我的心就凉了半截,自我改造的理想立刻化为泡影。现在正是所谓“秋剥皮”的日子,半个月来都是烈日当头,厕所散发出浓烈的尿臊气,还有的人不自觉,趁人不备就在厕所旁的草地上拉尿,简直要把你鼻子臭得麻木。
我从没注意过学校的厕所竟有这么臭,一看到这情景我只得修改自己的“改造”方案。我觉得做人好难,做了“坏人”以后做好人更难,你要么一开始就是好人。想到自己目前的尴尬境地,我就有了办法。我打算前面10天根本就不去打扫卫生,这样有两个后果:一个是卫生委员很负责,天天都去告状,在班主任面前进谗言,这是最坏的结果——我就要扫一个学期;二是卫生委员不负责,她是女的,不方便去男厕所,每次都要请一个男生代劳,很是麻烦,也就马马虎虎,等到十来天挨过去,最后那几天我才好好搞,结果会在老师心目中留下好印象……
二
今天是星期四,是全校唱歌的日子,她照例又迟到了。可她照例又躲过了政教处的王胡子,她运气真好啊,我几乎怀疑是不是王胡子故意装做没看见她。我正这样想着,却远远地看见她拿着扫把从教室里冲出来,她的班主任大声说:“你这个人,叫作屡教不改!”她不答话,拖着扫把怒火冲天,一阵风冲进女厕所,可是不一会儿,她就逃了出来,大口大口地做着深呼吸,好像煤气中毒一样。这下我可乐坏了,她朝我瞪一眼,你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我说,味道不错吧。她说,是不错,怎么样?我真是乐坏了,我想,这下你的好运气到头了,我有点儿幸灾乐祸,她的火气更使我笑破了肚皮,她也被我的笑逗乐了。
“真倒霉,”她说,“政教处又没抓住我,我又没让班级扣分,他火什么火,还修理我!”
我说,你才不倒霉呢,倒霉的你没看见。我班10多个男生都从橘园里摘来橘子吃,吃得肚子泛酸水,果皮扔得满教室都是,可他们谁都没事。等到我取出橘子,还没把皮剥完,就被班主任抓住了,加上我爱出风头,给自己剃了一个光头。结果呢,数罪并罚,写一千字的检讨。
“一千,那么多,你怎么完得成?”
“一千算什么,我从幼儿园就开始写,一万字都不成问题。”
“语文老师肯定蛮喜欢你喽?”“才不呢,他说我故意增加他的工作量,王婆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我们聊了几句,她说:“难怪,天天看你在这里站岗。今天你扫完了?”我说:“当然完成任务了。”看她那样子好像准备重新加入战斗,我说:“算了吧,你还没尝够那味道是不是?你们卫生委员是男的还是女的?”她说:“男的。”我说:“那就好了。”我把我的经验传授给她,我说:“你费什么劲,反正他们又不能进去看。”
她说:“学校扣我班的分怎么办?”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说,那也得看运气,不过天气这么热,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往这里面跑呢?
“蛮对。”她对此表示赞同,我很高兴。这是我花4天时间研究出来的成果,得到赏识,当然高兴喽。我还告诉她,以后迟到就用不着躲躲闪闪了,要知道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养成了这种坏习惯,有损自己的光辉形象。再说反正已经到了这一步,连厕所都扫了,你还怕什么呢?干脆大大方方地走到王胡子面前去,让他扣几分,把你们班主任气得七窍生烟。她笑眯眯地看着我,对我的建议好像很满意。
三
“真倒霉,我不该信你的话,”第二天星期五,她对我说。“他说,他本来只想要我扫两三天,没想到我敢跟他斗气,现在要我永远扫下去了,都怪你,都怪你,”她说,“都怪你出的馊点子。我现在是越来越倒霉了。”
“你太天真了,”我说,“这只不过是他们要修理你的借口罢了,他们修理了你,心里多少有点儿过意不去,就要找出你更多的错误——那你就去扫吧,你进去呀。”
“去就去,难道我还怕那点臭气不成。”可是她却没有动。
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扫厕所就扫厕所,反正我们又不是真的去扫。这样更好,我们不要上读报课,读报课简直闷死人,根本不读报,只有老师在上面唠叨,唠叨得你只想睡觉,电风扇吹的都是热风,里面那么多人,空气哪有外面好?他们不要我们进去,我们还不想进去呢。再说现在又不是正式上课,我们也没有损失一点儿知识。我们的时间一点儿也没有浪费,我们在享受自由呢。”
“照你的意思,这倒是十全十美的喽。中学生守则第十条说有错就改,又没有规定要我们扫厕所。”她说。
“说得好,”我说,“这说明什么呢?很显然,这说明他们也不对,这是他们的土政策。可是他们对也好,不对也好,我们照样要来扫厕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有修理人的权利。”
“那我们给校长写信,检举他们吧?”
“悟性差,”我说,“全校都在干同样的事。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修理方法,甚至包括罚钱。罚钱可以代替其他的修理方法,要是你身上老是有钱的话,你违反纪律就不用扫厕所。你以为校长不知道吗?你以为他会来管这些事吗?”
“那我们是没得救了?你是说他根本不会来管这事?”她说。
“你开始觉醒了,”我说,“一旦他们定出这样那样的规矩,总有一些人要倒霉,不是你就会是别人。这是我被修理后得出的结论。”我像发表演讲一样滔滔不绝,对自己的口才十分得意,我大谈自己的苦难史,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难的天才,我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啊。我,全班公认的最有才能的人,一个17岁的男子汉,在我那个怀才不遇的爸爸的教导下,甚至读过罗素的《西欧哲学史》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喜爱并熟悉19世纪俄国文学,学识不可谓不广博,但是仅仅由于剃了一个光头,摘吃了一个橘子,就落得个扫厕所的下场,是的,扫厕所的天才,命运对我是多么不公正啊!
“我就是老迟到,我也不是故意迟到的,”她气愤地说,她向我诉说了种种令人同情的原因,可是班主任就是不听她的,“每次他都说,‘我不听你的理由,反正迟到就是不对,就是给班集体脸上抹黑!”
酒逢知己千杯少,1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有点儿恋恋不舍。“没关系,”她说,“还有明天呢。”我们各自拖起扫把走了。
四
又是星期四了,全校在唱歌,这一周里我们聊个没完。现在呢,差不多什么话都说完了,都有点儿说老话了,她闷闷不乐。说实话我对这种生活也有点儿烦,不管怎么说,被人修理总不是什么好事。我没话找话,说,“看样子你是蛮喜欢唱歌喽?你最崇拜的偶像是谁?”
“唱歌我倒是喜欢,只不过,”她说,“我才不崇拜什么偶像呢。”
“那么你崇拜谁?”
“为什么我一定要崇拜别人呢?他是他,我是我。”
“那你是崇拜自己喽,你这个自大狂。”
“自己有什么好崇拜的,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天天扫厕所,”她说,“你不觉得这事有点档次太低了吗?你不觉得烦躁吗?就好像自己是一个另类似的。”
“你想上档次喽。”我说。
“我是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她忧愁地说,“你呢,也差不多。”
“没关系。”我说,“我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我不是说这样还自由一些吗?”
可是她并没有听我讲,她还是很苦恼:“我受不了啦,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怎么结束。”
是呀,我应该想到她是一个女孩子,根本没有我这样坚强,经不起生活的波折。我说,“那你去写检讨吧:‘老师,我再也不迟到了,你看我的实际行动吧。要不,你就干脆交钱了事吧,他要多少给多少。”
“他要是还不同意呢?”她今天很悲观,总是把问题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说,“那就只有这样两个办法了,一是等厕所臭得不行了,只好把我们撤下,换那些认真负责的干部来搞卫生;二是我们在这里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他们觉得让我们俩呆在一起很危险,也会把我们另做安排。”
“那我们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我们来谈谈恋爱吧,”我说,“保管叫他们魂飞天外。”
她的脸红得很快:“你要死了,光头!”
“对不起,”我连忙说,“对不起,我说着玩的,噢,连这个玩笑都不能开了?”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谈到了理想,她说:“我要做一个政治家。”她说得很突然,把我吓了一跳,不由得仔细打量起她来,她的样子很严肃,“我要做一个讲原则的政治家,把他们都管得服服帖帖。”
五
第二天她没有来,她再也没有来过。谈恋爱那个玩笑开得有点儿过火,我为自己说错了那句话深感后悔,不过也许是她已经交了罚金,或者老师认为已修理得差不多了,她解放了。
日子真难熬呀,特别是你一个人呆着,没人跟你说话的时候。幸运的是,班主任总算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两周期满,她就安排了别人来接替我。这个接替我的也是一个倒霉的人,他和别人打架,害得班上被扣了整整10分。
我们班的同学又快快活活地笑了一回,当然,轮不到自己值日,无需到厕所去领略那浓烈的臊气,自然令人高兴——除非他虚伪。我也很高兴,虽然我是一个刚被修理的人,本该抱有同情之心,可是我却偏偏没有。真的,一点儿也没有,真是人心险恶呀!我也不例外。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周期满,下一个候选人是谁。不过话又说回来,被人修理,固然不是什么好事,可是凡事都要一分为二,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能够被修理,也是一种运气,我是那么怀念那些被修理的日子啊!有时候我心情激动,抄了几首诗准备送给她,以示纪念。我们在漫长的被修理的生涯中结下了浓厚的友谊,分手了怎么可以没有任何表示呢?当然,这种行为很可能引起别人的误解,可是这并不违反中学生守则啊,但我还是很害怕,可是我可以保证自己的动机是纯洁的。等诗抄好了,我才发现我不知道她叫什么。直到很久以后的元旦演讲比赛那天,我才知道她叫什么。她的演讲很精彩,演讲题目是《我要做一个讲原则的人》。她像政治家那样挥舞着手臂,结果得了一等奖。
看来她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她正在为做一个政治家而努力呢。
我们偶尔遇见了,我点点头,她也点点头,算是那段交情的延续,动作幅度极小,生怕别人发现。不过四下无人之时,她叫我:“嗨,光头!”我也说:“嗨,你啊。”顶多就这样。
(摘自《盛夏光华》,少年儿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