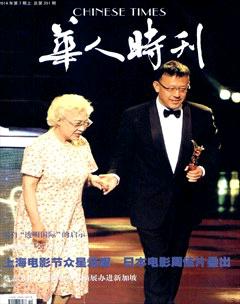落马贪官炙手可热与“腐败文化”
邹燕秋
近年来,中国反腐败成效令人瞩目,一些怪现象也令人困惑。
新华社2013年2月16日报道:2006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11年的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于近日提前出狱,当地官员、煤老板及名流富商争相迎接,鲜花簇拥,甚至准备鸣放礼炮;侯伍杰回家后门庭若市,其礼遇如英雄凯旋。
一高官儿子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四处碰壁,郁郁寡欢。他到狱中探视父亲并诉苦。父亲说:这事好办,我给你写个条子。儿子说,你已经不在位了,而且当前这种窘境,你写条子还好使吗?父亲说:“放心了,当然好使。如今我身陷囹圄,虽然没有提拔他们的权力,却有让他们下台的能力。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父亲说罢,狡黠而又意味深长地望着儿子。片刻工夫,儿子转忧为喜,恍然大悟地点头离去……果然,儿子顺利到组织部上班。
对上述案例作一管窥,不难发现:如今贪腐往往不再只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一个集体的、体制的、机制的问题!
窝案频发,腐败联盟
早在2007年,广西检察机关在广西民政系统挖出以厅长张廷登为首的贪污贿赂窝案、串案65件80人,其中厅级干部3人,处级干部14人,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这场“官场地震”数量之大、涉案人员之多全国罕见。
更为罕见的,是两位副厅长截然不同的态度:A副厅长在专案组到来后如释重负,不但将多年来厅长主持分配且分文未动的涉案钱物悉数上交,而且将所知的腐败问题和盘托出;B副厅长却死猪不怕开水烫,拒不交待问题,且为民政系统的贪腐问题百般狡辩。
案子最终告破。可是在民政系统,人们对A副厅长非常不屑,而且埋怨A副厅长供述腐败问题导致民政系统职工福利锐减,甚至称其为“软骨头”、“叛徒”;对B副厅长抗拒抵赖行径大加赞赏,称其为“硬骨头”、“硬汉子”。人们到监狱看望张廷登厅长和B副厅长者众,而看望A副厅长者寡!
无独有偶。被查300万元受贿问题、主动交代1亿元的呼市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被判死缓。侦查机关从马俊飞位于呼和浩特和北京的住宅中,查获的现金包括人民币8800万元、美元419万元、欧元30万元、英镑2万元、港币27万元和黄金43.3公斤。金条、美元、欧元、价值不菲的收藏品堆满了两所房子!
媒体报道说,自2009年8月被任命为副局长后,马俊飞最头痛的一件事便是藏钱!马俊飞曾向办案人员说:有人拎着里面放着百万元的皮箱,直接就放到办公室。不收,就会被人视为异己;收了,就“上了贼船下不来”。办案人员不解地问马俊飞:“这么多钱放在那里,不消费,也不退赃,为什么?”他说:刚开始还有侥幸心理,后来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了。这么多钱,不消费是为了将来轻判一些;不退赃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退,也无法退还。
于是,在办案机关只掌握了300万元受贿线索的情况下,他一股脑儿地交代了一亿元的赃款和赃物,自我感觉解脱了!
人们从中不难明白,腐败为何常以窝案、大案的形态出现:你不腐败,同类官员不放心啊;你腐败了,其他官员才会将你视为同类,才会同进退,你才能得到提拔。否则,就像马俊飞说的那样:不干,一辈子注定默默无闻。
官员腐败的圈子,有时候真是水泼不进、针扎不进。这个同盟体往往是随核心人物的倒台而瓦解的,也是靠突破像A副厅长和马俊飞这样的内部薄弱环节而破解的。如果腐败联盟固若金汤,普通干部职工甚至纪检机关也恐难破获。腐败联盟中偶有不慎落马者,只要不揭发不坦白,便会收到“丢卒保车”的作用,那些潜伏的贪官们怎不感恩戴德,千里迢迢赴监狱看望落马者?怎不处心积虑营救、为落马者搞缓刑减刑呢?怎不绞尽脑汁地照顾其子女呢?这种特殊的腐败利益共同体彼此间心照不宣、配合默契,明显成为反腐败斗争中的羁绊与掣肘。
“腐败文化”令人堪忧
无论是入狱贪官志得意满地安排儿子就业,还是出狱贪官享受凯旋式礼遇,无不折射当代“腐败文化”之重。
腐败在一些地方之所以泛滥,原因之一就在于腐败在社会中被视为“正常”,他们的行为甚至受到同辈、家族和朋友强有力的支持和称赞。恰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谬尔达尔所指出的:在那里形成了一种“腐败的民俗学”,它“容易使人们认为,掌握权力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或他觉得应当忠于的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这意味着,腐败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文化”。由于“腐败文化”的蔓延,它又成为腐败赖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催生着新的腐败分子,使得反腐败斗争面临着严峻挑战。当前“腐败文化”在社会意识中虽然不占主导,但它有着广泛的社会性,同时还具有极强的诱导性,易致上行下效,进而败坏社会风气。
据笔者长期观察分析,“腐败文化”主要表现为:
思想认识上的“腐败文化”。一是“容忍腐败”:有人认为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就要容忍腐败的存在,甚至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某些群众公开说,干部贪不贪没关系,只要给我们带来实惠或使当地经济发展起来就行;二是“羡慕腐败”:能够找关系、上门行贿、买官卖官、包揽项目,往往被人称为“有能力”、“有门路”、“有眼光”。那些贪官和不法商人一旦马失前蹄、落入法网,则被人说是“后台不硬”、“赶上他倒霉”,总之“笑廉不笑贪”。在这种氛围中,原本清正廉洁者不仅受到孤立、排挤和打击,而且可能被毒化;三是“期望腐败”:常听一些人说,“我们无职无权,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啊”,内心深处有一种“腐败”的期望;四是“攀比腐败”:现在见面打招呼有了新的“时代特征”,问“昨晚没有找到你,你到哪儿腐败去了”,答“到某某某腐败去了”;问:“你这东西真不错,从哪儿腐败得来的”,答“是某某腐败给的”。腐败竟然成了一种时尚,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体制层面上的“腐败文化”。制度设计不健全的地方,容易出现体制内腐败。如一些人利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法律制度不健全,钻体制的空子,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一些人利用干部考察任用制度上的漏洞,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拉帮结派。由于这些行为具有普遍性和公开性,往往不被视为腐败行为。一些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蜕变成了谋取小团体利益的工具。在群体性腐败中,你腐败,他腐败,我也腐败,大家都腐败,法不责众。其内部轻则形成心照不宣、互相照顾的松散“合作”,重则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分享腐败所得。这种“腐败文化”使得腐败现象在—个群体内上行下效,好比森林火灾成片成片地蔓延。
行为方式上的“腐败文化”。“腐败文化”渗透到日常行为方式中,比如“吃公不吃私”成为一些人的共识,有些商品销售公款的价格高,个人的价格低。一些地方接待住则高档酒店,喝则高档名酒,还陪客人游山玩水、逛街购物,开销则由公款负担。腐败的行为文化还形成不良的“官际关系”:一些下级很怕上级,对领导唯唯诺诺,实际是怕影响自己的升迁和既得利益,导致下级对上级人身依附;有的则以老乡、同学等名义聚合,形成小团体。官官相护、互相利用、相互包庇是小团体主义的表现,阻碍反腐败工作开展。部分领导干部讲究迎来送往,热衷于灯红酒绿,经不住金钱、美女等诱惑,与行贿者形成畸形人际关系。
在“腐败文化”影响下,一些地方和一部分领导干部反腐败羞羞达达、半遮半掩,甚至出现拥戴和保护贪官的怪现象。山西出现“当地官商列队欢迎贪官刑满出狱回家”的怪事情,其实岂只是山西?
“腐败文化”还使腐败成为某些人“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惯例”,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对腐败现象“习以为常”、不加问责的非正常现象。“腐败文化”的孳生和蔓延,造成人们的是非标准颠倒、价值取向扭曲,把不正常的视为正常,把正常的视为不正常,让腐败有立足之地和生长空间,增加了反腐败斗争的难度。
如何铲除“腐败文化”
在开展权力反腐的同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将反腐败延伸到反腐败文化的高度,大力开展文化反腐、制度反腐,用廉政文化占领人们的思想阵地,根除“腐败文化”产生的土壤。一是要把握廉政文化的导向性,努力唱响“主旋律”,使廉政文化建设从“文件”走向“文化”;二是要把握廉政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利用现代新型传媒,使廉政文化的辐射范围从“有限”走向“无限”;三是要把握廉政文化的传承性,发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活廉政文化由“历史”走进“现代”。
不就文化抓文化,致力于将“文化”这种社会权力的“软约束”与“制度”这种国家权力的“硬约束”有机结合,努力奠定、夯实廉政文化的制度性基础,形成对公共权力监督制约的有效机制,消除“腐败文化”产生的空间。
中国有句谚语:“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构建合理惩戒文化,提高惩处腐败力度,降低腐败容忍度并对腐败行为进行严惩和威慑,有利于建立廉政制度的强约束力,培育个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引导行为主体在廉洁和腐败的考量中做出正确的抉择,使人“想贪而不敢”。“腐败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是人们模仿“成功者”的一个不断加长的链条。要打断这个链条,关键是铲除“成功者”,使这些“成功者”变成警戒人们的反面典型。
以“廉政文化”的正能量,抵御“腐败文化”的蔓延态势。当代中国,网络反腐败相当成功,北京市纪委一位副书记坦陈,目前网络举报80%属实。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大宣传力度,扬善与惩恶相结合,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利用媒体加强舆论监督,形成全民监督网络,对腐败现象掀起群起而攻的舆论态势。(责编 张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