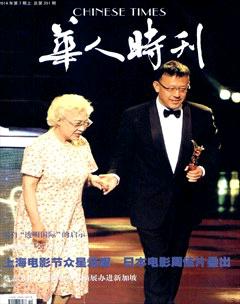青年公务员的心路独舞
袁浩
几百人拼搏对战只为一个岗位,前几年公务员考试的盛况还历历在目。不过,今年一些公务员私下将简历投给猎头机构,加入了跳槽大军。在杭州某猎头公司负责人方垚的人才库里,今年出现了不少公务员的身影。“都比较年轻,年龄在30岁到35岁之间,普通科员。”方垚说,“教育背景都非常不错。毕业于名校,学历很高,研究生居多。”
今年春节过后,关于公务员跳槽和裸辞转行的事例在微博和微信上屡见不鲜。国内不少媒体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职场的新动向。为何出现这样的逆向流动局面?公务员的生存现状如何?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实例,来寻得答案。
梦想篇:永远对峙的现实
2008年11月的某一个冬日,我从坐满了面试官的房间退出来,抬头看见挂在灰色天空中鸡蛋黄的太阳。这一个稀松平常的冬日,将成为我人生的一个拐点。在这之前,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我内心里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因为跟孩子们打交道,环境单纯,工作也清闲。可是职业不能等同于爱好,更不能等同于一张长期饭票,我在深刻感受了合同教师和编制教师待遇的巨大差异、进编又无望的情况下,开始四处寻找新工作。
相比毕业后闲赋在家几年的同学,我是幸运的。在知道我被录取为公务员的那一刻,我的父母比我要激动许多。
在机关上班的两年里,我已完成和环境彼此纠结的全过程。现在,我和我的公务员生活就像结婚多年的老夫老妻,无甚大激情,但是它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缺少它。
我在日记里这样记载:“对于现在坐办公室的生活,我还在严重适应当中。虽然以前在学校也要求坐班,可那时候的办公室大得我们常常在里面扭秧歌、做健身操,你还可以去班上溜一圈再回来。而现在,且不说地方大小,我们工作的性质本身就很严肃,你要是在办公室扭个秧歌蹦个操,敢情当事人来了,会立刻傻眼……”感叹完毕,我也有了把办公室所有的铅笔头都纹身的壮举。
七点起床,八点上班,十一点半在食堂吃饭,中午办公室午休,下午五点半下班回家,日子就在这“五加二”(五个步骤,两个半天)中悄然流逝,呆板而乏味。我心中陡生悲怆之情:我的青春,我的人生,难道就在这永远的“五加二”中度过吗?
回家乡工作一年后,我有了辞职的想法,在家里引起轩然大波。父亲哼出一串“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母亲也冷冷地丢出了一句:你出去可以,但是你可以干什么?
理想和现实永远在对峙。我开始责怪自己为什么当初要回来,过这种“波澜不惊”的公务员生活。我甚至打电话给远在上海的儿时好友。她在电话那头带着一腔侬语软调,哧哧笑着说:“你羡慕我什么?我羡慕你才是呢,工作稳定,在父母身边,不愁吃穿。我虽在大都市,但一切事情都得自己打点,身边说话的人都没有,工资高也买不起房……”
我牢骚满腹的时候,周围的人就开始训斥我:典型的身在福中不知福!作为一个女孩子,足够啦!剩下的,就是找个好男人嫁掉……
今年休年假的时候,我重回以前任职的学校,重温一遍老师“办公室———教室———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我突然庆幸自己离开了这个环境。我发现离开才两年,我已不再是以前的我,而他们依旧是他们。
我似乎已经完成了从老师到公务员的转变,但内心不安生,时常纠结。我依偎着公务员生活,看着围城外熙熙攘攘想要冲进来的人们,想到了报刊上的一句话:中国国考热透露出中国人已经在求稳,这对于前进中的中国并不是件好事。
怎么样生活,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我想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公务员,也许你在另外的舞台上能够舞得更好。要么尘埃落定,要么远走高飞,你自己选择吧!
爱情篇:给她介绍对象的人太多
我的女朋友研究生毕业,她找工作时就瞄准了公务员。她前后考了七八次,有几次考了第一,但面试时被淘汰。最后在一个事业单位考试时考了第一,并通过面试,得以进入公务员队伍。
我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来到了女友所在的小城市。我以为能在这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结果是悲剧的:“你的学历太高了,我们的工作专科生就可以。”
女朋友刚进单位时工资就2000元出头,过了半年左右加了200元,一年后又加了300元。原因是她硕士毕业,一年后转正,成为副科级干部。
我的女友刚进单位时很闲,一是不熟悉业务,二是单位事不多,和当时拿的工资比确实不对称。但是下半年调动部门后,她忙得甚至都不想干了。因为科长什么事都不做,基本把所有工作都安排给了她。所以,有人说公务员上班就是看报喝茶,其实那是老员工或领导做的事,新人没那么清闲。
在我女友的单位里,男同志的妻子往往都很漂亮、很时尚,女士的老公98%都是公务员或在事业单位,工作、生活有保障。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女生成为公务员后,往往会产生优越感,工作稳定、有地位、福利待遇好等等。所以,有好多女生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后,往往会和原来的男朋友分手,除非她的男朋友很厉害,能养得起她。我的好几个女同学进入事业单位后,就和相恋五年以上的男友分手,并以不到半年的时间和单位同事介绍的一些大龄男闪婚。
我的女友成为公务员后,不下十个人给她介绍对象,对方都是公务员或在事业单位工作,有车有房。我为了女友来到这个小城市,拿着可怜的工资,还经常受到别人的威胁,这是很难受的。我也和女友说:“我们分手。我去大城市发展,你也可以找个家庭条件好的,没有买车买房的压力。”可女友觉着我为她付出太多,没同意。
好了,就说这么多。我希望公务员队伍里,能多出几个像我女友那样的人。
西部篇:遥远的中产之梦
大学毕业后,我响应团中央的号召,孤身一人来到了陌生的新疆,成了一名大学生志愿者。2010年5月,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过关斩将,最后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录取。我不知道别的公务员怎样,就说说自己吧。
我工作快半年了还没有套工资,师里先按一个月1800元预发。那套完工资得多少呢?据我调查,也就2200元左右。你会说这在新疆不少了,那给我个解释的机会。
首先这2200元是我每月的所有收入,包括阳光工资在内所有税后所得;第二,大家认为贫困的地方挣钱少、消费也低,可在新疆这种说法不成立。我们经常吃的拌面12元一份,我最喜欢的肉夹馍在老家山东卖1.5元一个,在这里4元一个,牛肉的5元,可怜我一顿要吃两个才能饱,再要一碗粉丝汤,吃顿饱饭至少要10元;衣服基本不打折,打折的很多还是假的,像买到“康帅博方便面”、“营养专线”、“可日可乐”,我已经见怪不怪。
现在父母岁数慢慢大了,需要儿女照顾。可他们都在山东老家,我一年也难得回家一次看看他们。想把他们接过来,又没有房子住。即使有房子住,这儿的气候他们未必能适应。
为了一天省下两块钱,我一般都是跑步上下班。虽说跑步比较费鞋,但我算过,还是比坐公交车划得来,只是跑步上班中午要多吃一个肉夹馍……虽然大学时《西方经济学》我能考九十多分,但这个经济账我实在算不太明白。
我想,即使转正后工资涨到2500元,可又有什么变化呢?不过只要我不失业,我和父母就不会受冻挨饿,我就有机会翻盘,将来发展成为中产阶级(给自己画张大饼)。
乡镇篇:只有工作,没有下班
2010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选调到国家级贫困地区重庆市武隆县江口镇工作。刚到单位时,我被临时安排在党政办打下手,复印材料、送取文件、分发报纸……那时我觉得堂堂一名研究生,竟要做这些小事,简直就是大材小用!
一天下班后,郁闷至极的我决心第二天就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经过一个晚上的思考后,我放弃了当“逃兵”的念头。是啊,逃避不是办法,知难而上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熬过艰难而又枯燥的一周,出差回来的领导决定让我先去组织办学习锻炼一段时间。
到组织办后,我才发现基层工作并不是想象中的那回事。我不仅要负责党建资料的收集工作,还要为“三项活动”编印各类工作简报,为领导起草讲话报告,撰写总结经验材料,对外进行党建宣传报道等。尤其是第八届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启动后,我作为选举指导组工作人员,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往往是一项任务还没有完成,新的任务早就布置下来。
在基层,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记得第一次加班时,组织委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基层没有下班的说法,只有做完(工作)的说法。”
第六次人口普查开始后,我们镇政府工作人员全被“拉壮丁”去当普查员。幸运的是,我普查的区域离镇政府很近,任务也相对较少,只有136户。苦恼的是,作为一个讲普通话的外地人,我常面临被拒之门外的尴尬。
一次,当我敲门自报家门时,房主隔着门说:“你是骗子吧?电视上早就报道了。现在很多外地人趁人口普查来骗人呢!”我普查的区域流动人口较多,白天普查找不到几个人。无奈之下,我和另一位同志将两人的普查任务合并,他前面“开路”,我后面登记;白天找不到人,我们就晚上登门拜访……到最后全镇人口普查数据汇总时,只剩下一天多的时间,我们几个年轻人硬是熬了一个通宵才完成任务。
在基层工作,除了常规性工作之外,我还得兼做一些简单而又枯燥的工作,比如手工誊抄党员档案(800多份)、经常电话联系村干部(最多时一次40多人)、每月收发党刊杂志(近千份)等。
在简单重复的日常工作中,我逐渐提高了办事能力,学会了人际交往,增强了综合素质。我撰写的材料还被重庆党建网、中国当红网以及《公民导刊》等媒体采用。在和基层群众的频繁接触中,我渐渐地学会了当地的方言。
我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让人记住的成绩,但我尽力了。
结语:正如硬币的两面一样
在今年全国已发布招录公告的23个省区市中,16个省份报名人数下降,其中15个省份出现招录、报名人数“双降”局面。很多人认为,公考“降温”意味着人们对公务员这一职业的认识已经呈现出理性回归,特别是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和公务员管理日趋严格的情况下,“公务员不好当”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一些对公务员岗位抱有幻想的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谨慎三思,甚至望而却步。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公考“降温”的重要推手。
客观地讲,公考“降温”值得我们为之欣喜。长期以来,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公考热”高烧不退,一些本来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大展身手的年轻人,一些本来搞学术研究非常有天赋的优秀人才,都一心想去政府部门,想去做官,造成了人才浪费和人才流失的隐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身居中国多年,他评论中国的“公考热”时说:“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都挤着想去做公务员,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我们希望看到聪明的年轻人对妈妈说:‘妈,我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开公司了。”如今公考“降温”,公务员的形象观瞻正在被逐步剥去“神秘”面纱、褪去耀眼“光环”。公务员报名人数下降传递的正是这种信息,这对政府和群众都是一个良好的信号。
正如硬币的两面一样,公考“降温”也有值得忧虑的一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如何,至关重要。尤其在当下打造服务型政府,更需要一支优秀的公务员队伍。公考“降温”固然有矫正价值取向、转变择业观念的倒逼与引领作用,同时也传递出一些人生观、价值观错位的信息。如果年轻一代都抱着一种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公务员这一职业———公务员职业吃香,就挤破头想进来;公务员回归平淡,就黯然神伤想退出,这恐怕不是一种好现象,更非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基层公务员、特别是青年公务员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经过调研,已经着手制定改善措施,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呼唤人们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即便公务员这一职业将来再平淡,也得创造条件、创新机制,吸引一批有志于精忠报国、为民服务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责编 张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