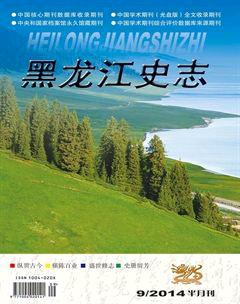民国时期北京使馆区历史简述
李潜虞
[摘 要]北京使馆区在民国时期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1-1941年),在这一阶段列强驻华使馆成立了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统一管理使馆区。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七七事变”后建立的华北傀儡政权对此均予以承认。第二阶段(1941-1945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北京使馆区并控制了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1943年,日本又将北京使馆区“交还”给中国,而实际上使馆区仍为日军所控制。第三阶段(1945-1949年),抗战胜利后,北京使馆区被正式收回,但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工作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外国驻华使馆;不平等条约;修约外交
引言
外国驻华使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开始逐步在北京建立起来的。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位于东交民巷的各国驻华使馆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攻打。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十一个西方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大清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1]从此,北京使馆区成为一个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
以往有关北京使馆区的研究多集中于晚清时期,对于民国之后北京使馆区的历史却鲜有研究。本文将主要依据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史料并结合已公开出版的历史文献对民国时期北京使馆区的管理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从而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一、第一阶段(1912-1941)
《辛丑条约》签订后,北京使馆区的管理一直由《辛丑条约》缔约国驻华使节开会来商定。从1901年到1911年的十年间,使馆区一直没有统一的管理。当时,整个使馆区分为东区、西区和英国使馆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公共事务管理方式都不尽相同。各国驻华使节于1911年5月27日召开会议,首次讨论对使馆区实行统一管理的问题。经过多次争论之后,各国驻华使馆终于在1912年制定了对使馆区进行统一管理的相关章程。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组建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The 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 of the Diplomatic Quarter,以下简称公署),并于1914年1月1日正式成立。
公署由5名代表组成,其中3人由《辛丑条约》缔约国驻华使节指定,而另外两人由使馆区的居民选举产生。这5名代表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公署的行动通过投票的方式以简单多数决定。公署主席必须由《辛丑条约》缔约国驻华使节指定的3名代表中产生。公署的一切行动必须受到《辛丑条约》缔约国驻华使节的控制和认可。公署还可以任命一名财务官员和一些负责道路、警察事务的官员,并有权雇用和任命一些人员从事警察和道路维护等方面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公署设立一个常任秘书办公室,并指定一名官员担任常任秘书,常任秘书不能从公署的5名代表中产生。这名常任秘书就成为北京使馆区日常事务的实际管理者。[2]
对于使馆区成立这样一个类似于政府的机构,北京政府立刻予以承认并表示欢迎。1914年1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函内务部通报了公署成立的消息以及人员构成的情况。外交部在函中明确指出:“若将来凡使馆界内事务由该署与警厅及北京市地方官直接来往,则与速办事件殊有裨益。兹各国大臣嘱代为陈明,应请转行地方官一体知照。”内务部接函后立刻将此函作为命令下达给京师警察厅。京师警察厅又将此情况通知了各区警队。[3]实际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辛丑条约》缔约国分属敌对的两方,而中国又参加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公署从1919年才开始真正管理使馆区。也就是说在北京政府承认公署的时候,公署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运作。北京政府之所以这样急于承认公署,其根本原因是袁世凯为了获得列强对中华民国的承认,采取了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政策。袁世凯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正式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明确承诺:“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4]而这里所说的条约自然包括《辛丑条约》在内。3个月后,公署成立,北京政府立刻予以承认并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1926年下半年,奉系军阀逐渐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奉系军阀在对外政策带有明显的反苏倾向。1927年4月,发生了著名的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事件,而这一事件并不表明北京政府已经收回了使馆区,实际上,奉系军阀的行动得到了西方列强的认可。搜查苏联使馆的具体行动方式奉系军阀已经事先与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商定。4月6日,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奉命率军警300余人至使馆区,称使馆界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党人暴动机关,事机迫切,立即搜查,请予准可等,经荷兰驻华公使签署后,即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区搜查,拘捕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5人,逮捕李大钊等革命党人30余人,劫走大量文件。然而,西方国家虽然乐见奉系军阀的反苏行动,但他们决不会放弃在北京使馆区的特权。就在事件发生仅3个月后,曾代表西方国家出面准许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的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京师警察厅现在派侦探到使馆区访查,他受各国公使的委托,要求京师警察厅立即将所派侦探撤回。外交部于7月26日将函件转京师警察厅。7月29日,京师警察厅命令侦缉处查明有无此事回报。7月30日,侦缉处复文表示并无此类情形。[5]这都表明西方国家准许军警进入使馆区只是出于反苏的需要,而并不想改变使馆区“国中之国”的特殊法律地位。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积极开展修约外交。在修约外交的大背景下,北平市政府曾一度准备收回北京使馆区,但计划最终胎死腹中。1929年1月,北平市政府草拟了《筹拟收回使馆界行政权案》。这份文件草案明确指出:“现值中央政府与各国修订新约之时,对于北平使馆界行政权似应早日收归市政,以期根本解决。”文件提出致函外交部分别进行交涉。文件表示,虽然“中央交涉结局未可预定”,但“该界内之治安、道路、交通、卫生等行政亦宜筹备办法,一面备政府之参考,一面作收回之准绳”。[6]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就倒向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外交政策上体现出明显的亲美反苏倾向。收回北京使馆区的动议也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京,但公署仍然继续对北京使馆区进行管理,而日本扶持的华北地区伪政权对管理工作给予了配合。
综上所述,进入民国后,列强驻京使馆为了便于对使馆区进行管理,成立了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华北傀儡政权都承认这种状况。使馆区“国中之国”的法律地位与晚清时期一般无二。
二、第二阶段(1941-1945)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北京市使馆区已经发生了不详的变化。1940年11月30日,汪伪政权、伪满洲国和日本发表了《日“满”华共同宣言》,表示“三国要互为善邻、紧密提携”。[7]伪满洲国驻汪伪政权的“外交代表”于1941年10月间表示除在南京开设大使馆外,伪满洲国还要在北京开设大使馆,在天津和济南开设领事馆。1941年12月4日,伪北京市警察局局长余晋和发布训令,表示按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命令,准许伪满洲国在北京开设大使馆。[8]而这时距珍珠港事件爆发只有几天时间了。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日军就控制北京使馆区。日军进占使馆区之后,又完全掌握了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在1942年4月22日公署发出的一份公函中可以看到,一名名叫藤井又一的日本人担任了公署署长。公署原来的英文印鉴也改成了日文的印鉴。[9]
1943年,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开始实行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其中包括所谓“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等内容,企图以此来掩盖沦陷区的殖民地本质。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向英、美“宣战”,同一天,日、汪还签订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协定》第五条规定:“日本国政府应承认中华民国迅速收回北京公使馆区域行政。”[10]同年3月22日,日本又与汪伪政权在南京签订了《关于收回北京使馆界之实施细目》,《细目》规定“承认中华民国于本年3月30日收回使馆界行政权”。就在3月30日当天,伪北京市市长刘玉书向日本致公开信,表示对日本政府的行动“至为感佩”。北京使馆区还有一些空余土地被称为“隙地”,刘玉书在公开信中表示,将按照符合日本利益的方式来使用这些“隙地”。当天,伪北京市政府还制定了《北京使馆区隙地使用方法》,其中第一条就是“为纪念中国参战及大东亚建设,与德国方面交涉,利用旧奥国兵营旧址东北一角,建设纪念碑,使之为本隙地之中心。”这个办法还规定划出一块土地由伪北京市公署使用,而“实际上则充为日本军使用,日本军以外人员,暂时使用时,应联络日本军后,由市公署许可之”。办法还规定,从前门至崇文门的城墙“暂由日本军使用”。[11]
除此之外,伪北京市教育局还要求北京的中学生到使馆区去参加种植花木的活动,美其名曰“勤劳奉公”。1944年7月,伪北京市教育局在训令中表示“吾国自参战以来,迭蒙盟邦协助,各地租界次第返还,本市东交民巷之使馆界亦早收回。兹为垂久纪念起见,爰于旧使馆界四周辟为花园。……查勤劳奉公为学生之天职,暑假期间藉之锻炼体格,更富有意义”。训令明确规定了从7月12日至27日,每天到使馆区参加劳动的学校名称和学生人数。在此期间,有27所中学的2100名中学生到使馆区进行所谓的“勤劳奉公”。[12]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太平洋战争后,北京使馆区实际上被日本军队所控制,所谓的“交还”完全是一纸空文。
三、第三阶段(1945-1949)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参加反法西斯同盟,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1943年1月,重庆国民政府与美国和英国签订了关于取消外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收回租界和使馆区的新约。以中美新约为例,条约规定:“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协助中华民国政府与其他有关政府成立必要之协定,将北平使馆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之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华民国政府。”条约同时规定:“在北平使馆界内已划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土地,其上建有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房屋,中华民国政府允许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为公务上之目的有继续使用之权。”[13]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公布了《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其主要内容是:主管机关接收各租界或北平使馆界时,应将公有资产区分为三类:一,原为租界或北平使馆界为公有者;二,原为同盟国或中立国之政府所有者;三,原为敌国政府所有者。对于第一类资产,应点明清册,对照物品之数量及其状况先行接管。其债权债务关系留待清理委员会清理。对于第二类资产,应予证明属实后准其继续保有。对于第三类资产,应由主管市政府接管,缮造清册,呈报行政院核办。凡属于敌国使馆之财产,应由外交部派员会同市政府接收。办法还特别规定:北平使馆界内同盟国原有之使馆土地及房屋应按中美中英等新约规定,准其继续使用,由各邦国政府派员接收。办法还规定每一租界或北平使馆界接受完毕后,由政府组织一清理委员会,审查并确定各块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内应行移转于中国政府之官有资产及官有义务债务,并厘定关于担任并履行此项官有义务及债务之办法,呈候行政院核准施行。[14]
根据这一办法的规定,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同时在11月24日公布了《租界及使馆界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组织规程》,其主要内容是:“各清理委员会的职责包括:1,审查并确定各租界及使馆界内应行移转于中国政府之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与债务;2,协助接收机关接收租界、使馆界内之官有资产;3,拟定如何担任并履行官有义务债务之具体办法,呈请行政院核准施行。各清理委员会各设主任委员一人,综理会务,由当地市长担任。各清理委员会设委员五人至七人。由行政院指派法律专家及熟悉租界使馆界之人员充任之。主任秘书一人,承主任委员之命处理日常会务。各清理委员会应于成立后一年以内将各项工作办理完竣。各清理委员会遇有不能解决之事项,应即呈请行政院核示办理。”[15]
1946年7月,北平使馆界官有资产及官有债务义务清理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市长熊斌(后为何思源)任主任委员。[16]这样,国民党政府接收北京使馆区的法律和组织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自清理委员会成立到1947年12月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北平市政府各部门及清理委员会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清理委员会确定了到底什么是北平使馆区的官有资产、官有义务和债务。官有资产是指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所有及保管的一切资产,包括动产、不动产、流动资产、设备及使馆界广场,这些资产都进行绘图和清点造册的工作。官有义务是指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所行使之公共职务,包括治安、消防、卫生和公务四项。这些义务现在已经由中国政府履行,以后应继续由中国政府履行。官有债务是指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所欠的债务。[17]由此可见,所谓使馆界的官有资产、官有义务和债务都与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有关。
其次,北平市政府各部门开始恢复使馆区的市政工程建设,收回使馆区的公用设施。1946年12月至次年7月,北平市工务局制定了整修使馆区道路的计划,并对使馆区内的树木、桥梁、水井等进行了统一的接收,还提出了使馆区的改建计划。[18]1947年6月至7月,北平市卫生局也接收了使馆区的公共厕所,并制定了整修启用计划。[19]
第三,有限度地清理使馆区中西方列强留下的有辱中国国体的痕迹。在英国使馆围墙的东北角墙壁上,有义和团运动时期留下的枪弹损坏痕迹30余处,英国使馆在其上用蓝油漆写了“Last We Forgot”(永志不忘)的字样,而且字迹清晰,清理委员会员认为“有碍新好”,通知英国使馆予以清除。另外,在德国使馆院内有遗留下来的铜炮两门,清理委员会通知工务局将这些铜炮转移到位于故宫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工务局于1948年5月搬移完成。但是,这种清除工作也很不彻底。在英国使馆门前有两座石碑,分别记载了义和团攻打英国使馆的日期和在义和团运动中死亡的英国人的姓名。清理委员会认为石碑上只有日期和人名,并无其他文字,因此允许英国使馆将石碑移至馆内保存。在意大利兵营和德国使馆也各有石碑两座,意大利兵营的两座石碑记载的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阵亡士兵的姓名。德国使馆的两座石碑均记载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中德国人死亡的日期和时间。清理委员会及北平市工务局认为“碑文纯系为纪念性质,并无轻侮我国文字”。意大利兵营被接管,因此允许将石碑移至使馆内保存,德国使馆石碑仍置原处。[20]
应该说,当时的北平市政府为收回使馆区做了一些工作,但这些工作不可能非常彻底。收回使馆区后,北平市政府也就使馆区做了一些规划,这些规划是美好的,然而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在内战连连败绩,彻底收回改造使馆区的历史责任显然已经不能由国民党政府来完成了。
结语
使馆制度是一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外交制度,它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一制度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北京使馆区的形成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是中国屈辱外交的象征。进入民国以后,北京使馆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北京使馆区不同的情况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中国在1911至1949年期间的兴衰荣辱和国际地位的变化,民国时期重大的外交政策在北京使馆区的管理工作上都有所体现,北京使馆区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民国外交史。
参考文献:
[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长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06页。
[2]Robert More Duncan, Peiping Municipality and the Diplomatic Quart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Peiyang Press Ltd, 1933)pp.104-107.
[3]《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关于使馆界内设立事务公署的公函》,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181-018-03488。
[4]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一九一一——一九一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5]《外交部关于查明和欧使函送京师警察厅请撤回使馆界内侦探一事的函》,北京档案馆档案,档号:J181-018-21066。
[6]《北平特别市政府关拟收回使馆界行政权及军人纪幕天经使馆界被阻拦的来函》,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001-007-00013。
[7]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
[8]《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准在北京等地开设满洲大使馆及领事馆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181-022-12764。
[9]《北京特别市卫生局管理使馆界公署请淘挖沟池的来函及工务局关于市长交下德国大使馆函请填平德国墓地水沟并迁移石碑情况的报告以及市政府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017-001-02597。
[10]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第197页。
[11]《北京公使馆区域隙地使用方法》,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001-002-00753。
[12]《北京市教育局关于派学生前往东交民巷“勤劳奉公”给大同、山东、中院、附中、成达中学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004-002-01302。
[1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256-1257页。
[14]《北平市政府奉行政院令发接收租界、使馆界办法的训令及财政局给所属机关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009-001-00140。
[15]《北平市政府转发行政院关于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官有资产、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组织规则的训令(附接受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017-001-02926。
[16]万永光:《国民党政府收回北平使馆界》,载《文史资料选编》第四十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页。
[17]万永光:《国民党政府收回北平使馆界》,载《文史资料选编》第四十二辑,第244页。
[18]《北平市政府关于接管前使馆界树木石桥和拨东单练兵场地基为北平社会服务处举办各项建设用的巡礼及工务局的呈》,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017-001-03313。
[19]《卫生局关于接收使馆界内公厕一案办理情形及公厕粪便处理的呈文、公函及市政府命令》,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005-001-01536。
[20]万永光:《国民党政府收回北平使馆界》,载《文史资料选编》第四十二辑,第244页;《北平市工务局关于将前德国使馆院内碑炮移运历史博物馆保管办理情形给市政府的签呈》,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017-001-03451。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北京市外国驻华使馆的历史与现状”(2011SKL023)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北京市外国驻华使馆的历史与现状:(12KDC03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