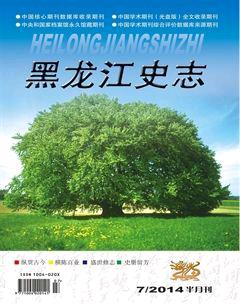浅谈唐玄宗王皇后被废
郭慧芳
[摘 要]学界关于唐玄宗王皇后被废的原因比较少探讨,本文主要从三个角度论证分析王皇后被废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王皇后本人及其家族并没有多强烈的权力欲望。并且分析了唐玄宗为防止后宫干政而不设皇后的政策不是因为王皇后而起,而是因为武惠妃而起。唐玄宗之后的皇帝很少立后,也不是全是因为唐玄宗的后宫政策,而是自有其原因。
[关键词]王皇后;政治原因;武惠妃;符厌;后宫政策
学界关于唐朝后妃的问题多有探讨,多数集中在几个比较热门的人物上,如对长孙皇后、武则天、唐肃宗的张皇后等人的研究,或者是通过不同角度对唐代的后宫整体情况进行研究,如杨小敏《论唐代后妃预政》、张淑芳《论唐代后妃与朝政的关系》、杨春蓉《唐朝后妃被废与被杀的原因探析》。但是关于玄宗的王皇后为何被废却比较少人研究。王皇后于先天元年(712年)被册为皇后,开元十二年因为符厌事件被废,被废后三个月死去。[1]2177关于王皇后被废的原因,目前学界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王皇后被废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如李文才《试论唐玄宗的后宫政策及其承继——<太平广记>卷224“杨贵妃”条引<命定录>书后》,文章明确提出王皇后被废是因为唐玄宗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并且这也是唐玄宗的后宫政策,即不设皇后以防后宫干政。《剑桥中国隋唐史》中也提及这个问题,说到王皇后被废可能有政治动机,但没有具体加以论述。还有一种就是传统的观点,即王皇后是因为与武惠妃争宠而被废。
笔者认为要判断后妃是否干政要有几个因素,即家族在政治中的参与程度、后妃本人是否有参与政治的野心、朝堂上是否有人与其有密切的政治往来。从以上因素来分析王皇后,可以分析出她因为干政被废是不准确的,其原因有三。
首先,从王皇后的家族来看,她虽然也是太原王氏一支,但她的家室并不显赫,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她的父亲王仁皎并没有因为女儿是皇后而在官场上取得多大权力,“仁皎不预朝政,但厚自奉养,积子女财货而已。” [1]4745她的兄长王守一,娶了清阳公主。唐代的驸马几乎没有政治实权,这也是唐代士人很少乐意娶公主的原因。虽然王守一与玄宗的关系很好,但是玄宗也没因此而给他多大的权力,他担任过殿中少监和太子少保,而这两个职位中,殿中少监掌管皇帝的衣食住行等,太子少保又是个闲职,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影响力。由此可见,王皇后的家族并没有因为她是皇后而在官场上有实权。唐玄宗对之前武则天改唐为周、太平公主的夺权斗争以及韦后乱政等有印象深刻,所以他对于防止后宫干政,防止外戚对朝廷一手遮天也应当早有所防范。王仁皎也说过“明明天子,择贤共理,琐琐姻娅,则无无仕。不识不知,乐我而已” [2] 2325可见他对政治并没有多大的野心。父亲多多少少都会给女儿一定的影响。王皇后受到父亲兄长的影响,应该是不会存有过多的政治野心,最多也只是为了保存皇后之位,保护好家人的荣华富贵。因此也排除了后妃干政的其中一个可能性,即外戚势力强大。
其次,王皇后并没有与朝堂的官员政治往来密切。有的学者认为从姜皎泄密给王皇后说唐玄宗要废后,就断定姜皎是皇后的支持者,进而断定皇后干政,这个是不准确的。第一,王皇后是皇上的原配,一般来说,大臣如果不是别有心思,基本都主张维护后宫稳定,废后是件大事,可能牵扯到很多事情,随意废后会影响朝政。第二,王皇后家人虽然没有政治实权,但她毕竟出身于太原王氏,在当时是士族高门,一般来说没有大错不至于要废后。第三,玄宗废后,提出的理由是皇后无子,但实际上是因为宠爱武惠妃,而武惠妃是武则天的堂侄恒安王武攸止之女,而武氏一族对李唐皇室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况且武惠妃家族并不是士族高门。退一步说,如果废弃王皇后,那么要选新皇后,从当时后妃的情况来看,也是王皇后占有优势,玄宗宠爱的赵丽妃,即太子李瑛的生母,她是出身卑微的娼妓,即使再得宠,也不可能封后,而肃宗的母亲杨氏,似乎在史料上也没能看到她得宠。武惠妃上文已说,是不可能被立为皇后的。无论如何,要立武惠妃为后,基本都会遭到反对。所以,姜皎支持王皇后也不难理解,但这并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这点可以从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时,大臣的反应印证。当时褚遂良、长孙无忌、上官仪等人都是支持唐高宗的王皇后,但这并不能说他们都是王皇后干政而培养的党羽。
第三,有人从“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 [1]2177就断定王皇后有政治野心,这更是不准确了。《唐会要》载:“元宗皇后王氏。长寿二年。纳为妃。” [4]29王皇后九岁就与玄宗结为夫妻,待玄宗准备起事时,他们已经做了许多年的夫妻了,作为结发夫妻,王皇后必然要支持玄宗的事业。并不能因此判断出王皇后有政治野心,顶多能说明她有一定的政治才能。长孙皇后在玄武门之变前都慰劳诸位将士,“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1]2164她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支持自己的丈夫,并不可以说明以后会有干政的野心。王皇后被废后,后宫人人思慕,玄宗也对废弃王皇后而深感后悔“后宫思慕之,帝亦悔。” [3] 3491如果王皇后真的是因为干政的缘故被玄宗废弃,他就不可能在王皇后过世以后还怀念她。
最后,王皇后的符厌事件。“后兄守一以后无子,常惧有废立,导以符厌之事。有左道僧明悟为祭南北斗,刻霹雳木,书天地字及上讳,合而佩之,且祝曰:‘佩此有子,当与则天皇后为比。事发,上亲究之,皆验。” [1] 2177我们知道,由于皇后无子,肃宗当年被交给王皇后抚养。就算不是亲生的,但名义上也是自己的孩子。就算无子,对她的皇后地位也不能真正影响,虽然说七出之罪里有无子,无子的确是可以休妻,但是皇家和平民家是不同的,皇后无子,但是皇帝有很多妃嫔,可以过继给皇后,而且皇后是一国之母,废后的话必然牵扯甚多,如果皇后不是因为重大的原因,一般为了维护后宫稳定不会轻易废后。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玄宗第一次以皇后无子为由要废后并没有成功。最终废后是因为王皇后弄出了符厌事件。再者,皇后在进行巫蛊事件的时候也已经四十岁左右了,这个时候才恐惧没有孩子似乎已经太晚了。如果她是担心武惠妃的孩子会被立为太子,她完全可以扶持肃宗与武惠妃的孩子一争高下,不必要在这个时候想让自己怀孕生子。所以我认为,王皇后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野心的人,在这件事上,她的目的并不是要争夺权力,而是需要一个孩子稳定在后宫的地位,并且她的当时做法很奇怪,像是病急乱投医,不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会做的。她极有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玄宗废后提出的皇后无子而受到刺激,再加上自己的家族势力不大,无法成为她的后盾,便天真的想借由孩子来巩固皇后的地位。并不是说自己要成为武则天取代唐玄宗。
有学者认为唐玄宗的后宫政策,就是自王皇后被废之后不再立后,以防皇后干政,与皇帝分权。但是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有待商榷。首先,唐玄宗废弃王皇后之后,欲立武惠妃为后“将遂立皇后” [3] 3491,因大臣反对而作废。有学者从“及王庶人废后,特赐号为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 [1] 2177这句话佐证玄宗的后宫政策是不立后,但是笔者认为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大臣反对,无法立武惠妃为后,所以为了补偿她而赐号惠妃并且礼秩一同皇后。唐玄宗确实有限制后宫干政的做法,但不是从王皇后被废这个事件中体现,应该是从武惠妃而起,武惠妃与李林甫等人勾结,陷害太子,做了一系列与前朝大臣勾结的事情,玄宗怎可能毫无知觉。如“三庶人”事件,“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常构异谋。玄宗遽召宰相筹之,林甫曰:‘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锈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天下之人不见其过,咸惜之。其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崇,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 [1] 2177对比之下,王皇后并没有与朝堂上的官员有过密的联系,除了前文所说的姜皎泄密,也没有做出残害皇帝子嗣的事件,而且她的家族也没有在朝堂上握有实权,如果玄宗要断绝后宫与朝堂的联系,保留王皇后应当是不错的选择,上文已经说王皇后家族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大的势力。前面说到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等人的政治斗争给唐玄宗带来深刻的影响,这对于早早防范后妃干政是一种提醒;黄永年《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中论证了唐玄宗根本就没有想过立武惠妃为皇后,这两点可以说明玄宗对于后妃干政的行为是清醒的;但是对于立王皇后他并没有迟疑,只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废弃了她,而武惠妃则根本没有被立为皇后。结合以上这三个方面来看,对待武惠妃才是真的为了防止后宫干政而不立她为皇后。所以笔者认为,唐玄宗有限制后妃干政的做法,但王皇后被废与这个政策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至少从事实上来说没有。但不排除玄宗过于敏感和他人的陷害。让这种政策实施的人是武惠妃。
综上,王皇后因为政治原因被废是不准确的,笔者认为王皇后被废最直接的原因使因为符厌事件,触到了唐玄宗的逆鳞,加之无子、武惠妃的夺宠、家族势力不大,无法支持她的皇后地位造成的。关于唐玄宗不立后的政策影响到后世以至于历代皇帝都刻意不立后更是无稽之谈,这点在黄永年《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中已经有说明“不过这种不立皇后以防微杜渐的措施,在玄宗以后没能继续推行下去。……蓄意不让贵妃正位为皇后的只有宪宗·……不让立后总不像太平盛世的缘故。” [5]78在玄宗以后的皇帝也是有立后的,如肃宗的张皇后、昭宗的何皇后,德宗的王皇后在册为皇后的没多久就过世了。如果真要深究唐玄宗以后的皇帝们皆不立后,我认为这可能和宦官专权有一些联系,关于这个问题,就要在下一篇文章中进行论证了。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清]董浩《全唐文》卷二百三十《赠太尉益州大都督王公神道碑奉敕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宋]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5]黄永年《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燕京学报,新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