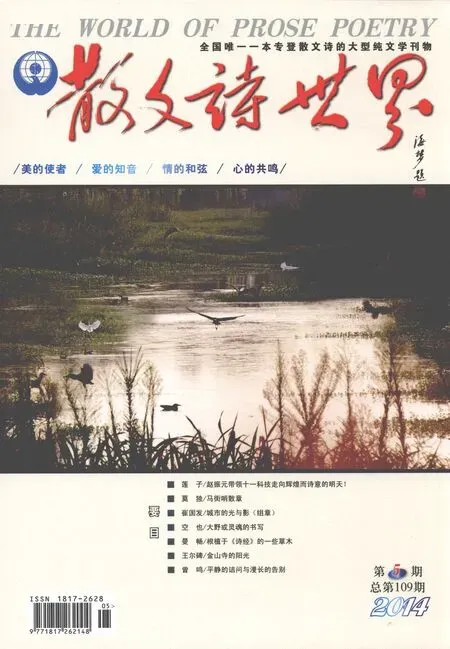野菜和春天的关系(外五章)
大连 点 点
野菜和春天的关系(外五章)
大连 点 点
野菜是绽放的,它比北方那些著名的花儿盛开得更早。即使是迎春,也是在野菜蓬勃了数天之后,才灿烂地呈现,更别说桃花、梨花、杏花。她们是江南的尤物,她们以无遮无拦的耀眼,接续着诗人们迫不及待的春梦。我领略过江南的迷离和柔美,小桥流水的江南,烟雨蒙眬的江南,柳叶婆娑的江南,似乎与这些春天的宠儿更搭调更匹配,更接近无边无际的想象。
而野菜最先亮出自己的旗帜,在我寻找了多日但春天就是不来之后。这朴素的绿荡漾着肥沃的营养,蓦地养活了我形销骨立的热盼。告诉我挚爱的朋友们,告诉我还没换上轻装的亲人:在金州,野菜以温暖人心的力量,已经走在春天的路上。
山的斜坡,枯草丛中,向阳地带的星星点点,它们有板有眼,一天胜似一天地闪着亮光,照润了村庄和牵挂。在春天的早晨,野菜,选择了眺望,选择了铺张,选择了成为后工业时代餐桌上的新欢。野菜受得了委屈,它一生的修炼,足以打败那些仪式般的桃花运。
有人缘的野菜不会孤独。从前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因为它的指引,一些水性杨花的,一些招蜂引蝶的,一些朝三暮四的,一些洋洋自得的,一些手忙脚乱的,一些繁密复杂的,所有的诱惑,都会烟消云散。
我热爱野菜,无异于热爱盐。在春天,在北方的四月,当所有看得见的生命还在蠢蠢欲动,我有向宠辱不惊的野菜致敬的冲动。它们是:荠菜、苦苣菜、山麻楂、马齿苋、婆婆丁……
麻雀或者我自己
那些满身灰色的麻雀,有时候我叫它鸟,因为它能从这里飞到那里。我一向崇拜有翅膀的生命,不像我,无论多远的路,我都要一步一步朝前走。飞,实际上是一根扎在人心里的刺,拔不出来,就只剩下尖锐或迟钝的痛。现在,我变成麻雀的粉丝,我热爱它的一举一动。
我听见这被我叫做鸟的小东西,在清晨醒来的时候叽叽喳喳地叫,它在唱歌,它过着我认为美的生活。它就停在我窗外的栏杆上,看我。看我有时候睡懒觉,可能做梦,别的人成为我梦里的主角。有时候我躲在被窝读书,甚至写几首花里胡哨的诗歌,我写:“这个普通的早晨,有风,有鸟鸣,有小草的芒刺指向辽阔的大地和天空。”
那天傍晚,有雨来袭。彼时,麻雀们正在泥土中寻找果腹的草籽和小米,我分明听见领头的打了一声唿哨,群起群落的景色真是壮观。那两只经常对歌的伴侣,多么机智,一只看我,一只看阳台上的粮食。其实,它们更像两个孩子,面对香甜的糖果,谁能拒绝被美味诱惑!但是,它们到底还是误判了我鼓励的眼神,它们到底还是飞到了一棵大树的枝桠间,睁大明亮的小眼,猜想这个世界的颜色。
很多时候,我愿意用麻雀来类比我自己。这个人类的旁观者,渺小,懦弱,谦卑,飞得不高,它深藏着提防或是警惕,不敢轻举妄动。
一缕春风刚出门
迎春,并不急于打开,她静静地抱着自己,静静地羞涩着。嫩黄的芽尖,悄悄咬住一缕春风的衣角:如果你来,我就轻盈,我就眉清目秀。可是,这样的四朵,近春情怯,欲说还休。
我依然竖着衣领,我常常低下身,我的眼睛充满疑问。比绿更绿的草,它们准备好了吗?在城市的草坪,这一棵醒了,那一棵还在做梦。这一生,我无法以一个过路者的身份与这些慵懒的小生灵握手言和。
在四月,更北的北方,洁白的雪依然是大地上最耀眼的插图。想来就来,谁忍心拒绝这些不愿退场的翅膀,犹如芭蕾舞者,踮起的脚尖只为旋转而精彩。
一切生命自有自己的理由,雪停或不停都是一种表达。不说冷!一缕春风刚出门。
现在,我幡然自省,我遇见了敌人。我以往的堕落在于,离自由的天空太远,离强大的经验太近。
行走的灵魂
你交给我月色,我交给你什么?你指给我看行走的灵魂,我指给你看什么?
是的,一切终将完成。终将亮出参差不一的表情,高低不一的身份。毫无悬念,所有的内存告急,所有的殊途同归。只不过,你们是先行者,是最初的散兵游勇,是结局里的一枚死棋。比如这些光滑油亮的农具,比如这些等待被饲养的渺小生命,比如渐行渐远的前辈们。你们,曾经靠强大的经验一声不吭地活过,活过了,等于抽身而去。“悲欣交集”,让我这个天生的讷言者浮想联翩。
许多年后,允许我结束幻想,说到一个重要的日子:2013年7月7日。
一个庄严到骨髓的仪式,伴着耳语般的一声声叮咛:搬家了。天亮之前,让你们搬到新家。夜半,鞭炮声划响暗空,宣告时光对接的成功。坟墓打开,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鱼贯而出,这些奉召的人,将自己捧出泥土。面对这个巨大的奢望,一下子将我内心的虚构击垮。亲人们哪,你们被毁灭,你们是否已抵达彼岸?我讨厌意外,讨厌出卖真相。但是现在,我在真相中无声地颤抖。
左拐左拐左拐,我已隐约分辨出青山的轮廓,欲雨的黎明中,一方方纪念碑高高竖起。我愿意称它们为纪念碑,一个个永久栖息的灵魂,从此之后随心所欲地说着家史和方言。4点49分,当我离开,当我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是啊,任什么能够遏止岁月在一条大河里沉浮,推心置腹。
我曾经耽于恐惧,以后我或许还将耽于忧伤。
今夜,月照故乡
没错,今夜月照故乡。照着老屋的遗址,照着废井,照着无人理睬的野草,也照着曾经人来人往的小径。你听到虫声了吗?无忧无虑地不疲不倦地吹拉弹唱。指挥在哪里?一阕相见欢,两阕雨霖铃,三阕执手相看泪眼。集合起来吧,今夜我忍住心酸,绝不过问你们有没有怀孕。
月照故乡,照着惊醒声、脚步声、欢呼声,照着一哄而上的抢夺声、沾沾自喜声、自断手臂声、落荒而逃声……照着这些称职或不称职的囚徒,这些被假释者,在去往自由的路上,在一块灰色的破瓦上,写:王XX到此一游。也许这样写:张XX来过。
月照故乡,照着呻吟的浅海,荒秽的河沟,白发的芦苇,照着阒静的山野,空无一人的场院,照着一只落单的家鸡,一条奔跑的瘸狗,一群慌不择路的瘦鼠,照着一颗三百年的古槐,古槐身上的黑洞。“蚂蚁也搬家了?”它用深褐色的眼睛悄悄问,我不回答,我说不出口。
月照故乡,照着寂寥的东山,芜杂的西山,让人心疼的北山。离群索居的北山是落叶们最后的归宿地,是秩序的最后拥护者。月照北山,照着父亲的三尺泥庐,泥庐旁疯长的青藤和三朵无人欣赏的牵牛花。树是守卫者,它们并不粗壮。父亲,这个有月光的晚上,你能不能走出来,重做一枚枝上的绿叶,做一个梦也好。
月照故乡,照着岁月这个和平演变的高手。嗯,我守口如瓶吧。
老屋以及水井
即将成为告别的一部分,老屋以及水井以及比烙印更深的往事。
以及维系一生的怀念。怀念通过抚摸表达出来。这时刻,我恨不能生出一万双手,一块砖,一片瓦,一丝木窗的细纹,一帧全家福旧照,有体温有呼吸有流淌不息的血液。它们存在,虽然我看不见它们,就像风,它们簇拥在我的身旁,我因此惊恐或者荡漾。这之前,我一直欠它们一个正视和端详。现在,我不能对它们说出我的任何一种情感,我一筹莫展。
几代人,我们在自己的江山上堆积粮草,积攒越来越旺的烟火,镌刻生存的谱系,建造宗庙和社稷。大胆设想,我们原本的渴望,能够在汗湿的土香中生根。深入的根,欢快地向深处掘进,多么谦卑的辽阔!谁是告密者?谁在多嘴?我这个敏感的当事人,分明感到了缺氧的绝望。
我决定不去招惹那些有月的晚上。因为彼此喂养的忧伤,像海绵里的水,不碰最好。一碰便泛溢,便恣肆,便无力阻止。当我仰望这些以明天的名义命名的废墟,我不能反抗,不能起义,不能暗怀不良的心事。“这是我的绫罗,我做梦的地方。”“这是我经年的胎记,我要用它将短暂的黑暗挤走。”
只有风模仿着它们的容颜。风依然洞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