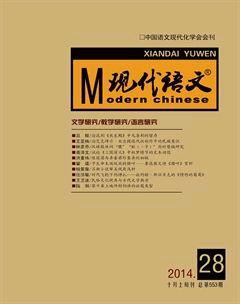文体自觉:内容与形式的深刻辩证
摘 要:晏杰雄的《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一书聚焦于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问题,角度独特新颖。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或者文体意识的自觉化是该著作的核心议题,它在根底上依旧是对小说内容与形式之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与检讨。正是因为参透了内容/形式的辩证法,该著作对文体概念、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范畴与总体特征等问题的研究,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关键词:新世纪 长篇小说 文体 形式 内容
一
自“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产生以来,对这一阶段文学的关注度日益增加,相关的论文、专著层出不穷。这当中,有关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研究成果却依旧不多,且多为作品选读或有关新世纪作家代表作品的评论集。而对新世纪长篇小说进行整体研究的,则更为少见,代表者有王春林的《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它们意在勾勒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发展轨迹,在作家作品的评论方面可谓面面俱到、深入细致。晏杰雄的《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则聚焦于文体问题,力图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对近十年来长篇小说的文体作一深入剖析。因研究角度的独特新颖,该著作有效避免了浮泛空论,而且为学界确立了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研究领域。
《研究》一书大体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围绕文体概念的界定、近三十年长篇小说文体的演进以及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整体特征等,对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体问题作了全面的理论阐发,并且提出了“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的核心观点。这一部分又进一步从三个维度展开:首先,作者在考察“文体”的词源以及评述前人对文体的定义后将文体界定为“人造物”,并由此出发划分长篇小说文体的基本范畴为叙述、结构、话语三部分;而后作者对长篇小说何以为“时代第一文体”作了全面缜密的分析,并勾勒出近三十年长篇小说文体意识由萌发、扬厉再到沉淀的发展趋势;最后亦即本书之重点,作者从理论高度提纲挈领地指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体现出了内在化、本土化、混沌化的总体特征。
《研究》一书的后半部分则致力于从文体范畴(叙述、结构、话语)出发进一步阐述“新世纪长篇小说问题向内转”这一核心观点。首先,在叙述上,体现出了传统叙述同现代叙述的完美融合,比如全知视角的复归和多样视角的综合。其次,在结构上,作为主体的情节性结构同多样性的开放型结构的交相呈现。情节性结构让小说重新具有故事性,并以内心的尺度来构造故事。开放型的结构则通过生活流、心理图示、系列小说、空间并置等多样化的构造类型,把拙朴的表现与内容的表达密切结合起来。其三,在话语上,突出体现在直接引语比例加大与对话性语言的出现。与直接引语增加相对应的是间接引语的大幅度减少及自由引语的节制适度运用,在对话性语言上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同时呈现在作品中。可以说,这些在文体范畴方面的变化都是长篇小说逐渐走向内敛成熟的有力表现。值得肯定的是,《研究》一书在后半部分结合具体作品做了大量的把脉式的微观分析。这样,既有根柢又有兴会,避免了浮根游谈,并且对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有着切实的诊断意义。
显然,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或者文体意识的自觉化是《研究》一书的核心议题,它在根底上依旧是对小说内容与形式之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与检讨。也正是因为参透了内容/形式的辩证法,该著作才在长篇小说文体研究方面有诸多斩获。
二
文体者,常涉两个层面:一为体裁抑或文类,二则是“形式”之代称。《研究》一书将文体范畴确定为叙述、结构、话语,显然更接近广义的“形式”。新时期创作中常见的文体实验,其实也就是形式的变革与探索,远远超出体裁抑或文类的范畴。对于写作者来说,文体并不是作品一件简单的“外套”,启用一套文体意味着“更新人们感知或想象世界的能力,使那些被既有文类规范挡在门外的生活经验获得呈现的机会”[1](P58)。因此,唯有以自觉的文体意识从对象化的世界中发现新的意义,作者才会感到真正的文体自由,文体才有切实的价值。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对文体形式的追求确实带有表演与炫示的成分,而且它以创新之名将每个创作者催逼得焦头烂额。后先锋时代的作家们显然厌倦了苦心孤诣的文体实验,更乐意冷静地去为内容寻找贴切的形式。当代长篇小说文体演变的历史性正表征了它自身的非本质主义特性。《研究》一书对文体本质的界定没有墨守前人成规,把文体界定为一个本质化的东西,而是强调文体涵义的动作性,突出人为性,“文体是文学作品中作为人造物的一部分,它规定作品的艺术特质,与作家的认知方式和现实世界存在一种对应关系”[2](P37)。这一界定无疑在处理形式与内容关系上下了功夫:文体与内容没有哪个具有先天的优先性,文体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对应关系。或者如《研究》一书作者所言,文体“内含着作家对小说的构造、设计和安排,与小说的内容、时代、社会、文化等非文体因素隐约呼应”[2](P41)。詹姆逊就曾指出:“文学素材或潜在内容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它从来不真正地在原初是无形式的,从来(不象其他艺术那些未经加工的实体材料那样)不是在原初就是偶然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具有意义,既不多于又不少于我们具体社会生活本身的那些成分:语词、思想、目的、欲望、人们、地点、活动等等。艺术作品并不赋予这些成分以意义,而是把它们的原初意义转变成某种新的、提高了的意义建构;由于这个原因,作品的创作和释义就都不可能是一种武断的过程。”[3](P362)因此,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只是对文学素材的原初意义进行组织,并转化为我们所能见到的新的文学意义结构。也就是说,形式与内容之间殊难进行截然的二分。
晏杰雄认为,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自觉转向了一种比较沉稳的文体创新,即具有向内转的特点,其演进特征则体现为文体意识的沉淀。具体表现有,作者不再轻易地秉持内容决定文体论或是唯文体论,“文体意识已经在作家的内心沉淀下来,他们自觉把文体意识贯彻到长篇小说的主题经营、人物塑造、事件排列和场景描绘之中”[2](P71)。在考察了近三十年文体意识的演进趋势后,他指出,文体演变是连续性的而非断裂性的,而在这连续性中体现的是文体和内容关系的新变,即“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过程,实现了一次漂亮的回归……一个螺旋式的前进过程”[2](P84),文体因此趋向成熟和内敛。
三
《研究》辟专章具体阐述了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总体特征:内在化、本土化、混沌化。这三者以内容与形式之辩证法为前提,获得一种有机的统一。
内在化,即“形式和内容建立了一种生息相通的默契和对应关系”[2](P87)。形式和内容达到统一,并非是以前那种理念先行的内容形式两结合的统一,而是相伴相生的,文体与现实同构,文体在作家“文气”的带动下自然成形,这样生长出来的作品既是受大众亲睐的可读小说,又是饱含美学含量的好小说。晏杰雄认为,新世纪长篇小说实现了好看小说与好小说的合一,这种合一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返归,以平实易懂的情节、贴近生活的描写,搭配富有张力的文体,两者的搭配融洽而不突兀,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契合。
返归现实主义也就是要促成文体形式的本土化。它并非要回到一种单一的创作技法,而是指在文体上奉行一种“现实”而理性的态度。比如对传统文体形式的借鉴就以对文化“现实”的尊重为基础,中国小说流变过程中的所有文体,比如章回体、史传体、笔记体等,都可以成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借鉴来源。这种文体形式上的“现实主义”态度,确实有利于祛除一味西化的迷梦。上世纪80、90年代是新时期文学文体实验的高潮阶段,各种主义轮番上阵,炫目异常。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有了中国版本,但文学的自主性却也在鹦鹉学舌中迷失了。因此,文体形式上的“现实主义”态度为本土化确立了观念前提。不过,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在文化上返归传统,奉行文化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无论文体形式的本土化内涵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是以其与现实文化世界的对应性为前提的。而纯粹西化或复古主义的文体形式不过是对现实文化世界的完全遮蔽与漠视。经过百年现代性进程的洗礼,不可能再有完全以中国古典文化为基础的纯然“本土”了。今天意义上的本土已经是中国文化经验与全球化相互激荡、交合的产物,当中既有自己传统的东西,也有西方文化的影子。因此,晏杰雄指出:“新世纪文体本土化的边界已经大为扩大,致力于在立足本土文学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吸收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获得一种民族根性的突出,同时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的中国书写形式。”[2](P104)《研究》一书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本土化写作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汉语传统写作,比较纯正的本土化;二是原生态写作,更多与地域性有关;三是具有现代性质的本土化写作,文体意味比较先锋。[2](P105-112)这个分类正体现了长篇小说文体本土化内涵在新世纪的扩大和丰富。有理由担心这种分类是否过于泛化。其实,开放的本土化并不是任意的,不变的正是那种具有民族根性、民族气的东西。可以说,开放的本土化所追求的是“建立形神具备的本土化文体”[2](P114)。这是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走向,也是本土化在当下呈现的新内涵。
这种开放的本土化因此呈现出一种形式与内容辩证合一的“混沌化”特征,“一方面,它复杂多元,可以包含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中国叙述传统和古今中外的一切文体因素;另一方面,它单纯到极致,所有艺术元素被安放得恰如其分,彼此交融,浑然天成,形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2](P116)
总之,“本土化”特质的形成是文体意识自觉化的体现,是内容与形式层面的深刻辩证。曾经风行一时的文体实验,在轮番上演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剧情的同时,却完全忽视了中国自身文化经验的在地性与特殊性。这当然也就裂解了文体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的隐性对应关系。因此,本着现实主义文化态度的本土化书写可以说是对过度西化的一种纠偏与补正,是形式与内容间的一次全新融汇。这种书写形式正是以文体内部“深刻的裂变和优化组合,形成了富有本民族特色的独立的丰茂的叙事美学”[2](P104)。
四
在涉及叙述、结构、话语等文体基本范畴的具体分析时,《研究》一书也切实地体现了著者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关注。
在叙述方面,新世纪长篇体现出一种全知视角的复归,它与中国叙事传统相接通,以最接近生活原生态的视角再现复杂的生活和时间跨度巨大的历史事件。出于故事和主题的内在需求,作家也追求多样视角的综合。时间上,与文体实验期的时间变异化相异,顺时成分增加,不刻意追求时序错乱,“以最简单的时序创造最丰饶的文体意义”[2](P161)。空间上,形式实验中浮夸的因素逐渐去除,以更成熟的方式沉淀在以时间形式为主导的小说文体的底层,空间形式的运用节制从容[2](P169)。在结构方面,结构与主题相生相伴,与表达内容血肉相连,具有现实特性的情节型结构成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主体。在话语方面则摈弃集体性话语,向原初本真的杂语性、对话性复归。这些叙述方面的变化可以说“反映着长篇小说文体意识的沉淀和内在化倾向,即文体向作品的内容和精神内核靠拢”[2](P155),表明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达到了新的艺术水准。
晏杰雄敏锐捕捉到了评判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状况的节点:正是作家们具备了清醒自觉的文体意识,才使得这一时期的长篇创作出现长足进步。这一致思角度不仅敞开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域,而且为这一领域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学理基础。从《研究》一书的行文中,不难品味出晏杰雄在褒奖长篇小说文体变革的同时,也寄予了殷殷期待。在长篇小说创作整体向好的大局面下,亦有诸多危机潜滋暗长。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态度确实成就了不少作家,却也使得部分作家浑水摸鱼,轻易规避了文体问题上的大考。王蒙、莫言、韩少功以及先锋派诸将都曾经历过文体实验高峰时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文体上的感觉积淀,运用起来自然举重若轻。而有些作家之返归文体上的“现实主义”则不过是出于商业目的,为迎合市场谋求迅速蹿红的讨巧行为。正如一个评论家所说的,“文体的自由对于作家的意义迥不相同。天才作家手中的自由提供的是展现天才的空间。天马行空,神来之笔,这是自由赠予天才作家的风格;庸才作家手中的自由提供的是掩护平庸的借口”。[4]
与文体形式上的工具理性态度相伴随的则是题材内容方面的新危机。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全面合围下,我们的生活单一而雷同,如是境况下的创作信息来源自然是极为近似的。显然,作家生活的中产阶级化带来了生活的同质化。诚如韩少功所言,都市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沙发是大同小异的,客厅是大同小异的,电梯是大同小异的,早上起来推开窗子打个哈欠也是大同小异的,作息时间表也可能是大同小异的。在这样越来越雷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形同做梦[5]。形式主义文论家早就深谙如下观念:形式亦即内容。适度的文体实验往往具有颠覆、改写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面对生活同质化的迫力,适度文体实验也许依旧必要。
注释:
[1]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晏杰雄:《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3][美]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4]南帆:《文体的震撼》,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
[5]韩少功:《作家的创作个性正在湮没》,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8期。
(王瑞瑞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