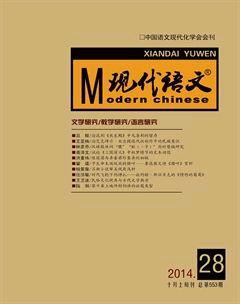人生如梦
摘 要:19世纪末老纽约的习俗,在《天真时代》中得以生动的展现。它造成了令人扼腕叹息的爱情悲剧,同时也探索了走出痛苦的道路。评论界多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关注其中受压迫的女性角色,极少从哲学层面予以解读。本文从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出发,勾勒女主人公人生悲剧的解脱之道。
关键词:悲剧 欲望 痛苦 意志
伊迪斯·华顿的代表作《天真时代》,荣获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其作品以老纽约上流社会为背景,揭示其风俗习惯,并以细腻的笔触剖析家庭、人性、伦理、婚姻,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风貌。
《天真时代》中的男主人公阿切尔陷入一场爱情困境:与刚从欧洲归来的埃伦相爱,却又与她的表妹梅·韦兰订婚、结婚,最终有情人也未能成为眷属。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上流社会相当保守。阿切尔与埃伦迫于世俗的压力,还是各奔东西。其间,尽管埃伦并不畏惧保守的家族势力,但她的善良本性不容许她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因而远离纽约,定居于巴黎。她的爱情虽然破灭了,但始终没有向自己卑劣的丈夫妥协。时隔将近三十年之后,她丈夫已去世,可是她仍然保持了自己既有的生活方式。这时的她,显然已经看透了人生:放下各种欲望,脱离世事的牵绊与苦恼。然而,将近三十年的平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评论界对这部小说多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解读,探讨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及女性追求自由的斗争,本文则采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以揭示人生的本质。
一、引言
叔本华将非理性哲学的意志确立为哲学与美学的本体,认为意志也是悲剧的本体。由于意志的存在,人生就出现多种欲望,这些欲望又是盲目的。欲望一旦得到满足,就会产生下一个欲望。更为可怕的是,欲望得到满足会觉得无聊,得不到满足就会感到痛苦。痛苦与无聊就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贯穿于人的一生。王国维也指出生活因欲而至痛苦的本质: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而一矣![1]因而,如何面对人生的苦痛,成为古今中外无数贤哲不断思考的问题。叔本华认为必须否定生命的意志,才能达到对人生的静观,这样才会摆脱烦恼与痛苦。“生命意志的否定,就是把欲求的千百条绳索,作为贪心、恐惧、嫉妒、盛怒,在不断的痛苦中来回簸弄我们的绳索,统统都割断了。”[2]所以,若能够领悟到这一点,生的痛苦自然也就消失了。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得以解脱的情况又分为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当一个人目睹了他人所受之痛苦,领略到宇宙人生的本质,感受到苦痛与意志如影随形,之后能够放下自己的欲求,达到精神的解脱,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一个人不断地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奋斗,又不断地遭到挫败,直至绝望,那他最后也就否定了生命的意志,这种解脱也是颇为悲壮的。
叔本华认为:“对于悲剧来说,只有表现大不幸才是重要的。”[3](P347)他将不幸的来源分为三种:一是坏人的挑拨或恶行,二是盲目的命运所酿成,三是由于悲剧中人物所处的地位关系所造成的。第三类被王国维认为是“悲剧中之悲剧”,因为人们在正常情况下,互相对立,但又并非恶意而制造的悲剧最让人痛苦。
二、“剪不断,理还乱”
埃伦从欧洲归来,希望能够得到自己家族的支持,与龌龊的丈夫离婚,不料却在上流社会引起了非议。阿切尔,作为一个思维超脱于传统的年轻人,尽力去帮助埃伦缓解尴尬的处境。作为一种手段,他与埃伦的表妹梅订婚了,从而不自觉地为自己将来的爱情之路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埃伦的率真与坦荡打动了阿切尔,同时她也为阿切尔的与众不同所吸引。可是,毕竟两人都承担着自己将要面临的家庭责任,在忍受着巨大痛苦的情况下,这对情侣只能劳燕分飞。
人生的欲望是盲目的,阿切尔自然也不例外。埃伦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公开亮相,是在剧院看演出。可是,因为她的衣着的肩部和胸部露出的部分比当地习俗略多了一些,就引起了不满,并且有人认为她是不甘寂寞,所以来看演出。阿切尔看不惯众人羞辱她,就决定宣布与梅订婚,希望借此能够证明埃伦此行并非随性而来,而是必须参与家族的事务。毫无疑问,他的做法会起到相当的作用。然而,此举也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某种程度上,他的订婚满足了纽约社交界的期待与家族的要求,但这都是出于外界的“压力”,阿切尔并不真正了解梅,更谈不上爱慕。梅的可爱之处,也只能是她符合老纽约对女性的各种行为规范的要求。因而,盲目的欲望也使他一度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曾见过埃伦丈夫的人这样评价他:“老喝的半醉,苍白的面孔上露出讥笑……,我来告诉你他那德行:他不是跟女人在一起,就是去收集瓷器。据我所知,他对两者都不惜任何代价。”[4](P13)与这样的丈夫在一起生活,何谈幸福?埃伦希望离婚,就常理而论,并无不当之处。纽约上流社会的风俗确实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们所关注的是埃伦的行为是否符合他们的标准,女性离婚就有损自己家族的荣誉。从中外的传统来看,女性离婚的确是社会的一种禁忌,不少文化中甚至更极端。但是当时整个社会就是那种氛围,所以也不能认为反对埃伦决定的人就是邪恶的,他们也不过是按照通常的社会伦理道德作评价。这样一来,就是两种善的力量的对立与冲突,造就了阿切尔与埃伦“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悲剧,也可谓“悲剧中之悲剧”。
埃伦之所以放弃自己的诉求,完全源于她对恋人的爱与善良的本性。她曾很明确地告诉阿切尔,她放弃离婚并非为了婚姻的尊严,也不是害怕在别人眼中沦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为了家庭避免舆论、避免丑闻,必须自我牺牲,我才放弃了吗?因为我的家庭即将变成你的家庭——为了你和梅的关系——我按你说的做了,按你向我指明应当做的做了。她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我可没有隐瞒:我是为了你才这样做的!”[4](P148)她是不畏惧任何势力阻扰她获取幸福的,而当自己的恋人充当家族的说客劝她不要离婚时,她还能指望什么呢?如果将她视为一个战士,那她绝对称得上是一员虎将。可是面对自己人时,她就不知所措,“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梅和阿切尔只是订婚,并非没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假如她奋力一搏,把阿切尔争取过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几百年前,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敢做的事,凭什么她不能呢?“爱之愈深,情之愈切”,她不希望自己成为阿切尔人生的包袱。对于自己而言,即使被家族遗弃也无所谓,可是她不希望连累自己的至爱。毫无疑问,刻骨铭心的痛是她长时间都挥之不去的。非理性的欲望就是这样折磨她,她也只能默默地承受。
在阿切尔眼中,埃伦这位贵族少妇为人坦率,不拘世俗,老纽约的风俗人情却是充满了世故与圆滑。“她身上却散发着一种美的神秘的力量,在她毫无做作的举目顾盼之间有一种自信,他觉得那是经过高度训练养成的,并且充满一种自觉的力量。同时,她的举止比在场大多数夫人小姐都纯朴。”[4](P53)这在埃伦对客厅的装饰中也有所体现,桌椅摆放得极为讲究,花瓶里插着红玫瑰。而她所读的书,保罗·布尔热,休斯曼和龚古尔兄弟的书,都是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作品,可以看出她是力图探寻生活的本来面目的人。这样,在阿切尔眼里,“经过高度训练”也就不足为奇了。相比之下,梅所表露出来的人格特质恰恰相反。“所有这些坦率与天真只不过是人为的产物。未经驯化的人性是不坦率,不天真的,而是出自本能的狡猾,充满了怪僻与防范。他感到自己就受到这种人造的假纯洁的折磨。”[4](P39)这是在他仔细剖析了梅的性格之后得到的结论。梅自然很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借以向阿切尔和艾伦施压,率真的艾伦又怎么能是她的对手呢?梅所做的每一件事,又都是以上流社会的规范为依据的,无可挑剔。任何人也不能否认一位女性按照社会所认可的伦理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力,她的所作所为也不应该受到指责。在明知自己未婚夫移情别恋时,却不能拍案而起,据理力争,因而她也是那种特殊社会风俗的受害者。这也是埃伦与阿切尔爱情悲剧最令人心痛又扣人心弦之处,也注定了埃伦最后必然再次选择放弃阿切尔的追求。
身为不幸婚姻的受害者,虽然具有悲剧英雄的气概,却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不能施展自己的抗争意愿。无法解脱与自己的丈夫的婚姻关系,更不能与心仪的男人长相厮守,同时还遭到世俗的压力,却无人愿意去倾听她精神上所忍受的痛苦。她尽管也坚持过,但终究还是妥协了。人生的欲求无以满足,接连挫败,对一位少妇而言,这种打击过于沉重了!
三、道不同,不相为谋
梅疑似“怀孕”的消息,促使埃伦下定决心离开纽约这个伤心之地。但是,她还是坚持了离开自己的丈夫,选择定居巴黎,而非回“家”。在阿切尔婚后的一年半中,她逐渐理解了这个小圈子,明白自己与它是格格不入的,“经历了最初的新奇兴奋之后,她发现自己——像她说的——是那么‘格格不入,她无法喜欢纽约喜欢的事情。”[4](P208)生活中虽有许多高雅的乐趣,但要想得到,就必须付出巨大的“艰辛与屈辱”。埃伦此时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与其呆在纽约与阿切尔纠缠不清,受人诽谤,还不如远离是非之地,一个人去过平静的生活。
歌剧《浮士德》在书中反复出现,这也正是男女主人公所面临的艰难抉择。浮士德难题也是困扰整个人类永恒的难题:“怎样使个人欲望的自由发展同接受社会和个人道德所必需的控制和约束协调一致起来——怎样谋取个人幸福而不出卖个人的灵魂”[5]阿切尔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恪守自己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因而家庭是“美满”的。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成为执政当局眼中的“好公民”。可是,他本人的行为始终都是循规蹈矩的。像他这样出身显赫的人,也仅仅是处于墨守成规的水平。但是,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他是有责任与义务去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以使整个社会习俗更加合乎人性情理。滑稽的是,社会己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却沉溺于往昔的习俗之中不能自拔。尽管自己失去了“生命的花朵”,仍认为“旧的生活方式也有它好的一面”。老纽约那一套家庭伦理观已完全被抛弃,自己的儿子和曾经被上流社会驱逐的博福特的女儿相恋,无疑也是对那种压抑人性的家庭伦理观的嘲讽。过去神圣的规则归于虚无,这令生活于其中的阿切尔难以接受。“这壮观的景象已摆在他面前了,当他放眼观看它的时候,却感到自己畏缩了,过时了,不能适应了,与曾经梦想过的那种意志坚强的堂堂男儿相比,他变得渺小可悲……”[4](P309)甚至当自己妻子过世,儿子安排他与埃伦会面,他仍然不敢面对。或许他为当初自己的怯懦与“理性”感到惭愧,无颜面对所爱的人;或许他认为旧有的风俗还是比较好,自己应当至死坚守。无论如何,他都落伍了。
与阿切尔相比,埃伦在巴黎的日子显然是自得而又惬意。关于埃伦的生活,书中并未正面阐述。但是从阿切尔儿子的话语中,可以得知她对博福特的女儿范妮很友好,带着她在巴黎到处玩。她的生活方式在这三十年中没有改变,尽管令她伤心的丈夫已经过世。阿切尔的儿子是和父亲一块儿看望埃伦的,可是阿切尔却没有进门。这时的埃伦也是知晓往日的情人到达,她也没有主动去迎接。她并不是回避,也没有任何畏惧,只是顺其自然。历尽了人世的沧桑,酸甜苦辣皆已品尝过,无怨无悔。这在她离开纽约前已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在阿切尔婚后将近两年时又提出与埃伦逃离纽约,到一个类似于爱情乌托邦的地方时,埃伦很敏锐地意识到了其虚无缥缈。她认为希腊神话中的戈尔工已经挤干了她的眼泪,“她也打开了我的眼界。说她弄瞎人们的眼睛那是一种误解,恰恰相反——她把人们的眼睑撑开,让他们永远不能再回到清净的黑暗中去。”[4](P253)总之,她在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苦之后,认识到人生的虚无。此刻的眼界更开阔了,她已经能够达到对生命的静观。阿切尔仍然寄希望于埃伦能够同意保持情人的关系,这怎么可能呢?“背着信赖他们的人寻欢作乐”,必将玷污爱情,也将侮辱他们的人格,埃伦绝不接受。她明确地告诉阿切尔,“你从来没有超越那种境界,而我已经超越了。”这些细节足以说明埃伦对于人生的看法业已发生根本的转变:她不再留恋尘世的欢乐,不再对未来有明确的追求。
在这场爱情悲剧中,阿切尔本身并没有受到多深的伤害。尽管没有得到埃伦,他仍然拥有了“大家闺秀”梅做妻子,儿女的出生,也为这个家庭增添了一抹亮色。梅的品格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要求,阿切尔对她也是满意的。之所以与埃伦相恋,是因为埃伦身上率真、正直的品格补充了梅的一些不足,但也并非不可或缺。所以,在妻子过世后,他仍然放不下往日的世俗偏见。埃伦则不同,她从欧洲到纽约,几乎是孤注一掷,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要离婚。这其中她究竟流过多少泪水,书中没有正面交代,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老纽约社会中的“入侵者”,她所受的委屈常人无法理解。如此之大不幸,使其放弃所有欲求,摆脱人生的痛苦,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便是“觉自己之痛苦”而悲壮地获得了解脱!
四、结语
即便身处“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也必有梦醒的一天。人生就如一场梦一样,只是一部分人在历尽悲欢离合之后,能够梦醒归来。“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到头来终究都是一场空。无论“观他人之痛”,还是“觉自己之痛苦”而放下欲望,否定生命的意志得以解脱的,都是幸运的人!
注释:
[1]王维玉:《王国维悲剧理论的哲学视界》,社科纵横,2012年,第5期。
[2]蔚志建:《论叔本华的人类悲剧与艺术悲剧观》,东岳论丛,2005年,第5期。
[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伊迪斯·华顿,赵兴国,赵玲译:《天真时代》,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5]傅守祥:《理性悲剧〈浮士德〉: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张玉 湖南长沙 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41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