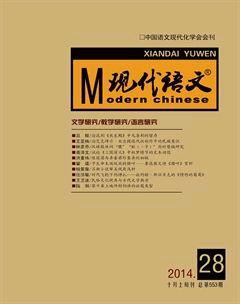精神分析视野下的《雷雨》主要人物命运分析
摘 要:运用精神分析法中人格构造理论、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对剧本《雷雨》的主要人物繁漪、周萍、鲁大海的形象特征及命运历程进行分析,探求隐藏在其内心不为人知的“潜意识”。
关键词:《雷雨》 人物 精神分析
《雷雨》是曹禺先生早期创作阶段的杰作,同时也是他的成名作。《雷雨》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作品的结构处理以及人物语言的独特之处,也应该归结于他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成功运用,正如郭沫若所说:“这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而曹禺《雷雨》中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成功运用主要反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并揭示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对主要戏剧人物命运历程的支配和操控作用。
一、繁漪: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中挣扎
繁漪是曹禺塑造得最为成功、进行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的人物形象。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整体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主要部分构成。在一个精神健康的人身上,这三个部分是统一的,相互协调的。如果这三部分相互协作,就能够使人在自己的环境里,进行有效的令人满意的生活和工作。反之,这个人就属于顺应不良的类型,对自己不满时,他就会变得发狂或消沉。”这段理论道出了繁漪悲剧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作者也正是从心理角度来探究在压抑苦闷的环境中如何通过本我、自我、超我的抗争,直至走向毁灭的结局的。
“本我”是由被称为“力比多”的原始生命本能构成,遵循“唯乐原则”,即无所顾忌满足本能的需要,寻求快乐、避免痛苦。繁漪是个本我意识很强的女人,她年轻貌美,天生丽质,受过新式教育,她原有着美丽的心灵,对生活怀着热情的憧憬,对爱拥有更多的渴望,自从嫁到周家来,就如同一只金丝雀落入一口令人窒息的枯井里。周公馆这个禁锢的封建大家庭,极大地限制了她追求幸福、满足情感的欲望,十几年的伪善、专制、冷酷、凶横把她渐渐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但是自周萍从乡下来后,她压抑多年的爱欲找到了投射的对象,周萍的爱情也点燃了繁漪原本以为自己不会有的欲望,她重新获得了新生。
“本我”驱使繁漪可以毫无顾忌地追求原始欲望的满足,但是这种实现是有限度的,她更多的是“自我”的存在,“自我”遵循“现实原则”,繁漪的现实是她身为太太,过惯了舒适豪华的生活,并且生育了自己孩子周冲,不可能弃家远逃,她企图在“本我”与“自我”的夹缝中苟且偷安,但是来自“超我”的道德原则理智地提醒自己,这种与继子的畸形恋情是为传统伦理道德所不容、为现实社会所不齿的。虽然她能够高傲地说“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但她和周萍却只能“闹鬼”,他们的恋情唯恐被外人知道,沉浸在热恋之中,却无法向任何人吐露自己的幸福,而儿子周冲的存在多少使她有些内疚和不安。当正常合理的人性需求在受到现实和道德的压抑与扼杀后,属于“本我”因素的本能欲望遭到“自我”和“超我”的压抑时,她不得已以隐秘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感,整日把自己关在楼上,以养病为名躲藏在自己的空间里,也逐渐形成果敢、阴鸷和乖张的性格。当发现周萍决心退出时,她不惜牺牲自己的自尊和高傲,如笼中困兽一般作决死的拼杀,这种挣扎和奋斗,烧毁了自我的理智,也揭开了另一出更大悲剧的面纱,终于使自己的精神彻底崩溃。
二、周萍:在误认和错位的恋母情结中沉沦
“恋母情结”又称“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即指男孩被压抑在潜意中的恋母弑父欲望。弗洛伊德认为:3岁—5岁儿童的人格发展处于男性生殖器崇拜阶段,此时男孩对母亲有着强烈的依恋性,将母亲看成自己爱慕的第一个对象,而将父亲看做竞争对手,表现出攻击意识。作为《雷雨》中的线索人物,周萍的内心深处有着挥之不去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印记,不过,由于周萍性情的荒唐复杂和生活环境的特殊,他的“恋母情结”明显出现了误认和错位的倾向。
作为周家的大少爷,周萍从小生活在缺失母爱,而父爱也不健全的家庭,生母“早逝”,父亲不易亲近,被寄养在乡下的他,在童年时代的潜意识里其实早已埋藏了一种对母子情爱的神秘感,他强烈渴望得到母性的爱抚和依恋,直到长大回到周公馆,繁漪以继母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这种郁积心间的“恋母情结”终于找到了实体目标。他一头扎进了她——现在的母亲的怀抱,实现了孩提时代无意识欲望的满足。可以看出,周萍的这种情结一方面表现在对繁漪的暧昧关系上,另一方面又表现在对父亲的嫉妒与不满上,当他察觉到“母亲”受到父亲的压制陷入痛苦与不幸时,这种嫉妒感就愈发强烈,可能导致报复甚至仇杀。他憎恨自己的父亲,曾对繁漪说过“自己恨父亲,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事他也干”。然而,屈于家庭教养和父亲威严,周萍没能走上这一步,他觉得自己用了另一种方式来报复父亲——即占有父亲的女人,周萍的恋母情结逐渐发展为杀父意图,引诱自己的后母,无异于俄狄浦斯的娶母。
但是繁漪毕竟是周萍名义上的母亲,与亲生母亲侍萍相比差距甚远,周萍在与她的暧昧关系中越来越明显地体会到这之中的误认。虽然相处那么长一段时间,他始终没能体会到浓情如火、沸腾如潮的甜言蜜意,相反留下的却是无穷无尽的悔恨和罪恶,周萍的原始欲望(自我)不但没能得到满足,反而遭遇现实(自我)和道德(超我)的冲击,乱伦的罪恶感占据了上风,他不再爱繁漪了,甚至厌恶这个忧郁过分的女人,他喝酒胡闹,处处避开后母的纠缠,试图通过和四凤的正常恋爱达到自我的升华。
如果说周萍对繁漪的恋母情结是一次误认,那么对四凤的感情却是这种情结的延续和错位。四凤是周朴园前妻侍萍的女儿,无论外形与内部,与母亲侍萍极为相似,在四凤身上,周萍找到了苦苦念想生母的影子。所以,当这个18岁的女子出现周萍面前时,他一下子抓住了她,“觉得她新鲜,她的‘活!”并迅速爱上了门不当户不对的丫头,这个恰恰说明,周萍始终没有逃脱恋母情结的桎梏,他逃脱了爱上继母的犯罪感,却又不自觉地陷入了另一对象——四凤的恋母情结的无意识深处。当发现自己和四凤身上流淌同一个生母侍萍的血液时,面对这种残酷现实,周萍的精神崩溃了,他只要活着就永远摆脱不了祖先积累下来的感染力对他的控制,他只有一死,别无选择。
三、鲁大海:在仇父情结下的孤独反叛
在弗洛伊德、荣格等精神分析家的眼里,恋母憎父原本就是一对不容割舍的孪生情结,将鲁大海的逃亡归结于仇父情结的败坏与破灭,不失为一例绝好的佐证。从剧本来看,鲁大海是一个罢工工人的代表,但同时也是一个被生父遗弃的儿子。与周萍不同,他刚烈坚定、粗犷直爽、不畏权威、嫉恶如仇,在他身上无一不是憎父、弑父情结的化身,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视生父与继父为寇敌的“雷公崽子”。
鲁大海对两位父亲的“仇”不尽相同。对继父鲁贵,他从没叫过一声父亲,二人关系极端恶劣,不仅看不惯继父好逸恶劳、卑鄙庸俗的奴才嘴脸,更容不下继父在家里摆一副自鸣得意、吆五喝六的老爷派头。他不屑一顾地骂鲁贵“他忘了他还是个人”,他揪住鲁贵的领口,逼迫鲁贵去找周萍,甚至不惜把手枪对准继父,厉声咆哮“我打死这个老东西”,使得鲁贵诚惶诚恐,恰如一个儿子一般。当母亲侍萍难以劝服四凤放弃周家时,鲁大海俨然以一副“长兄如父”的姿态前去干预四凤恋爱私事。这足以说明在现实的家里,鲁大海早已流露出厌恶父亲的情绪,甚至暴露了取代父亲的势头,也反衬出大海对母亲的深情和依恋,因此他要处处取代父亲,来保护母亲,不让母亲蒙受任何人的欺凌。
再看看鲁大海对周朴园的态度:面对自己并不相识的亲生父亲周朴园,他表现出极大的轻蔑和嘲弄,怒斥周朴园卑鄙无赖,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不要脸的董事长”,是“老混蛋”“强盗”,并向他发出的“绝子绝孙”的天遣:“哼,你的来历我都知道,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在叫江堤出险”“你故意淹死两千两百个小工,每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虽然这与父子冲突无甚关系,但通过侍萍之口可知大海是决不认父孝亲的,横亘在父子之间的是无法消解的阶级鸿沟。当鲁大海的身世关系揭开时,他不得不离之而去,亡命天涯,与其说他恨周朴园,不如说在重亲情、尚孝道的伦理规范下,鲁大海的“仇父情结”因变得“非法”而没有了与周朴园共同生活的空间。
四、结语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性欲的升华。”不管是繁漪、周萍还是鲁大海,他们的感情、行为和命运轨迹在很大一部分上都受到了本能潜意识和俄狄浦斯情结的影响,正是这种隐性的俄狄浦斯情结,让他们在感情中充满了矛盾与纠结,越想挣脱却永远被命运之锁扼住了喉咙。这正如《雷雨》的悲剧,并不仅限于阶级悲剧、命运悲剧,它也充满古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俄狄浦斯、拉伊莱特一样的悲剧色彩。
参考文献:
[1]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朱君,潘晓曦,星岩.阳光天堂:曹禺戏剧的黄金梦想[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陈晓娴.蛮性的遗留,神性的主宰——试论《雷雨》创作的原始情绪[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9).
(干敏 广东深圳 罗湖外语学校 51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