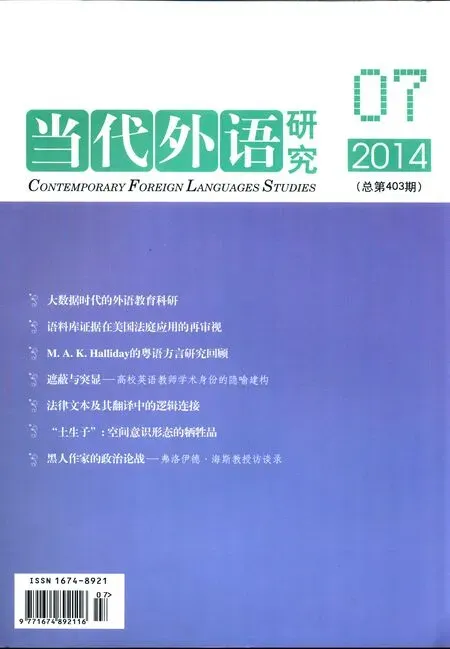柏杨译“大力水手”的个案分析
白立平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
1.引言:有关翻译与意识形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过程,而是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有紧密关系的活动。1970年代以来,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逐渐在西方兴起,这些研究者关注的不是“应该怎样翻”,而是强调对翻译活动进行一种客观的描述性研究,更加注重对影响翻译活动的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描述翻译理论研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group)是描述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学派。这一术语来自于赫曼斯(Theo Hermans)编的论文集《文学的操控:文学翻译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书名中的“操控”一词由安德鲁·列夫维尔(AndréLefevere)给出的,后来阿米·保罗·弗兰克(Armin Paul Frank)创出了“操控学派”(亦称 manipulation school)这一术语,并通过玛丽·斯奈尔-弘比(Mary Snell-Hornby)的著作而广为传播(Hermans 1999:9)。列夫维尔是“操控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Lefevere 1992b:81)认为,文学翻译研究需要将社会历史纳入研究的视野,重要的不在于考虑字词怎样吻合,而是探讨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社会、文学、意识形态的考虑促使译者那样去翻译,他们希望那样做能达到什么目的,是否达到了目的,原因何在。他(Lefevere 1992c:10)还认为翻译需要与权利、赞助、意识形态、诗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点探讨各种将不同的“文化万象”(Universe of Discourse)①整合起来的做法,考察各种使文本容易理解,并操纵文本使其为特定的诗学和/或意识形态服务的现象。
什么是诗学(poetics)?这个术语总是与亚里士多德那部著名的《诗学》联系在一起。虽然亚氏在《诗学》里并没有对这一术语进行明确界定,但从他论及的内容来看,“诗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阐述文学基本原理的学说。列夫维尔(1992a:26)认为诗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一套文学手法、文类、主题、人物、情景及象征﹔其二,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文学的角色是怎么样的,或者应该是怎么样的。而后者对于社会系统相关主题的选择有影响作用。列夫维尔说诗学的功能组成部分明显地与来自诗学外部的意识形态影响紧密相关,是在文学系统中由意识形态因素所促成的(同上:27)。
对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业内解释与界定众多,莫衷一是,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意识形态”包含各种各样的含义,而且很多彼此之间并不兼容,因而没有人能下一个定义将“意识形态”所有的意义都囊括进去(Eagleton 1991:1-2)。他在书中列举了流行的十七种定义,认为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社会生活中意义、符号及价值的衍生过程”,可以是“特定社会团体或阶级特有的一套观念”,可以是“促使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利合法化的观念”,可以是“促使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利合法化的错误的观念”,也可以定义为“被有系统地扭曲了的交流方式”等等(同上)。不难看出,这些定义有的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主要涉及政治权利。列夫维尔本人在他的著作里也没有给意识形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在谈论“赞助”时,借用了詹姆士(Jameson 1974:107)的界定,指出“意识形态”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包含了任何能够指引行为的形式、习俗以及信仰(Lefevere 1992a:16),这一定义也涵盖很广的意义。
列夫维尔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及诗学对于文学翻译的影响,而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他说,有两种因素决定着文学翻译活动,即译者的意识形态(不管他是甘愿接受还是赞助者强加给他)以及翻译进行时译入语文学的主流诗学。意识形态决定着译者采用的策略,并对源语与译入语的“文化万象”引起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Lefevere 1992a:41)。而当语言因素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因素发生冲突的时候,前者往往会让位于后者(同上:39)。
赞助(patronage)也是影响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赞助”是指那些“足以促成或妨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力量(包括个人和团体)”(同上:15)。赞助人会对译者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及诗学取向产生影响。列夫维尔(同上:11-25)认为有两个控制元素可以保证文学系统和社会其他系统不至于有较大的偏差。这两个元素包括文学系统本身的一些“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以及来自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专业人士”指的是批评家、评论家、教师以及译者。他们经常会对一些文学作品进行干预,使其不能与主流的诗学以及意识形态相去甚远。“赞助”包括了三个元素,第一是“意识形态”因素。其次是经济因素,“赞助人”通过给予译者一些津贴或者使其担任一定的职务确保作者或改写人有经济的来源。列夫维尔说乔叟(Chaucer)就担任过国王的特使,与乔叟同时代的约翰·高尔(John Gower)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并不自由,却至少在经济方面是自己的赞助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赞助”不一定包含所有的因素,也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甚至一个人可以成为自己的“赞助人”。第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地位问题,接受了赞助就意味着融入了一定的赞助团体及其生活方式。这三者可以统一于同一个“赞助人”,也可以不属于同一“赞助人”(同上:17)。
在三十五年前的台湾,发生了一件由翻译引发的政治冤案——著名作家柏杨因漫画“大力水手”中的几句翻译而锒铛入狱。罗曼与维达(Román &Vidal)指出,对于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了解译者在译文中添加了什么,省略了什么,选择了什么词以及如何放置这些词。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因为译者做出的选择展示了历史以及社会政治背景(Román & Vidal 1996:5)。本文将结合意识形态的有关论述对柏杨的翻译及其获罪原因进行分析,考察柏杨的译文是否有添加或省略的情况,他是否使用了某些有特定意义的词汇,以及在这些“改写”的背后是否有译者意识形态的影响。
2.柏杨译“大力水手”分析
柏杨翻译的这组漫画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八年二月号第12~13页,如下页图所示:
“大力水手”“卜派”(Popeye)是美国漫画家西格(Elzie Crisler Segar,1915~1994)创造出的一个可爱的卡通人物②,然而他却几乎给柏杨带来灭顶之灾,柏杨被控译文语气有“侮辱元首”的嫌疑,柏杨夫人艾玫(当时担任《中华日报》家庭版编辑)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被传询长达十五个小时,柏杨也于三月一日至二日被传询长达二十七个小时(孙观汉1974:35)。后柏杨被捕,并牵连出其他问题,总共被监禁了九年零二十六天。为什么一幅漫画的翻译给柏杨带来如此之大的麻烦?我们可以使用列夫维尔的理论来分析这幅漫画及柏杨的译文。
在诗学方面,柏杨译文有什么特点呢?如果抛开原作不管,译文与原漫画人物相映成趣,所用语言短小精悍,非常口语化,而且符合人物身份。对照原文,会看到有的地方翻译得还是不错的。比如,在原英文中,儿子说:“Is write-in votes okay?”这句话中的“write-in”是指在选票上写上非法定候选人的名字,言外之意是,儿子不大情愿投父亲的票,而要投自己的票。这里柏杨的译文是“我要跟你竞选!”译文虽然与原文意思不完全对等,但将原文的隐含意思译了出来,假如照字面意思翻译,译文可能会显得累赘,中国读者也不大容易理解。柏杨将其灵活翻译为“我要跟你竞选!”就显得口语化,与画面也相配。当然,这句话似乎也可以翻成“能不能选其他人?”或“我能不能投自己的票?”
柏杨的翻译整体上传达出了原文的基本意思,但如果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柏杨的译文并不忠实于原文文字,与原文有较大的出入。比如,其中一幅漫画中,父亲趴在一块木板上写着什么,父子对话如下:
Son:Now that ya owns yer own country,how is yago’ner rule it?
Father:We is goin’to have free elections and I yam runnin’fer presidink!
这段对话的字面意思是:
子:你有了自己的国家,那你怎么来治理呢?
父:我们将进行自由选举,我要竞选总统。
柏杨的译文是:
子:老头,你要写文章投稿呀!
父:我要写一篇告全国同胞书。
原文没有“写文章投稿”以及“写一篇告全国同胞书”的意思。柏杨在这里似乎并没有根据原文去翻译,而是根据画面自己编出“要写文章投稿”这样有趣的问题。
原文中,父亲只有一次谈到他要发表演讲:“As a candidate fer presidink of this new country I would like to make a speech!”(柏杨翻译为“等我先发表竞选演讲!”)柏杨的译文则强调了这一点。漫画中,父亲说的“我要写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就是在准备演讲稿。“And one③of us is going to vote!”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其中一人要投票!”柏杨的译文是“但我还是要演讲。”
在最后的一幅漫画中,父亲说,“And if ya don’t vote fer yer adoptid pappy yajust might git spanked!”意思是说,“你不投你养父的票的话,我就打你屁股!”柏杨这里的译文是,“千万不要投小娃的票。”原文的基本意思传达了出来,但语气有所减弱。
柏杨的译文中还有多处与原文出入较大:
Father:Popalania is go’ner be the mos’peaceful nation on earth!
Son:How is yago’ner manage that?!
Father:It will be simple fer a smart ruler like me to build a peaceful country!
Father:I will only let the swabs I know I can lick become citizens!
这几段话的意思为:
父:Popalania将成为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
子:你怎么办到呢?
父:对我这样聪明的统治者来说,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家,真是轻而易举!
父:我会让我能征服的水手成为我的国民!
柏杨的译文是:
父:你算皇太子吧!
子:我要干就干总统。
父:你这小娃子。口气可不小。


这里,柏杨没有根据原文进行翻译,而是根据漫画进行联想,编出上述对话。儿子的“我要干就干总统”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原文四句话里,儿子只有一句话,而且不是重点,其中心是父亲谈如何来治理新国家,但译文的重心转移到儿子身上,父亲让儿子当“皇太子”,儿子不服,说要当“总统”。儿子在原文的话本不重要,但在译文里,则成为父子对话的核心,父亲紧接着的两句话都是针对这句话而说的。但如果对照上述两种译文,会发现前一种译文句子要长得多,而后一种精悍短小,非常口语化。
使柏杨招罪的主要是这么一句话:
Father:Fellows Popalanians...if ya votes fer me I promises to give yapeace,happiness an’spinach in yer pots!
柏杨的译文只是简短的几个字“全国同胞们……”,原文的其他部份被省略。漫画中,父亲在演讲中许诺,“如果你们选我的话,我会给们带来和平、幸福,锅里还有菠菜可吃!”都被柏杨省略。总之,如果从传达原文字面意思上来考察,柏杨的翻译是不忠实的,是对原文的改写。但译文在总体上传达出了原文的故事梗概,用词方面也符合人物身份。柏杨在翻译方法上,并没有做到忠实原文,他说这是当时台湾漫画翻译普遍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要引起读者的兴趣。他在一九六八年给孙观汉的信中说:
过去我在翻译时,为求简单与趣味,以便引起小读者的兴趣,故有很多地方未采用原文原字(台湾漫画翻译均是如此),且用语力求“俏皮”“幽默”,但对主题及整个故事,毫无违背。盖一旦违背,便无法发展。(参见孙观汉1974:9)
看来,我们不能够强求柏杨的译文作到忠实无误,因为这并不是他的翻译指导原则。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分析柏杨的译文,可考察柏杨翻译这部作品时是否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这里暂时抛开柏杨事发后的辩解。要看这幅漫画是否有政治寓意,就需要结合柏杨翻译这幅漫画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一九四九年之后,国民党政府兵败大陆,来到台湾,蒋介石在这里实行的是一种严厉的统治,多次“连任总统”。其子蒋经国也身居要职,是蒋介石“总统”的“接班人”。蒋介石每年元旦都要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柏杨翻译的漫画讲述的是一对父子来到一座孤岛上的故事,这对父子很容易使人想到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这座孤岛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台湾这座小岛。到了岛上,父亲要发表演讲,以竞选总统,而讲词中却有蒋介石常用的“全国同胞们”(或“全国军民同胞们”)这样的用语,因英文原文并不是如此,这容易使人联想到译者是否别有用心,而漫画发表的时间恰好在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的第二天,更能使读者对号入座了。漫画中父亲竞选总统所采用的手段并不光彩,明为民主,实为独裁,这会使人联想到可能在影射蒋介石。在翻译中,译者无中生有了“你算皇太子吧!”其隐含意义则可能是,现在已经实行民主了,但封建皇权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而柏杨所写的杂文很多都是抨击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文字,他很有可能在这里借题发挥。从以上分析来看,柏杨很可能利用翻译这样的漫画来针砭时弊,并影射讽刺“国家元首”。从赞助人这方面来看,这幅漫画会使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柏杨接受了某个组织或个人的赞助来从事这样的活动?如果是的话,这个赞助者是谁?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这位可能的赞助者是不言而喻的,受到这样“赞助”的人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柏杨本人并不会同意以上的推理。这幅漫画的真正译者是谁?柏杨也有不同的说法,他曾说这幅漫画是他翻的,但在别的场合又说是他的学生颜素心翻译的,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保护颜素心。他说,
……而且即令退一万步,退到文字狱盛行的清王朝时代,可以构成文字狱啦,亦与柏杨先生无关,我不过照本宣科,一字一字誊之抄之而已,但在询问过程中,法官老爷则一口咬定非颜小姐手笔,而是我包藏祸心、独出心裁,存心侮辱国家元首。迄今为止,我没有拿出颜小姐这批原译文,因颜小姐为菲国籍,来台四年,事我如父,事艾玫如婶,宁可使我身陷万劫不复之地,不愿献出原译,使一异乡孤女遭受祖国内斗的凄苦之灾……(同上:12-13)
柏杨译文中出现的是“全国同胞们”还是“全国军民同胞们”?这里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在孙观汉《柏杨和他的冤狱》以及李敖写的《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中引用的译文皆为“全国同胞们”,本文引用的漫画出自《明报月刊》,与孙观汉和李敖引用的材料一致。但在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的《柏杨回忆录》里却指出柏杨将其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
“大力水手”漫画是连续性的,金氏社每次直接寄下两个月的稿件。大概十二月初,一天晚上,倪明华④刚进家门,就接到《中华日报》的电话说,大力水手已没有存稿,明天一早,会派专人来取。明华这时候才紧张起来,一面坐下来赶工,一面催促我,一定要快点赶出译文:“译稿完成后,请放到送稿袋里,我不再看了。”
“大力水手”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漫画,没有政治色彩。可是,那一次的稿件,画的却是波派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父子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在开场称呼时,波派说:
“Fellows...”
就是这个Fellows,引爆使我毁灭的炸弹,我如果译成“伙伴们”,大难降临的时间或许延后,可是,我却把它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心中并没有丝毫恶意,只是信手拈来而已。译完后,蹑手蹑脚走进卧房,把它轻轻的塞进送稿袋,舒了一口气,上床就寝,没有一点恶兆。历史上说大人物灾难发生之前,总会有点不祥的预感,这也恰恰证明,我不是一个大人物,只不过一个倒霉的平凡作家而已。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日,《中华日报》刊出这帧漫画,没有人注意它,连我和明华也没有注意它,它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刊出的连环漫画罢了。可是,虎视耽耽的特务们像发现新星球一样,奔走相告;假如我的耳朵敏锐的话,会听到他们的磔磔笑声。(柏杨1996:251-52)
柏杨自己并不承认他翻译时有侮辱元首的动机。按照他的说法,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挣点稿费。他说“明华要我翻译,以我的英文程度,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但我却接下这份工作,因为漫画上的对话十分简短,更重要的是,又多了一份稿费”(同上:251)。他在一九六八年给孙观汉的信中也说:
……去年(1967)五月,艾玫主编中华日报的家庭版,增设“大力水手”漫画,为美国金氏社出版供应。当时曾向社方报告,请政大女生颜素心翻译。可是有一天在饭桌上,艾玫忽然曰:“你也可以译呀。”可是我的英文程度不够,她说可以查字典,可以跟她研究。而稿费可以补贴补贴家用,听了稿费,这才接下这份工作。但数日下来,深感负担不胜,且无时间,艾玫乃仍□⑤颜素心小姐,而颜小姐已还菲律宾(她有菲律宾国籍)。直到十一月间,她由菲律宾返台后,仍接手翻译。因她对编排外行,故仍有两事由我负责,一是把原文割去,一是把颜译稿抄在原稿之上。(参见孙观汉1974:7-8)
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柏杨到底是不是有影射元首之嫌呢?柏杨坚决否认。李敖(1998:314)也说,“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中央了”。设法营救他的孙观汉也认为特务小题大作,他对“大力水手”这样的漫画也不以为然,他说,“讲句老实话,在我心目中,‘大力水手’是一种迎合低级趣味的无聊出版物”(孙观汉1974:22)。
办案人员虽不懂列夫维尔的翻译理论,但他们却不自觉地使用了其思维方式,将柏杨译文与一系列的文本之外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并由于这一事件而连代地揪出了柏杨的其他问题,最后使其锒铛入狱。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同样套用列夫维尔的理论,将柏杨事件与当时台湾紧张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就不难理解⑥。加之,柏杨的其他作品多针砭时弊,早已让当局不快,他翻译的“大力水手”就成了一个导火索。
3.结语
柏杨的“大力水手”事件使我们看到了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意识形态问题,即使译者没有意识到,也有可能会被他人联想到。这件事对译者的启示可能在于,翻译一定要字斟句酌,避免出现一些敏感的词句或容易引起对敏感事件联想的词句,以免产生不应有的误会。当笔者将列夫维尔的理论套用到柏杨身上,进行一番分析判断以后,惊讶地看到这一思维模式与揪住柏杨问题的人的思维模式如出一辙。柏杨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九年多的铁窗生活!这件事对我们如何来借鉴某些翻译理论也有一定的启示。翻译研究者可以借鉴一些翻译理论,但不能牵强机械地套用理论,而是要尽量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面,尽量客观全面地分析翻译中的问题。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一定是绝对的。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可能会体现在译文上,但译文中某些词句或段落不一定是意识形态影响的体现。研究者在分析译本的时候,不可以断章取义,而应该更多地了解到问题的方方面面,这样才不至于得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
附注
① “文化万象”是指“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概念、意识形态、人、物的总和”(Lefevere 1992d:35)。“文化万象”这一译名借自谢聪所译《翻译的策略》一文(参见陈德鸿、张南峰2000:177)。
② 有关“大力水手”的情况,可参考 Grandinetti(2004)及Sagendorf(1979)。
③ 原文这里用黑体。
④ 即艾玫。
⑤ 原信中该字无法辨认。
⑥ 关于国民党在台的情况,可参看刘红、郑庆勇(2001)、黄嘉树(1991)、雷震(1989)和李敖(1999)。
Eagleton,T.1991.Ideology:An Introduction [M].London & New York:Verso.
Grandinetti,F.M.2004.Popeye:An Illustrated Cultural History [M].Jefferson &London:McFarland.
Hermans,T.1999.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ic Approaches Explained [M].Manchester:St.Jerome.
Román, Álvarez & M. Carmen-África Vidal.1996.Translating:A political act[A].In A.Román & M.Carmen-África Vidal(eds.).Translation,Power,Subversion [C].Clevedon,Philadelphia & Adelaide:Multilingual Matters.1-9.
Lefevere,A.1992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Lefevere,A.1992b.Longer statement[A].In A.Lefevere(ed.).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C].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81-171.
Lefevere,A.1992c.Introduction[A].In A.Lefevere(ed.).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 [C].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ヲ-え.
Lefevere,A.1992d.Universe of discourse[A].In A.Lefevere(ed.).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C].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35-45.
Sagendorf,B.1979.Popeye,the First Fifty Years [M].New York:Workman.
柏杨.1996.柏杨回忆录(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陈德鸿、张南峰.2000.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黄嘉树.1991.国民党在台湾:1945-1988[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雷震.1989.雷震全集[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李敖.1998.李敖快意恩仇记[M].台北:商业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李敖.1999.白色恐怖述奇[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刘红、郑庆勇.2001.国民党在台50年[M].北京:九州出版社.
孙观汉.1974.入狱时的大概[A].孙观汉.柏杨和他的冤狱[M].香港:香港文艺出版社.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