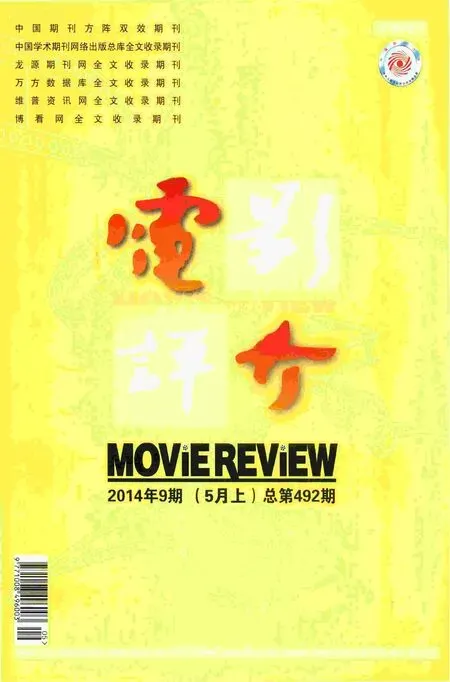四季轮回中的人生《春去春又来》——一则关于生命的寓言
□文/吉 平,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匈牙利罗兰大学副教授
罗兰·巴尔特根据文本的基本性质及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的不同,将文本分为“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概言之,“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则不断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显然,韩国导演金基德的《春去春又来》不是一部明白晓畅的读者性文本,其中的点滴设置及整体安排背后的深意值得观众再三思量。
一、空间的功能:山、水、古寺与外界
影片中环境元素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环绕的群山、苍茫的湖面和湖水中央的一座古寺。在这里,山和水都是远离尘嚣、保持佛土清净的屏障,只有一叶小舟往来于古寺与外界、佛性与人心之间。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中,故事中的人物行为就能够更加突出地展示生命本能冲动与佛界归化的冲突与斗争。[1]
二、时间的作用:轮回的只是四季
故事的讲述从春天开始,主体部分完成在冬天。影片终了,作为故事的余续,春天明媚的阳光又洒在宁静的湖中寺庙上。此时复现了影片开始时的场景:还是一小一老两个和尚和谐相处,只不过当年的小和尚已成为此时的老和尚。这令人不禁感叹:又是一个相似的人生故事在缓缓拉开帷幕。春夏秋冬又一春——始而复返的何止是四季,更是绵绵不绝的人生轮回以及轮回中表现出的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影片关注的焦点是人内心那个浩瀚无垠的宇宙。
三、风景的效果:一切景语皆情语
故事中,水的波动是人物心境的外露,与四季轮回一起变化的人生命运就如同湖水的形态:春日水平如镜,老少二人和谐相处;夏天波澜涟涟,青年欲念勃发;秋风萧瑟,湖水漫涨,青年犯下了杀戒;待到刑满归来,人到中年已是万念俱寂,而此时恰逢湖面冰封、寒冷坚硬。[2]一切景语皆情语,人物的内心世界与风景变换相呼应,山水形态的变化应和着人物内心的悸动。就这样,人物内心激越动荡的情感冲突在永恒不变的大自然背景中展开,使得影片在呈现出含蓄婉致的写意风格的同时,也形成一种动与静的相互映照。
四、动、静互易的镜头叙事手法:富于哲理的视角变换
水中的孤寺是故事发生的起点,也是潋滟波光中唯一静止不动的中心。但在影片中,导演却通过机位的变化,以动静倒置的镜头画面营造出一种新的意境。从一组表现老僧带小和尚划船外出的镜头中可以看到,辽阔的水面上,划动的小船在不断扩大的取景框里仿佛凝滞在中心一般,由此把动态的场面转换成静穆的表达。而在另一组表现山水寺庙景色的空镜头中,近景处的下方一直保持了半淹在水中的树的形象,中景是孤寺一间,远景则是绵绵远山。在镜头推移的过程中,偏斜的树和远处的山脉构成扇形的观景面,当扇面缓缓展开时,老树因占据近景的中心位置而保持着静态,远山则由于连绵不绝而显得毫无变化,给人以纹丝不动的假象,而居于中景的孤寺却产生了漂移的假象,从而赋予静物以动感。[3]此外,还有长大的小和尚与女孩一起在寺庙屋檐观望山色;小和尚杀人归来、又被警察捉走之前在寺旁面对远山的冥想;老和尚涅槃前的打坐……都是人在观山,而影片中表现的手法却是通过镜头的缓缓扫视,让自然山水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呈现在观众眼前。这种新颖又意味深长的动静互易的摄影效果,令影片的叙事产生了一种哲理性,即一切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换一个视角来看,在变中可以有不变,在不变中可以生出变:变中的不变,或是美与爱——景之美、人之爱,以及天人合一——世间至高境界的一种美与爱;不变中的变,则是亘古的自然、佛境与如白驹过隙般稍纵即逝的短暂人生的对比,以及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人性与佛性撞击、冲突时不同的具体表现形态。
五、高僧的眼泪:人性的温度
影片一方面借用了佛教传说中“收伏心魔”的故事原型,另一方面又在整体的叙事进程中偏离了原有的“立地成佛”的静态故事原型,侧重以动态的叙事变奏暗示人性较量的艰难与曲折。[4]
且不说影片中的重头戏——小和尚所经历的激烈的内心斗争与挣扎:正当年的小和尚在强大本能的驱使下堕入情网后追随爱人奔向红尘,乃至因爱不成而生恨,杀了背叛自己的爱人,为逃避追捕而重返寺庙,后在师父的点播之下通过刻写木地板上的佛经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内心净化,若干年后服完刑期重返并重整寺庙,抱佛像上山,收养婴儿,直至春暖花又开……,就连看上去清静无为的老僧身上也体现了某种矛盾之处:轮回中,寺庙年迈的住持虽然能够以意念遥关中门、驻留小舟,却不能够掌控爱徒的人生航船。尽管他倾力相助,观察点拨,顺势牵引,却终不能够阻止爱徒奔向红尘的步伐,亦不能将已在精神上有所醒悟的徒儿从尘世的牢狱中解救。他的美好祝福与深深牵挂终成随风飘散的暮鼓晨钟,无所不在而又无从驻留。徒儿在被警察带走之后,老和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自己的后事。在涅磐之时,一向超然的老僧流下的两行泪水模糊了闭塞视听的宣纸。
按照佛教教义的说法,生死轮回是人生苦的表现,把苦的根源归结为与生同在的欲念,所以老僧选择了封闭五官的辞世方式:在一寸见方的白纸上写下“闭”字,逐一糊在眼耳口鼻上。“闭”的目的在于隔绝外物,通过回归本心的澄明来灭绝杂乱丛生的欲念。[5]然而,相反的意义指向总是在叙事的重要关口出现——两行眼泪模糊了写着“闭”字的白纸。这就形成了影片的叙事裂隙:超然高僧为何会流下浸染着尘俗苦痛的泪水?
当年,之所以明知徒儿在爱情的强大引力下即将背弃信仰,奔向滚滚红尘,却在不寐中听着徒儿偷偷离开寺庙,是因为老僧晓得人的天性不可违逆,只能因势利导,所以尽管他身怀绝技,却从不滥用,因为他谙知人的界限。在老和尚身上,一种普世的关怀与爱分外感人。然而,在徒儿带来的尘嚣终于落定之后,清净无欲的老僧却选择了辞世。他涅磐前的泪水意味深长:爱的失落,人生之痛。影片意象的矛盾设置构成了对于叙事对象的反思与质疑。老僧以猫尾为笔,蘸墨在寺庙前的木地板上书写佛经,试图帮助爱徒平复内心的狂澜,重归佛门净土。故事中,小和尚的矛盾是外显的,老和尚的矛盾是内化的。人想超越自我,达到一种圆融的境界,谈何容易!
在超然的老僧身上,导演努力做的是增添他身上的人情与人性的温度——善待生命,关爱徒儿;对于静寂的千年古寺,也做如是处理——春夏秋冬,不同季节出现在古寺左近的的狗、鸡、猫、蛇,令佛门净地染上了生命的灵气与活力;而对待生命活力旺盛的小和尚,导演则力图凸现他内心深处潜在的佛性——由一个懵懂的小和尚,到受到欲望诱惑而破戒、还俗,甚至犯了杀戒,再到服完刑后回归、重整寺庙,最后抱石像上山,象征性地战胜了肉身的自我,达到了一种灵性的超越。此间充满了辩证意味,也让影片内涵变得更加丰蕴。
六、无墙之门:自我修行的隐喻
影片中数度出现了门的特写,从寺庙孤零零的山门到寺庙内和尚寝室与佛堂之间的门。这门有些不寻常:门是真的门,墙却是虚空。导演试图表达的是:与事物隔绝的墙存乎人心,而门却通向佛境。无墙之门意味着人内心的自省自觉,正如儒家强调的“君子慎独”。
门启门闭,天地悠悠,光阴荏苒,季节更替。小和尚一直跟随师父循规蹈矩,依门而行。然而随着自然生命的生长,青春期欲念勃发的小和尚在夜晚试图开门去与睡在佛堂的少女相会。可是由于师父躺着的身躯的阻碍,门无法打开通行。无奈之下,他只得匍匐爬过无物之墙去与少女相聚;青年和尚与少女初次去山中幽会,漫涨的湖水淹没了山门的门槛。在门的开合之间,显示的又何止是流逝的时间!“门启门闭,因心而行,人的一生,知理辨识,都在每一次推开命运之门的瞬间,万物有序,人性参差。”[6]
更有一个镜头,在给寺庙山门特写时,往上抬了一下,三个字赫然映入观众眼帘:人生庵。其实,整个故事就是关于人生庵的叙事,它关注在不同生命阶段人的内心所经历和承受的一切,指向的是人生的超越。这个拥有佛学表象的故事,其本质是对于人生人性的深沉思考。
[1][2][3][4][5]老天使.后东方化的叙事意境[EB/OL].(2006-08 -15)[2014 -05 -19]http://movie.mtime.com/12717/reviews/295572.html.
[6]黎光容.用影像抒写的人生寓言《春来冬去》[J].电影文学,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