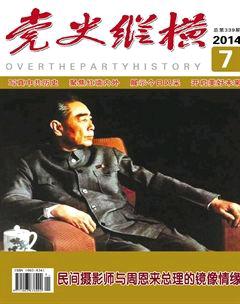彭德怀在最后岁月里写下的几封信
沈国凡


一篇含沙射影的文章再掀彭德怀生活波澜
彭德怀是1965年11月30日从北京到达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的。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将姚文元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学术研究》专栏里作了转载。当时,彭德怀忙于安排住处,接受新的工作,未能读到这篇转载文章。
12月4日,彭德怀在听西南三线建委留守处一位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后,趁休息的时间走到会议室的报架前,伸手取了一份《人民日报》,然后戴上老花眼镜阅读。姚文元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道:1959年6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看到这,彭德怀突然站起来,生气地将报纸扔到报架上。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一进门就一拳击在桌子上,同时大声地吼道:“胡说,这简直是胡说!”警卫参谋景希珍和秘书綦魁英看到这样的情景大惊,忙问:“彭总,发生了什么事?”彭德怀说:“别问了,你们去会议室看看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吧!”二人读完姚文元的文章,也都感到很震惊。
为了安慰彭德怀,景希珍和綦魁英说:“彭总,我们都是当兵的,谁弄得清那些学术研究,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文章批的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你又与他没有什么联系,更何况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专家,历史上的事情,让他们读书^.争论去吧。”彭德怀摇摇头说:“你们真傻,这文章明明是含沙射影,打我彭德怀的耳光,而且叫你有气都没有地方出。人家说的是历史,可实际却是另有所指。现在革命胜利了,我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还能弄得过那些摇笔杆子的人。”景希珍说:“彭总,那文章中又没有点你的名字,人家批的是戏。”彭德怀听后冷静了下来说:“小景说的也有道理,自古写忠臣良将的戏多得很,吴晗这个人,我与他没有什么交往,他写戏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说是为我老彭打抱不平?”
此时已远离政治中心的彭德怀并不知道,就在姚文元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就在杭州的西湖边,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已将彭德怀列入了“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打倒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庐山会议后的6年时间里,彭德怀一直独住在北宋忠臣良将杨六郎挂甲归田的挂甲屯,一边劳动,一边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从姚文元的文章中,他洞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他要趁这场风暴还未到来之前,抓紧时间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他要在这场风暴中,做一棵宁折不弯的英雄树,高昂起不屈的头颅,为真理、为正义、为着自己深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随时献出自己的一切。
彭德怀点燃一支香烟,一边吸着,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警卫参谋景希珍见他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就劝道:“彭总,你最近常咳嗽,还是少吸一些好。”彭德怀看了警卫参谋一眼,然后又猛地吸了一口香烟说:“哎,我也知道要少吸烟,可是自从庐山会议之后,这烟就越抽越多了。”接着,他又说:“那个姚文元是干什么的,怎么总是将吴晗的戏硬往我头上套,这是在搞学术争论,还是在搞别的什么?我是挨过全国上下批判的人了,刚出来工作,不容易呀!”停了一会儿,彭德怀接着说:“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为此我愿意做一块煤,燃烧尽自己。可是,现在看来,我就是想做一块煤,也不会让我燃烧了。”秘书綦魁英忙劝道:“彭总,不管那个姚文元怎么骂,反正你名叫彭德怀,又不叫海瑞,怕什么,还是多保重自己的身体重要。”彭德怀听完秘书的话摇摇头,凄然一笑,说:“綦秘书,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想你一定能看出这文章后面即将来临的风暴。这个姚文元真是个混蛋,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就开始无事找事,在鸡蛋里去挑别人的骨头。有什么法子哩,无非是再来一次全国上下对我彭德怀的批判。我已想好了,我一生光明磊落,对得起党和人民。实际上哪有人是被批臭的哩,只要自己不腐烂,不变质,就什么都不怕!”彭德怀的话让景希珍和綦魁英不便再劝了。过了一会儿,彭德怀走到桌前,用力掐灭了烟头,用牙咬了咬宽厚的嘴唇,坚定而果断地对他的警卫参谋和秘书说:“不管他们的,让他们去闹吧,我们还是得抓紧时间干我们的正事。明天我继续听三线建设工作的汇报,过几天我带你们一同到三线建设的一些大工厂去看一看。我们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地工作!”
身陷困顿的大将军写下的三封信
1967年元旦,彭德怀仍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
新的一年来到了,外面是什么情况,铁窗里的彭德怀一无所知。他如同一只猛虎,被关在了一只笼子里,将他与人民隔离开来,没有了行动的自由,更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对于目前的状况,他感到焦虑和不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看不到自己的对手,无法与对手短兵相接,更谈不上拼刺刀,这位战场上的赫赫名将,感到异常的无力和失望。毛泽东让自己出来到大三线去工作,现在怎么又会被一些学生莫名其妙押回北京来?这些学生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毛泽东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无数的问号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他怀疑党内出了内奸,有坏人在迫害自己。他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就将发给自己写检查的纸笔铺开,准备直接写信给毛泽东。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因为写信给自己引来灾难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在1955年写了近30万言的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国以来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些个人意见和看法的胡风——这是一个被认为是“鲁迅传人”的文人,后来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子,遭无辜迫害关押达25年之久,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得平反。另一个就是彭德怀,他于1959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写了“万言书”,陈述“大跃进”中的得失,后来不但被免去了国防部长职务,还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头子。人们始终弄不明白,行武出身的彭德怀为什么会想到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并非他的“强项”,然而他却做了这样的选择。
关于彭德怀到三线工作,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毛泽东已认识到对彭德怀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时候为他恢复名誉。另一种说法是:由于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
元旦这一天,彭德怀仍然不得安宁,住在他隔壁的“红卫兵”冲进屋来,说是给他“拜年”。他们将彭德怀拉起来,让他站在屋子里,逼他“交待罪行”。彭德怀问道:“你们把我弄到北京来,我的工作怎么办?你是找我算旧账还是新账,新账我没有,我去三线是毛主席动员我去的;旧账要算我不怕,我早就向中央讲清楚了,毛主席也是知道的。”“红卫兵”吼道:“你这个老反革命,老混蛋。你还想翻案!”说着,他们就冲上前来,一把夺过彭德怀手中的烟斗,又去翻他旁边的黄挎包,将里面的纸张弄得满地都是。彭德怀平心静气地站着,静静地看着这些。当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回北京待审。时间已过去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彭德怀再一次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无法忍受,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他从自己的日记本E撕下一张白纸,写好后认真地叠成方形,放在自己的眼镜盒里,然后叫来哨兵,让他替自己转交出去。彭德怀在信中写道:
主席: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在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这封信经层层转送,最后终于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在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宣读了这封来自“另一种生活环境”的信。信中,彭德怀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话。
3月6日,彭德怀被转移到距北京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干部队监护。这里管得更严,大门有卫兵守卫,囚室前有哨兵,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彭德怀的囚室里还安排了一名哨兵,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进行记录。看着四周的环境,彭德怀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在这里是坐监狱。”哨兵见他嘴里不停地说话,就过来干涉。彭德怀对着哨兵拍腿感叹道:“今年我已经被撤职8年了,这8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冬天将至,彭德怀却只有一件破棉袄,一条破棉裤,身上没有换洗的衣服。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只得让哨兵给借来针线,然后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自己缝补。由于囚室里光线不好,手时常被针剌出了血,他放在嘴里吸一吸,又开始自己缝补起来。
4月,彭德怀借着囚室小窗透进来的亮光,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在信中,他详细地谈到了自己被抓来北京的经过。对于当时报纸上不断批判他在西南大三线搞翻案活动,收买人心,妄图兵变等诽谤都进行了一一的驳斥。他在这封信的末尾写道:“……我到西南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做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信发出去后,仍然是石沉大海。
20天后的4月20日,彭德怀再次提笔,不过这次他不是给毛泽东写信,而是给周恩来写信。彭德怀明白。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周恩来所能解决得了的。他在这封信里没有谈到个人的事情,更没有谈自己此时此刻所受的苦难,而是向周恩来汇报他在三线建设中所看到和担心的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四川石棉矿的矿碴被任意地堆放在大渡河两岸,被河水长年冲击,流失严重的问题,为此他过去曾向西南局的领导同志做过汇报,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视。彭德怀在信中还分析了这种矿碴的利用价值。认为可以加工成钙镁磷肥,这种肥料成本低,肥效高,对于周围的农民种田很有好处。因为当地属于大山区,农民种地靠天然肥,外面的化肥很难运进去,就是运去了成本也很高,农民买不起,应该加快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是有利于工农联盟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搞了工业,丢了农民,得了财富,失了人心。彭德怀在信的末尾对周恩来说:“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你,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祝你永远健康!”信的署名为“石穿”。
唯一敢向姚文元开战的人
自从给毛泽东写了信后,彭德怀总是坐立不安地等待着。每当有警卫战士在外面走动,他都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满怀希望地看着外面。就这样,彭德怀每天都在囚室的窗口等回信,可是一直等了8年,也没有等来。
就在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写完那封信后不久,一群“红卫兵”冲进来,拿出一张《人民日报》让他学习,并对他说:“读后要写心得”。这些人走后,彭德怀躺在床上,翻开那张报纸,只见赫然地印着几个大字《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对“周扬”这个名字,彭德怀是熟悉的。这个既不管枪,又不管粮,更不管权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两面派”了呢?他觉得奇怪,便认真地读起来,读着读着他感到气愤了,文章中那些杀气腾腾的话,根本没有一点根据。这时彭德怀才翻过来看了一下作者的名字,这一看不打紧,他气得两眼圆睁,将报纸扔在桌子上,骂道:“又是这个姚文元!”
自从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之后,彭德怀便记住了这个名字。发表如此重要的文章,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占着如此大的版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彭德怀从自己熟悉的人中去搜索,怎么也没有这个人的影子。彭德怀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个姚文元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他断定这一定是一个“投机者”,一个钻进革命队伍里来的内奸。
几天之后,那群给他报纸的“红卫兵”来了,他们对彭德怀说:“怎么样,你对姚文元的文章有何看法?”彭德怀说:“没有看法。”这些“红卫兵”一听,立刻生气地说:“你真是一个花岗岩脑袋,你同周扬是穿一条裤子的吧?”彭德怀一听,生气地说:“你们了解个啥,姚文元的文章我读得不多,但大都是诽谤之词。我与周扬根本就不太熟,但从来也没听说他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呀,写文章最起码也得实事求是吧!”“红卫兵”一听说:“你到底写不写读报心导?”彭德怀说:“这个心得我不能写。”“红卫兵”冲上来就要动武,被守卫的战士拦住了。彭德怀说:“你们不要强加于人,宪法上早有规定,他姚文元有写这篇文章的自由,我彭德怀也有不写这个心得的自由。”“红卫兵”被彭德怀说得哑口无言。过了一会儿,彭德怀说:“我还是决定要写的,不过不是你们逼我写的那个心得,而是另外的一篇文章,你们给我拿纸来。”彭大将军手握着笔,铺开稿纸,给姚文元写了一封信。在“文革”的非常岁月里,在全国所有被姚文元写文批判的人中,彭德怀是唯一一个敢向姚文元进行反击的人。在信中,彭德怀这样写道:
姚文元同志:
读了3日《人民日报》:《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同志要我对其中一段表态度。即“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到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实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在特殊的年月里,有谁敢向正红得发紫的姚文元开战?身陷困境中的彭德怀就敢于拍案而起,以笔为枪,向姚文元宣战!1月6日,彭德怀的信被送到了专案组。专案组的人看了之后,立刻转到康生、戚本禹手中。康生读后生气地将那封信往桌子上一扔,说道:“这个彭德怀,就爱写信,庐山上写了信,犯了罪,到现在都还不肯改。”戚本禹说:“这哪是在写信,简直就是在翻案。看来他还没有认罪,还得让红卫兵小将们来批斗他,让他真正地低头认罪!”戚本禹将彭德怀写信“攻击”姚文元的“罪行”记在心里,除了发动“红卫兵”对彭德怀进行批斗外,他在讲话中处处将彭德怀作为修正主义的靶子来进行打击。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戚本禹在北京做了长篇讲话,这个讲话的题目叫人听后十分奇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这篇讲话。彭德怀看了这篇讲话后有些哭笑不得,觉得这真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建军纲领了?戚本禹在这个讲话中杀气腾腾地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戚本禹的讲话,句句如刀,都是冲着彭德怀而来。对于戚本禹这个人,彭德怀同样不熟悉。但是怎么同那个姚文元一样的口气?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戚本禹和姚文元是一伙的。彭德怀接着看下去,他在文章中发现了一连串的人名,这些人名是: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在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彭德怀认识的,特别是彭真,当时的地位很高,自己到三线去工作,还是他代表毛泽东找自己谈的话,这样的人怎么也成了反革命?那个写了《国歌》的田汉,怎么也成了坏人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唱这个坏人写的《国歌》?彭德怀百思不得其解。他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用笔重重地划了一道又一道粗线。顺着这些人的名字看下去,彭德怀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他被点名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了这些“黑帮”的“头子”。
彭德怀心中不由暗暗叫苦,自己犯了错误,却一下子连累到这么多同志。而且有的人自己连话都没有跟人家说过一句,特别是那些文艺界的一些人,跟自己从来都未打过交道,竟然也被押上了自己的这辆“囚车”。他用笔在自己的名字下面重重地划了一道。划完之后,他长长地喘了一口粗气,将那张报纸扔在地上。
此时的彭德怀更加确定地感到最后风暴的即将来临,那同样意味着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伴随而来。他躺在床上,用沙哑的喉咙唱起了《国际歌》。歌声中,他的耳边仿佛想起了千军万马的呐喊,眼前又浮现出血与火战斗的画面……门外看守的哨兵透过门上的小洞,一直关注着彭德怀的一举一动。根据要求,他们要在《看守日志》上记下了彭德怀的所有举动,直至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