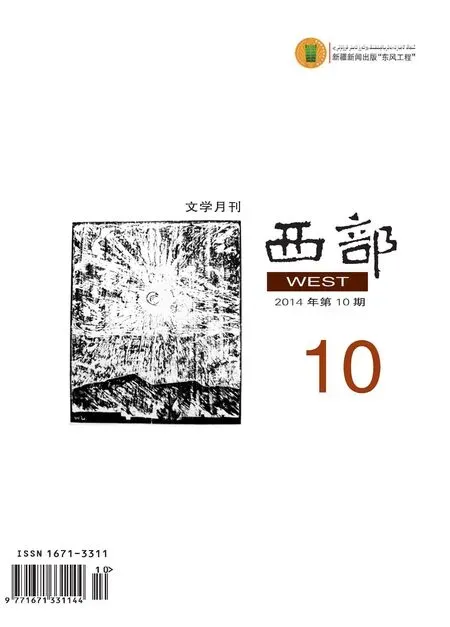故乡忆碎
谢宗玉
什么是家
初雪来临了,雪粒子从檐瓦间蹦跳进来,打得楼板沙沙作响。
来雪的晚上,母亲的叹息和儿子的兴奋也同时到来。雪停的早晨,母亲拿一个簸箕上楼扫雪,儿子就奔出去与村里其他孩子堆雪人,打雪仗,玩得忘乎所以。村前村后,快乐的童音喊成一片。母亲忧郁的脸上也就有了一丝欣慰的笑。
收了笑的母亲依然一脸忧郁。果不其然,雪融之后,寒风寻踪而至。寒风从去年熟悉的门缝里、窗缝里、墙缝里钻进来,一下子就把家里稀薄的温暖掠走了。寒风熟门熟路地把这个家当作了过路凉亭。儿子和女儿开始在夜里冷呀冷呀地哆嗦着叫唤。父亲和母亲就寻来所有的旧纸将来风的隙缝糊住,但寒冷似乎已侵占了这个家的心脏,温暖再也不肯返回。这个家急需一炉不灭的炭火,与寒风营构的寒冷对抗。
寒风终于也要喘息,天突然放晴,父亲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到十几里外的后山烧一窑木炭回来。母亲闻鸡起床烧饭。一大早,父亲就带着七岁的儿子上路了,留下母亲在家照看三岁的女儿。
把锋利的柴刀从腰间解下,父亲左劈右砍,杀出一条通向茂林的路。伐木声和父亲的吆喝声开始在静日的空山里清脆响起。锋利的柴刀去芜存精,一根根圆木就从父亲的手中递到儿子的稚肩,儿子的任务是将圆木运到窑边。
山鸟啼归时,父亲回到窑边,发现刚才空旷的窑坪这时已垒成了一堆“柴山”。身强力壮的父亲惊讶的不是刀锋之利,而是儿子稚嫩之肩的负荷能力。父亲心疼地扒开儿子的衣领,虽然隔着几层布衣,儿子的稚肩还是磨得又红又肿。父亲把一口口水吐在儿子肩上,然后用手揉揉。
父亲赞许的眼神是对儿子劳动的最大赏赐,儿子一时豪情万丈:干脆把火烧起来。父亲也仿佛回到了奔放的青春,答一句“行”!就将这个年纪应该考虑的事情全抛到了脑后,譬如饥饿来临,天色近晚;又譬如月初夜黑,归路崎岖。
在寒风中猥琐了十几天的男人终于在劳动中找回了自信。父亲扬刀断木的时候,儿子就将断木运到窑门边。父亲进窑装木的时候,儿子就在四处寻抱烧火的干柴。
夜幕降临时,父子俩将一切准备就绪。父亲让激动不已的儿子划亮了一根火柴,火柴点燃了熊熊巨火,火焰照亮半壁山岭,也映红了父子俩喜悦的脸庞。火焰在宽大的火洞里呼啸着舔进幽黑的窑口,就像舔进了父子俩寒冷已久的胸膛。再没有什么比在寒冷的冬天点燃一堆大火更让人忘情的了,再没有什么比在寒冷的冬夜保持一场大火更让人专注的了。火光之中,父子俩虔诚的脸庞是一副超然物外的表情,完全已忘记了家中的母亲有怎样一副盼归的心情。
日头依山岭时,母亲就背着女儿在村口望了又望。早晨母亲没有往父子俩的口袋里塞干粮,就盼他们饿了之后早早回家。母亲知道父亲干起活来就会忘记一切,总要把一件事弄得妥妥帖帖才记得回家的路。母亲已习惯了父亲这副脾气。但今天不同,今天是七岁的儿子第一次承担男人的重活,父亲应该懂得早早地把他带回家,以防他第一次就丧失对劳动的信心和兴趣。但现在日头都落山了,还不见他们的踪影,母亲的心开始被一种说不出的情绪揪着悬吊起来。惶惶然的母亲对自己说,做饭吧,也许做好了饭他们就回来了。母亲把晚饭做好后,父子俩依然没有回来,而黑夜却来到了村庄,伴随黑夜而来的还有轻微的寒风和凉凉的湿气。寒风在檐角边呜咽,像一支不祥的唢呐曲,母亲的心一跳一跳地在胸腔里舂米。这么黑的夜,这样陡峭的山路,让第一次出远门的儿子怎么回家呀?母亲再也没法在家呆了,给熟睡的女儿掖好被角,寻了一盏手电出门了。
母亲心慌意乱地匆匆上山。母亲的手电光在黑沉沉的夜色里萤光般渺小。每一丛摇晃的灌木都让母亲的心惊惊乍乍,每一只窜飞的山禽都让母亲的魂纷纷扬扬。而母亲的希望总是在手电光照清路前黑影的一刹那间,一次次破灭。
山路多歧,母亲就选择父亲最熟稔的路走。母亲以为凭借自己的直觉就能找到父子俩。母亲就这样翻山越岭,像一只母兽寻着亲人的气味一路而来。
母亲循路前行时,山坳窑口火洞里的大火依然熊熊。只是烧火的只有父亲了,又倦又饿的儿子像只猫咪偎依在父亲脚下睡着了。火光映照着他甜甜的睡脸,温暖营造他甜美的梦乡。在梦中,儿子看见自己捧着一团巨大无比的火送到母亲手中,那时的母亲是一脸神采奕奕的笑。
不靠理性指引,无路可走成了母亲最后的归宿。站在林茂木深的山中,孤独、恐惧、担心、委屈一齐朝母亲袭来,母亲这才发现自己竟是一个人独处黑夜荒山之中。惊恐无比的母亲突然从喉咙里喊一句:根生——,根生哎——!
空山夜静,母亲的呼喊像林间响箭直射夜空,群山为之应鸣,“生——哎——!”声音如涛似潮,重重滚过群山,渐遥渐远渐无。母亲把自己吓呆了,她没想到空山回音声势会如此浩大!一声呼喊,几乎将整个山林惊醒,一林子夜鸟都扑棱棱飞起,盘空喋喋长啼。
母亲再不敢喊第二声了。根生是儿子的乳名,母亲很后悔将儿子的乳名喊出来,若是让山精野怪听去了,以后寻着儿子的名字前来索魂那可不得了。这一声呼喊,甚至像是已把儿子的魂魄抛向了夜空,被四周的山精迅速撕碎,你一点我一点地瓜分带走。
恢复理性之后的母亲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山路蜿蜒多歧,她怎么知道哪一条是他们父子回归的路呢。也许父子俩早从别的山路回家了。母亲只好跌跌撞撞往回奔。跌跌撞撞的母亲突然发现寒风已把石头上的湿气冻成了滑溜溜的薄冰,山路像打磨了一样。焦虑就再度笼罩了母亲的心,母亲怕父子俩万一还没回来,这样的山路又该如何走啊?
果然,父子俩真没回家。母亲推开门时,家中只有被寒气冻醒的女儿在撕心裂肺地啼哭,母亲急忙忙跑过去,连女儿连被子一把抱起揣在怀里,心疼地哄着她继续入睡。
而那时窑前的儿子却被父亲拍醒。窑中圆木已经烧燃了,原先幽黑的窑口现在已火红火红,再不需要在火洞里加柴引火了。是该回家的时候了。只要隔几天来打开窑门,就可取出一窑上好的木炭。整个冬季就不用犯愁了。
父子俩开始趁夜色回家。夜漆黑而深沉,路崎岖而漫长。儿子在前,父亲在后,两人左手各拄一根拐杖,右手同牵一段藤蔓,就这样一步一捱,互相应答着向家慢慢靠近。好在再黑的夜晚,总会有些微天光,山路的薄冰既是回家的障碍,又是回家的指引。实黑的是灌木,虚黑的是夜空,那一条若有若无的微白则是通向回家的路。
时间在冬夜里停顿,精疲力竭的父子不知走了多久才看到村庄里母亲点亮的那一盏微灯。狗吠是寒夜最动听的天籁,从狗吠声中可以测出与母亲那盏微灯的距离,狗吠声声可以证明距村庄不再遥远。
微灯下的母亲支着下巴在等待那一场归来,灯花微微的爆响也会惊吓神思恍惚的母亲。母亲在等待中感到寒夜的时流也被冻结成冰,是那一声声狗吠和鸡鸣,才将神游的母亲从凝滞的时流中一次一次唤醒。
那等了千年万年的推门声终于“吱呀”响了。见到母亲的儿子,一扫全身的疲倦,兴冲冲叫道:妈,这个冬天我们再不用怕了!见到儿子的母亲没来得及答话,哭声就先侵占了她的喉咙。
放声大哭的母亲动作简直疯狂,她先是一把将儿子拉进怀中,被莫名其妙的儿子用力挣脱后,她又冲到父亲面前,拼命用手擂他的胸膛。
这个场景,二十年之前的儿子记住了却没法理解。二十年之前的儿子在那个冬季,只体会了辛勤的劳动可以换来在寒冷的冬天围着火炉,对遥远的春天进行美好的构思和幻想。
鬼节扶乩
农历七月初一是开鬼门关的日子,就像拉闸开洪一样,鬼们可以在阴间阳界四处游动,舒展舒展筋骨,走访走访亲戚,了一了尘世未了之缘。
鬼们出来后,再霸道的活人也变谦卑了,就说耀武扬威的村长吧,这时也撮一炷香,神情肃敛,在神龛下揖了又磕。胆子再大的汉子听了婆娘的叮咛,也会尽量在白天干完该干的事,免得黄昏来临要走夜路。
黄昏来临后,家家户户关门闭舍,早早上床,以免撞了坏鬼。鬼也有好鬼坏鬼之分,好鬼就是家鬼,就是家族的祖先。入夜后,去世了的祖祖辈辈就会聚飘在房屋的上空,以对抗来犯的恶鬼,保卫儿孙的安危。恶鬼生前要么就是恶人,要么就是暴死,它们即使做鬼也不安分,会趁这个放风的端口,在阳界到处惹是生非,拉几个心无敬畏的莽汉给他垫背。恶鬼不敢来犯人家,就只好在旷野东游西逛,逮谁是谁。
我家是个大族,祖祖辈辈若都回来,恐怕房子的上空都容纳不下呢,所以我并不害怕恶鬼在我睡后来犯。早晨起来,摸摸身体的各个部位,它们都好好的还在,我就知道,昨夜的保卫战又以我家祖先胜了。只是在睡梦中我并没有听见刀剑之声,想必鬼战是无声的,就像用气功打架的人一样。
鬼节来临后,村庄到处都是一些说不得碰不得的忌禁,最让小孩受拘束的是,再不能下河下塘洗澡了。水鬼是最厉害的恶鬼之一,但它并没恶相,只潜在水里,拽着它最喜欢的小孩的腿往深水区拉,然后把小孩从阳界带到阴间。
母亲说,家鬼本来是斗不过恶鬼的,但家鬼每天有后人给它们供饭烧纸,将它们养得精气神都足足的,恶鬼饿着肚子跟他们打架,自然就打不赢。我家每天也给祖先供饭,这些事都由母亲一人操办。母亲做好一桌上等的饭菜,洗手焚香,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口里念念有词,大概是请自家的祖先上席。母亲做这些的时候,我、父亲、小妹就神色紧张地靠墙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以免与祖先撞个满怀。祖先在世时一个个脾气都好,可不知做了鬼后性情是不是变了,就怕它们为一点小事见怪,拂袖而去,那我们家的夜晚就无鬼照看了。
阴间与阳界相反,阳界的白天是阴间的晚上,所以桌边焚香的同时还得燃上一支红烛,要不然祖先就看不见吃饭。香烟袅袅青蓝,烛烟袅袅炭黑,饭气袅袅灰白,都积在低矮的楼板下,像祖先的灵魂在飘飘荡荡。我想,祖先们都太客气了,只看几眼,却并不入席,桌上的菜饭分明没动半分。母亲却说,祖先们做鬼之后,只吃些香烟烛火饭气就够了。若真是这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祖先们天天在家做客就好了。家里有了客鬼,饭菜自然会好,到最后真正能大快朵颐的,还是我和小妹。
该给家鬼吃的已给它们吃了,该给家鬼花的已给它们烧了,这样就到了十五——鬼节的最后一天,家鬼们就要收拾行装上路了。可毕竟不放心,谁知道它们是否真的吃了拿了?怎么办呢?就去邻村的扶乩场去问问吧。
扶乩是沟通阴阳两界的法事。记忆中的乩是一根弯弓似的溜木,像一个小型的牛笳,先由一个巫师收着,到七月十五再拿出来。扶乩得由妇人,男子阳气太重,鬼魂不敢附乩。就算妇人也不是所有的妇人都行,得极阴极柔极慈之人,一个村子能找一两个就不错了,而我外婆就是其中的一个。
把一张八仙桌摆在古老厅屋中央,我外婆和另一妇人各执乩柄站在桌边,四面八方的乡亲把厅屋挤得水泄不通。凡是想跟祖先通话的,都可上前默念祖先,焚香烧纸作揖。过不了一会,被默念的祖先就会飘然而至,附在乩端。那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我外婆她们的手会随着弯乩不由自主地摇起来。
阴阳两界大多只能做简单的是非问答,乩身左右摇晃为非,乩身上下摇晃为是。
是××公公吗?乩身上下摇动说是。
在那边过得好吗?乩身上下摇动说好。
每年烧过的纸钱都收到了吗?乩身上下摇动说收到了。
后人知道了这些,往往喜极而泣,很快抹着眼睛心满意足地退下了。也有问什么,乩身都左右摇动的。后人知道先人在那边过得不好,一伤心,就忍不住抚案恸哭。一幕幕人鬼悲喜剧就在古老厅屋上演。我想,后辈哭时,祖先一定也在哭泣,只不过祖先的哭声我们听不到,就像祖先的影子我们也看不到一样。
我不知祖先是匿迹在水泄不通的人群,还是飘浮在厅屋的上空?如果是飘浮在厅屋的上空,它们的头一定都是朝下的,就像瓜棚架下悬着的倭瓜。这时若能显形,那情景该多么滑稽!这么想着,我突然一个人大笑起来,我笑得在人堆里乱滚。一厅屋父老瞪着我,面面相觑,都问我看见什么了?我说,你们每一个人的脑袋上面都顶着另一颗脑袋呢。大伙哗然色变,都说我有天目。事实上我是瞎猜的。
问完乩事,很多人家又连夜赶制了一批纸钱纸衣,烧给被恶鬼洗劫一空的祖先。还千叮咛万嘱咐,上路时一定要结伴而行,以免又被恶鬼打劫而去。强悍的祖先保护懦弱的后人,而懦弱的祖先被强悍的后人照顾,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就算阴阳两隔,大家也是精血相连,谁又会抱怨谁呢?
送别祖先,小孩们压抑紧绷的心弦终于放松了,该怎么玩还怎么玩。而大人们却不,大人们的心里会空空落落好一阵子。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大人的心思,因为我自己也长大成人了。长大成人后对时间我就有特别的感受,时间就像一层一层的玻璃隔板,冷漠而无情。每个亲人死后,时间就在他(她)身后竖一块玻璃隔板,将我们各隔一方,以后我们就只能靠回忆和梦境来见面了。而一年一度的鬼节,万能的玉帝抽去了时间隔板,使再漫长的时间也能成为一个可以来往的通道,这对活着和死去的人来说都该是多大的慰藉啊。只有这时,我们才不会感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才不会感到是活在时间的孤旅之中。
蜻蜓
钓鱼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群红蜻蜓在我的眼前和头顶安详地飞。这种记忆不是来自童话《小猫钓鱼》里的某些细节,而是童年时我常遇到的事。
夏天里,我常去荷叶塘钓鱼。荷叶塘是个野塘,没有荷叶,水面上飘满了浮莲。我坐在岸边,把杆线甩出去后就静静地等待。那一般是些初晴的日子,阳光温热而不炽烈,神思才恍惚一下,红蜻蜓就不知从何处而来,团飞在我的周围。那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空气里响着薄翼振动时细微的摩擦声,鱼情看好的时候,我一般置若罔闻。若久等无讯,而这时倦飞的蜻蜓又要停在鱼杆尖头,我也会动心。我将鱼杆一点一点地缩回来,待红蜻蜓伸手可及的时候,就猛地一抓。但往往是不成的,红蜻蜓太机敏了。而这时线那端的浮标却不见了,以为有鱼,就猛提鱼杆,但杆成弯弓,却不见鱼跃,才知钩那边与浮莲那细长的茎搅在一起了。
钓鱼的过程是一场静坐的过程,那应该是老人的爱好,不知那时我怎么就迷上了此道?童话里的小猫还有老猫带着,而我,往往是一个人呆在四周静谧的荒塘边。没有风,对面山林叶子上的碎光也像凝固了一般。天空没有云,湛蓝的底色上那枚太阳也像走不动似的。水面平静,满池浮莲妖娆,像一副定格了的画。我甩杆的时候,水里的杆影还曲曲折折的,像一条要往深水扎的蛇儿,但只一会儿,就倦了下来,恍若冬眠。然后我就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一副稻草人的模样在水的深处。我翕动着鼻息,闻到空气里有沉沉的花香,我眼皮一合,就有睡的意绪了,整个眼前的一切,竟似梦魇一般。这时,红蜻蜓飞来了,红蜻蜓是那个静止的世界里唯一轻快的事物。也许是因了它们的团飞,我才挨过寂寞的童年。又或许是因了它们安静的飞翔,成年的我才变得这样寡合于人。谁知道呢?我一直认为我现在性格的形成,与童年时每一件琐事,都有千丝万缕的牵连。荒塘并无多少鱼儿,那些个晌午,我常常是空手而归,要么就只有一两尾二指宽的小鱼,用一根小枝串着,提在手上。由于距钓上来的时间的确隔得太久,鱼儿已被阳光晒得硬邦邦的。母亲见我回来,也蛮欢心的样子,把两条小鱼拌上蒜叶,炒了给我与小妹吃。
是的了,小妹童年在干什么呢?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不知小妹那时候为什么没跟着我去钓鱼,而村庄里的其他小孩又上哪儿去了?
踏春
我们唱着歌,排成很长的队伍,在一个黯春季节,朝老峒进发。路是酥酥的那种,踩着软软的有弹性,却没多少沾鞋的泥。尚未春犁的田野里长着青青小草,几场雨后,有亮晶晶的水在田野里铺一层,人从旁边经过,就可以看见自己的小人影和高高的云天在水里移动。队伍中时不时有人伸手折一枝春花,悄悄插在前面同学的头上,惹得后面一串长长的笑声。有人顺手扯一片柳叶,噙在嘴里吹一声清脆的长音,惹得前面一串回头的笑脸。
老峒是故乡最有名的风景区,远远近近的山坡长满了青翠碧绿的茶树,在茶林的深处,还藏着一个神秘的洞穴。那一天,在全校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去这个洞穴探奇的。但黑漆漆的洞穴其实无奇可探,举着火把进洞后,我们很快就被薰得眼泪直流,四周的岩石模糊不清,稍远处的团团黑暗既在诱惑着我们,又在恐吓着我们。我们三五一群,一个拉着一个的衣襟,生怕会在这岔道繁多的洞中迷路,心脏跳得似小兔子在撞。我们也喊,喊得洞中声音一串一串在岩壁上撞来撞去,那袅袅余声就像撞着了一座古钟。火把很快熄了,我们再不敢往前走了。摸黑早早退出来,我们就围着小庙里的和尚,听他讲有关洞穴的古老传说。那时满山遍野的茶林里,这这那那都盛开着同学们的笑声。
从老峒回来,全校展开游老峒同题作文竞赛,我东翻西翻,参考了众多游记,终于写出了一篇自认为不错的作文。作文马上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认可,被推荐上去后,真的就获得了全年级第一名。获奖之后,作文被重新填一遍,贴在墙上示众。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校获得荣誉,那股高兴劲就别提啦。我一路兴冲冲地跑回家,扑门进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完后我又飞身出去,跑到东坡告诉正在伏头农事的爸。等小妹放学回家,我又急巴巴地迎上前。那天晚上妈妈还特为我煎了一个鸡蛋,颇有嘉奖的意思,小妹在一旁看着我吃,不妒忌,还抿着嘴笑,一副心悦诚服的样子。
那年我读初一。从此记忆里就多了一件温馨的事情。这么多年来,我只要一回忆当时的情景,脸上总会有淡淡的红晕和不由自主的笑意,然后再怎么阴暗的心情也会抹一丝亮色。我想,这与我现在走上以文谋生的道路也可能不无关系。而追根溯源,还是语文老师的推荐之功啊!如果没有他的推荐,留在记忆里的也许就只有游老洞这事了。而这事如果没有一个完美的结果,我又怎么会记得那么认真呢。获奖就像一只密不透风的玻璃瓶,把往事鲜活如初地保存在里面,让我常忆常新。
如果能让这份温馨的记忆一直伴我到死,那该多好。但在命运的云翻雨覆下,事情常常会突然展示出它的另一面来。若干年后,我与我的女友有了亲密接触。她是我初中同学。当我第一次吻她的时候,她嘤嘤哭了。她问我还记不记得那次游老峒。我就说,当然记得,回去后的作文竞赛我还获了第一名呢。她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我也记得……就在那个洞里,我被语文老师强行抱住吻了。那是我的初吻。我才十三岁……
女友再也说不下去了,她的眼泪一行行无声滑下。而她当年的语文老师就是我的语文老师!就像是从一场繁花簇锦的春梦中醒来,我突然发现自己是立在枝骨嶙峋的寒冬。
我终是没跟那个女友结婚。我也不再回忆那次春游了。即使偶尔想起,心中也是一种抽搐的痛。
永乐江
天暴热的时候,永乐江畔的安平大桥边就热闹了。下了课,太阳还没落山,学生们就一群群提着桶子,往河边走。那个季节,新绿开始变得无限的浓郁,阳光开始变得无限的明朗,跟随着,同学们的叫笑声也仿佛比冬天更富活力和生机。还有那一张张被阳光晒得红艳艳的稚脸,到现在还在我心中如花般灿烂开放。
河在安平大桥边被拦腰截断,上游波平岸阔,有湖的模样,下游则水流湍急,呈滔滔之势。我们游泳最喜欢在这里了,因为这一段水流最能逞勇。我记得每天都有胆大的,站在大桥的栏杆上,小小的身影一纵,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然后像箭一般扎入水中,水花团翻,半天才冒出一个头来。有时一连十数人接二连三跳下去,水花开一片,也开出一片惊呼和笑声。有更胆大的,则往下游的湍流里跳,仿佛一粒小石,投入翻腾的水流,根本听不到半点响动。待冒出头时,已被水流冲到十几米外的地方了,看客悬悬的心才算有了着落。
除从十几米的桥上往下跳外,还有其他两种逞能的方式。上游水深,就倒扎猛子往河床里摸石子,能摸出石子的,自然是水性好的。下游水急,就横渡江面。横渡并不很难,难的是在横渡的时候又不被水流冲下去,能在相对持平的彼岸上来,才算本事。
我记得我们洗澡的时候,对岸或远远的下游总有一些女生在漫步,她们多数时候在闲聊和看书,也有远远张望我们的时候,那时,一河子湿淋淋的头颅就更欢腾了,滚珠碎玉般的水花就一片一片地起而又起。我记得逆对夕阳,我们一般看不清她们的面容和眼睛,但她们清秀的目光,直到现在似乎仍可从时间的河面上直抵过来,穿透我的心灵。
那些日子里,快乐就像水边疯狂抽条的杨柳,心里那个舒畅,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然而悲剧,就像惊雷后的骤雨,说来就来。每年安平桥那段河面,总要在我们的快乐还没有完全舒展开来的时候,将我们的一个同伴带到真正的彼岸。死亡的气息就这样渗入盛夏浓郁的暑气中……然后是校方声嘶力竭地宣布禁律,然后是一河寂寞的波光在夕阳下延伸至远方。
在空白的记忆中度过夏日剩余的时光,直到秋雨至时,死亡的气息才连同酷暑一起被浇灭。经秋至冬,经冬至春,然后是夏季的欢乐重新生长,一河的笑闹声再次在水面盛开……
依旧是在欢乐还没到达高潮的时候,溺亡的悲剧又骤然而至……就像是嬉戏的麋鹿突遇猛狮,就像是初放的花朵突逢暴雨,无论怎么快乐的生命,说去就去了。死亡就像黄沙垅头的那一撮旋风,东一头西一头地乱嗅,根本没有规律可循。
许多年过后,回想往事,我不禁倍觉惊讶,在那样懵懂的岁月里,死亡怎么就把我撇在一边没管?事实上,有一次我的确是与死亡擦肩而过。我站在岸上,倒着头,插入水中,没提防就撞上了水中的乱石,我亲耳听见沉缓的撞击声从水中传过来,然后我的头就剧烈地痛起来。我以为我可能回不了岸,但我游上了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