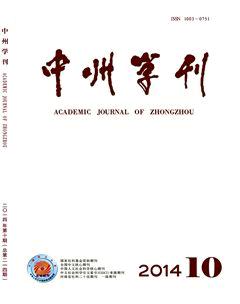微信:移动即时通信与新传播革命
摘要: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移动通信”是网络技术与移动终端革新的衍生物,其“内爆式”发展表征了新传播革命的结构性变迁及功能性转向,重构了以“融合”为特征的社交、信息和营销平台,弥合了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相区隔的传播交往关系,整合了大众媒体与自媒体分化的信息传播结构,创造了广告与商业入口一体化的营销模式。在这个熟人与生人,公共与私人,交往、信息与商业深切勾连、快速融合与转化的新型技术城邦中,自然与文化、人与机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得到修正,它们成为融合的共生体,其影响辐射整个社会结构、生活秩序及价值体系。
关键词:微信;移动即时通信;新传播革命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0-0169-04
自从新媒体技术深刻而广泛地介入人们的生活,传播革命的步伐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广播、电视、电影等曾经名噪一时的“新媒体”很快进入“旧媒体”的行列,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手机、iPad(平板电脑)、Kindle(电子书阅读器)以及与信息高速公路和先进数字化终端设备相伴生的博客、播客、微博、社交网站等等。“新”与“旧”的界定在高速发展和变迁的媒体信息技术面前变得困难重重,它们的相对意义取代了绝对意义。而“媒体”本身的含义也变得含混不清、难以辨识,人们越来越习惯用“新媒体”去标化所有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介、媒体技术、媒介应用,甚至终端设备。事实上,厘清“媒体”或“新媒体”概念本身似乎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认识这些基于媒体技术跃迁式发展的新生事物对于传播形式、传播途径、传播结构、传播交往关系等的变革和影响和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关系、政治形态、经济结构、文化观念所产生的普泛化作用,即它们作为新传播革命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说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等在这次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推广与使用”①的新传播革命中彰显出巨大的能量,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和世界,“从全球游戏规则到各国治理、统治方式,从科技创新到知识经济,从市场行为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②,那么随着中介电脑的传播向中介移动终端的传播之延展③,以国外的Line、WhatsApp、Kik,国内的微信(WeChat)、米聊、飞聊、陌陌等为代表的“移动即时通信”正在将这场革命推向新的高潮。④它重构了以“融合”为特征的社交、信息和商业平台,打破了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相区隔的传播交往关系,整合了大众媒体与自媒体分化的信息传播结构,创造了广告与商业入口一体化的营销模式,塑造了“信息机器”与人的新型结合体⑤。这场新传播革命即将从更深广的意义上重塑人们的社会生活甚至价值体系,将人们真正载入“第三媒介时代”⑥。笔者试图以“微信”为例,对移动即时通信助推的新传播革命实质进行解析。
从诞生伊始,微信用户就一直呈现几何量级增长的迅猛态势。微信依托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设备对移动互联技术的应用,将基于个人电脑的即时通信推送至移动即时通信的高新阶段,并不断改进和完善它的功能和用户体验。统计数据显示,从2011年1月21日苹果版微信首推,到2012年3月29日,短短433天,微信用户实现了从零到一个亿的增长;2012年9月17日,微信用户突破2亿,耗时不足6个月;截至2013年1月24日,微信用户激增至3亿,历时不足5个月;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的过程中。⑦微信用户的庞大规模和惊人增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移动即时通信”革命性的传播力量及其文化、政治和商业影响力。
一、中介化:现实与虚拟融合的社交平台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即时通信”技术首先构造的是一个革命性的社交平台,它既是对现实社交方式的改变,也是对虚拟社交方式的重构。它巧妙地将现实的传播交往关系和
虚拟的传播交往关系勾连在一起,消除了传统社交与新媒体社交的壁垒,形构了“中介化”的融合性社交平台。
首先,“移动即时通信”是一个融合现实朋友关系和虚拟朋友关系的综合性社交平台。微信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取“好友”,从而构建自己的交往圈:导入电话号码簿、导入QQ好友、导入Google好友、添加微信号、扫描二维码以及其他辅助方式,包括基于LBS技术(Location Based Service,定位服务技术)的“摇一摇”“按一按”“附近的人”“漂流瓶”等方式。这些途径决定了微信交往圈是由现实中的亲朋好友与虚拟空间中的“朋友”共同构成的。多数微信用户通过“通讯录”中“新的朋友”选项来建立最初的朋友圈,并不断扩充自己的朋友圈。在朋友添加向导中,用户可以快捷地找到电话号码簿、QQ联系人、Google好友中正在使用微信的好友,并发出添加申请,等待对方回应。电话号码簿中的部分亲人、朋友、同事、熟人以及QQ联系人中的部分好友往往构成了微信交往圈的主体部分。对于其他朋友,微信用户也可以通过添加微信号、扫描二维码(很多人甚至将二维码置于名片或者个人主页、微博、博客等之上)等方式进行添加。这些途径基本是在既存的交往关系和熟悉程度基础上来构建交往圈,尤其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密切相关,具有某种确定性和必然性。而“摇一摇”“按一按”“附近的人”“漂流瓶”等新途径则为微信用户开启了更为有趣、刺激和偶然的朋友交往体验,是对虚拟“朋友”的有效补充。“摇一摇”“按一按”可通过晃动手机或长按提示按钮来查找和自己同一时刻晃动手机或按按钮的微信使用者,“附近的人”可通过卫星定位搜索和用户地理位置相近的微信使用者,“漂流瓶”可随机打开某个陌生人传递的信息,而微信用户则可以自由选择这些“陌生的有缘人”进行通信联系、好友添加。丰富、多元、立体的交往途径使得微信用户的交往圈呈现一种以现实关系为核心的多向拓展结构,它并非稳定不变,而是随着用户的偏好不断调增和扩充,并将实现的交往关系和虚拟的交往关系进行整合。相比单纯的现实生活交往关系,它具有更大的开放性、灵活性、趣味性甚至冒险性。相比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等虚拟交往关系,它又显得更加真实、安全、私密,更突显主体性。在“朋友圈”里分享信息、关注好友、添加评论则类似于某种松散,但具有连续性的感情联络。尽管微信交往圈没有博客、微博和社交网站那么广泛,但是,正是这种选择性形塑了更为真实和可靠的社交网络和传播交往关系。事实上,博客、微博、社交网站中的“极化”现象(由于某种共同偏好聚集在一起,并形成偏激意见,甚至群集行为)、“虚假交往”现象(与过多的人建立交往关系,实质上跟大多数人没有真实、具体的联系)等已经开始暴露出对真实传播交往关系和社会文化的破坏力。
其次,微信朋友的交往方式融合了现实与虚拟的多元特征,超越了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真实虚拟”⑧。在微信空间中,朋友之间的交往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一对一交往”形态,即两个微信联系人展开同步或者异步的信息交流。二是“群组交往”形态,自主创建的小群体之间展开同步或异步的信息交流,如家庭成员、兴趣小组等。三是“朋友圈”形态,通过发布带照片的消息、链接与指定联系人分享信息、生活细节、情感体验等,信息发布人、联系人之间可以随时互动。四是“公众账号”形态,可以选择关注不同类型的媒体,接收来自它们的信息,并与之互动。这四种交往形态映射和整合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形态,同时融合了虚拟空间中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并置的传播交往结构,并将同步交流与异步传输糅合在一起。微信最奇妙的交往体验是既可以进行音频、视频的即时沟通,又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接收朋友、公共账号传送的资料,并且可重复浏览、收听、收看。这为用户创造了一个更加顺畅、自由、丰富和经济的社交世界。一方面,用户可以通过这个虚拟的社交平台获得类似现实生活中即时通话、手机短信、会议等的交往体验,并将其简单化、便捷化、经济化。另一方面,用户还可以借助这个虚拟平台获得不同于现实生活层面的交往体验,如组建一个家庭群组,随时获取来自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家庭成员的点滴信息,与他们维持一种生活与情感联系;在“朋友圈”通过随手拍、随手转、随手写与更多朋友分享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生活细节、生命与情感体验等。这些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对位模式的传播与沟通途径解决了用户在生活世界遭遇的传播障碍、表达不畅、沟通困难以及时空局限等问题,开启了信息传播、情感表达、沟通交流的新时空场域。
最后,微信的信息交流融合了多维样态,打造了更为个性化和人性化的信息方式。无论是朋友之间的沟通,还是群组之间的交流,只要手持设备能够连接互联网,微信用户就可以通过文本、表情、语音、影像,甚至实时对讲和视频通话等多维样态来展开。可以说,微信打通了移动电话、手机短信、聊天工具、电子邮箱、微博等产品的界限,综合了现实交流与网络交流的所有信息方式,既弥补了单纯语音交流的抽象性、单调性,又克服了单纯文字沟通所存在的背景缺失、情感隐匿等问题。并且高品质的音频、视频交流极大地提高了互动的品质,甚至使“仿真交流情境”成为可能,遂将中介微信的传播交往推向更为真切、深刻的层次,规避了间接互动、延时互动、屏障式互动可能造成的信息损耗、扭曲、变形等。⑨它使得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的交流变得灵活、多变、丰富、立体、有趣,更加个性化和人性化。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电子媒介的互联性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然而,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即时通信”却是这一观点反向延伸的最佳代表。微信既不是“现实社交关系”向互联网空间的简单迁移,亦不是“虚拟交往关系”被生活世界的纯粹收编,而是在二者融合的基础上生产的新型社交“时空域”以及与之相契合的“即时深度交互式传播交往”⑩关系。微信不仅解决了现实生活中社交范围狭小、传播交往方式有限、时空局限性强、沟通成本高昂等困境,而且克服了众多虚拟社交方式过度庞杂、开放、自由所带来的互动障碍、信息虚假、隐私外泄、自我丧失、网络暴力等问题,塑造了更为真实、可靠、高效的社交平台,自主的社交关系和人际沟通实体。
二、内驱传播:大众媒体与自媒体融合的信息平台
对于广大用户而言,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即时通信”工具的重要功能不仅在于维系“朋友”沟通,延伸交际圈,更在于获取和使用各类资讯,满足自身的信息诉求。微信等先进通信工具将大众传媒与自媒体的丰富资源融合于一体,并将选择权和互动权移交“受众”,将信息推送载入一个直接、高效的内驱传播阶段。所谓内驱传播是指为用户内在需求所驱动的传播形态。
在微信平台中,信息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微信朋友,一类是“公众账号”。微信朋友可以通过点对点方式,或者在“朋友圈”通过点对多方式将文本、图片、音视频等各类信息传递给自己的好友,甚至将意见、建议、感受、体验、评论一并发送,这种基于“强关系网络”的“直接现实信息”是关于周遭生活世界的意向性描抒,因其接近性和情感张力而为用户所需要和依赖,并具有类人际传播的强大效果。
然而,这部分信息毕竟是有限的、非专业的、个人化的,更多是生活体悟、个人絮语、情感宣泄,无法满足用户对多元、客观、专业、有效资讯的需求。“公众账号”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它是基于对“直接现实”的补充原则而铺设的更为广阔、有效和精准的媒体通道,大众传媒和自媒体在这里实现了真正汇流——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偏好任意搜索和关注不同类型的媒体资源,并与之互动。用户仍可以看到“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南方日报全媒体”“南方都市报”“时尚生活导报”“半岛晨报”等大众媒体的身影,接触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资讯、娱乐和知识。只是,它们已更换了新的面孔——精准的内驱传播将其装扮一新。一方面,它们的信息推送形式更加精准地瞄准用户的内在需求。虽然这些“大众传媒”的目标受众群体仍然是广博、绵延的“大众”,然而就用户体验而言,更类似“一对一”的新型信息传播和交往方式。它们通过点对点的传播形态将即时更新的消息直接推送到用户的移动终端设备上,用户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空间查看新消息、回顾历史记录、互动、转发或取消关注。另一方面,信息“进入”形式更加精准地贴近受众诉求。这些“大众传媒”并非它们“母体”的简单翻版或压缩版,它们中的一些成员甚至不存在所谓的“母体”。它们更多是按照新媒体技术特征、先进终端设备的传播特性,转换了新的信息制作方式和内容组构模式。因此,与其说它们推送到用户终端设备的是一些“强迫性阅读”的信息模块,不如说它们仅为用户准备了一些信息的“入口”和“版图”,简短的标题、微缩的图片等成为下一级信息的链接“入口”。信息被分割为多个层级:标题、故事梗概、背景介绍、关联信息、图片、音频、视频等。是否打开下一级“入口”,深入关注?是否转到相关链接,拓展浏览?是否阅读文字,观看视频,收听音频?这一切都取决于用户的自主选择。内在诉求驱动的自主选择成为移动即时通信信息服务的亮点。
在微信空间中,还活跃着一大批“自媒体”,如“新闻实验室”“香港媒体记者”“自媒体段茗舰”“新媒体前沿”等。这个庞大的集群同样具备信息推送形式和信息“进入”形式的针对性。或许它们在新闻制作与播报方面并不具备“媒体专业性”,缺乏科层制的组织机构、专门性的工作人员、统一的新闻价值标准及职业化的伦理尺度,但是它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更加专门化,是基于特定主题、取向、趣味等自发组成的小众传播信息源。它们缺乏大众媒体的权威性、可信度、影响力和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因此,它们更着力于打造某种“特色”,特别是大众媒体缺乏的“特色”来吸引特定微信用户的持续关注,赢得信任和美誉度。如“新闻实验室”的功能介绍是:“这里是方可成的新闻实验室。实验需要创新精神,我将跟踪全球新闻业前沿动向;实验同样需要遵循自然规律,我的实验室里最重要的定律是‘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该媒体推送的消息包括《为什么我们需要网络素养》《密苏里新闻学院学生的数据新闻学习笔记》《雪崩:重新定义特稿》等。它的目标受众群体锁定在传媒领域的学生、教师、研究者、从业者等。也就是说,微信自媒体可以为用户的特定诉求和偏好提供更为“精准”的信息、资讯和服务。
大众媒体与自媒体的关系曾经是新媒体技术腹地的一场边界战争,其争夺的目标一直是信息生产、受众依赖、合法性的领域。但是,移动即时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它们的分歧,并在维系它们之间张力的前提下开启了它们的共生之路。在这里,用户既可以了解大众传媒体传递的最新资讯,也可从不同形态的自媒体获取个性化、专业化、独具特色的信息、知识或者服务。用户的自主选择将媒体的使用与满足功能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用户实现了内驱选择和获取信息、资讯的新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即时通信用户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和重新赋权。
三、叠加效应:广告与商业入口融合的商业平台
新媒体技术无限延展着它在传播交往方面的巨大能量,也不断彰显出它在商业领域的潜在价值。丹·席勒在《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中讨论了“永久联通”的移动产业,“因特网泡沫破碎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供应方压力的新迹象。不断寻找新的高利润投资出口的巨大资本浪潮,牢牢抓住了移动通信行业……报纸、杂志、电视,当然还有因特网似乎毫不费力就达成了统一意见,一致认为无线是最有前途的新领域”。尽管丹·席勒这番话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的批判立场来说,但也从一个层面彰显了“移动通信行业”的广阔商业前景。然而,如何真正地将传播交往能力转化为商业价值?这是困扰许多新媒体产品的重要问题。坐拥巨大用户资源的微信,或许为新媒体传播与商业的联姻开敞了新的可能性。微信有五种营销模式:一是依托“附近的人”的“草根广告模式”——即通过签名档“广告位”将广告信息推送给正在查看“附近的人”的用户。二是基于“漂流瓶”的“品牌活动模式”——即通过大量抛出“漂流瓶”,增加用户“打捞”机会,帮助合作商家推动广告信息。三是借助“二维码扫描”的“O2O模式”(Online To Offline,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即通过二维码识别,使商家和用户建立起联系,形成“熟人”形式的SNS(Social Network Software,社会性网络软件),拓展会员制度、推广商业宣传和折扣信息。四是立足于开放平台和朋友圈的“社交分享模式”——即通过开放链接接入第三方应用,或者将应用的LOGO放在微信附件栏,方便用户在会话中进行调用、选择并分享内容。五是运用公众平台的“互动营销模式”——即通过公众平台向加关注的用户点对点地推送资讯、产品及活动信息,并开展一对一的咨询、互动等客户服务。不仅如此,微信还与财付通联合,开辟直接向好友转账、摇一摇转账、二维码扫描支付的通道,接入移动游戏;摇一摇功能也可将用户直接导入商家页面,或者进行歌曲搜索等,进行有效的线下聚合。
可以说,微信打造的是一个超越单纯广告推广模式、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规则简单、网络层次明晰的开放性商业平台,其特点有三:第一,该平台建立在强大的社交和信息平台基础上,丰富的用户资源已经被悄然转化为潜在的客户资源,而用户的使用习惯与依赖性则为商业宣传提供了可能性通道和有效性保障,因为,微信已经覆盖了庞大的用户群体,且其具有明显的高端化倾向(微信用户中大多是持有先进移动终端设备、消费能力较强的青年群体)。第二,微信是以熟人关系为核心、耦合性选择为补充的社交和信息平台,是现实社交关系在虚拟时空中的完美拓展和延伸,用户在这重时空中更倾向于追求一种类“真实”的存在——使用实名或为朋友辨识的化名;展示生活的细节、流露真情实感;关注最能满足自身诉求的公众账号;等等。并且,他们之间的信息交往打破了中心与边缘或科层制的结构方式,呈现出更为亲密、民主、平等与自主的特征。这无疑为“大众营销”“病毒式营销”的有效结合奠定了有利条件。因为,类“真实”的微信生活构造的是一个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为辅助的传播交往结构,商业信息在其中的推广可以借助大众传播的广阔覆盖性、人际传播的强大影响力以及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补充效益取得叠加效果最大化。第三,微信能够助推的不仅仅是广告和宣传信息,它本身就是一个理想的商业入口。一旦微信用户与商家建立某种联系,商家就可以将入口链接置于推送信息或者附件栏等位置,让用户直接跳转到自己的网站或主页,进行更深入的浏览,甚至即时采取购买行动。而“扫描二维码”更将线下与线上的商业互动融为一体。
正如丹·席勒所言:“多种形式的持续连接的需要,标志着进入‘移动私人化的新阶段。”微信这种多面向、去中心的社交和信息平台必将带来一场新的商业革命。在不断编码、传播、解码、再传播的过程中,每一个用户都可以轻松体验社交主体、信息接受者和传播者的身份,同时也被运作为潜在消费者,为商业宣传铺排了新的关系网络,也为消费行为敞开了新的路径。
四、结语
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移动通信”是网络技术与移动终端革新相结合的衍生物,它“内爆式”的发展表征了新传播革命的结构性变迁及功能性转向。“即时+移动”的新特性全面改变了个人电脑时代的传播交往结构与方式、弥合了真实与虚拟的割裂关系与体制,使得现实生活与赛博空间的相互移位、相互渗透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并且常态化、秩序化,甚至演变成一种新的“惯习”。社交生活、信息资讯、商业交往通过移动终端与互联网的勾连变得唾手可得,这不仅仅是一种有趣的生活及交往体验,更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及社会模态。换句话说,“即时移动通信”正在逐渐消弭生活世界与赛博空间的疆界,并通过社会关系、传播交往形态的革新重建社会结构、生活秩序及价值体系。在熟人与生人,公共与私人,交往、信息与商业的深切勾连、快速融合与转化过程中,赛博成为有力的控制论有机体,在这个新型技术城邦中,不仅现实时空与虚拟时空的关系得到修正,自然与文化、人与机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也同样得到修正,它们不再相互挪用和侵占,而成为一个融合的共生体。
注释
①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现代传播》2012年第4期。②李良荣:《透视人类社会第四次传播革命》,《新闻记者》2012年第11期。③Glen Creeber and Royston Martin. Digital Culture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07.④国外的即时通信工具,目前暂时没有统一的中译名。Line可翻译为“线条”,WhatsApp可翻译为“什么是应用程序”,Kik可翻译为“可可”。⑤Mark Poster. Information Please: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Digital Ag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81.⑥⑨⑩刘丹凌:《第三媒介时代》,《现代传播》2010年第3期。⑦肖华:《腾讯微信用户量突破3亿耗时不到两年》,腾讯网,http://tech.qq.com/a/20130115/000179.htm,2013年1月15日。⑧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50—351页。[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53—253、261页。参见《解析微信营销的五种模式》,《互联网周刊》2012年第17期。胡素青:《二维码刷一刷微信带你去商家》,《金融科技时代》2012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沐紫中州学刊2014年第10期微信舆论场的生成、效能及引导2014年10月中 州 学 刊Oct.,2014
第10期(总第214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