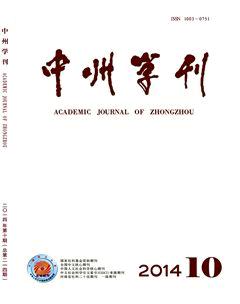北魏中原文化思维战略
摘要:自永嘉之乱后,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入主中原,与前赵、前秦、后秦、胡夏等相比,北魏的武力并非最强,但北魏自建国的道武帝拓跋珪起,就已经逐渐意识到要想永续地经营中原地区,就必须得到汉人的充分认同,从文化层面上得到汉人的接纳。北魏在从边缘到中央的空间转移中,同时完成了从部落到帝国的转型。与十六国逐鹿中原者相比,北魏竞胜者在于其拥有一套中原文化思维战略,即从“血缘关系的攀附”到“地理空间的占有”再到“历史文化的继承”,三大战略交叉递进,并形成了少数民族入主华夏的文化思维战略模式。
关键词:北魏;洛阳时期;中原文化思维
中图分类号:K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0-0122-04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造就了集中的政权、统一的制度、主流的文化,正式开启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族对于自我意象与异族意象之间的辩证与区分,自此,“族源历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①并形成了以中原汉族世袭旧王朝为正统、以胡族政权为僭伪的政治观念。②“戎狄不能为帝王”成为胡汉统治者的通识,后赵石勒为取信当时的晋幽州乌丸校尉王浚时便曾云:“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③此虽为石勒遮盖野心的托辞,但却说明了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在努力消除、弥合胡汉差异,以便名正言顺地入主华夏,成为政权的合法继承人。
历史上永嘉之乱后,许多少数民族涌入中原,但在小试牛刀后便销声匿迹,唯独北魏成为了第一个统治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它在从边缘到中央的转移中,完成了从部落到帝国的转型,④并统一了北方,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辉煌的国际都市洛阳,成为北方乃至中国的政治中心,并奠定了北齐北周以至隋唐的制度渊源。邢义田先生在《天下一家——传统中国天下观的形成》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很早就将中国看成一个文化体,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⑤的确如此。与十六国中几个较为强盛且具野心的国家,如前赵、前秦、后秦、胡夏等相比,北魏的武力并非最强,但北魏自建国的道武帝拓跋珪起,就已经逐渐意识到要想永续地经营中原地区,就必须得到汉人的充分认同,从文化层面上得到汉人的接纳。从道武帝拓跋珪到孝文帝元宏,北魏在与汉族交涉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思维战略,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从“血缘关系的攀附”到“地理空间的占有”再到“历史文化的继承”,三大战略交叉递进,它与南朝齐、梁正式进入政权正统与文化正统之争,北魏的富强与高度的文化自信促使了北方人逐渐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正统主义。
一、血缘关系的攀附
两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达到与华夏族“同祖同源”,进而赋予自己新的
华夏身份⑥的目的,一般都会对自己的民族血统进行委婉曲折的“失忆”和“记忆”,最终以炎黄子孙自居。《魏书·序纪》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⑦这段记载意在说明拓跋氏为黄帝后裔。但据考证,“拓跋”是秃发的音转,实为“鲜卑父匈奴母”之意⑧。历史上,拓跋鲜卑在迁徙到漠北后,与残留在草原上的匈奴人频繁接触,通婚融合,便形成了以“鲜卑父匈奴母”为内涵的“拓跋”族名。那么,一个原本“鲜卑父匈奴母”之后裔的民族何以会在《魏书》记载中成为黄帝后裔呢?
就目前所见史料看,最早将拓跋视为黄帝后裔是在桓帝拓跋猗陁前后。据《魏书·卫操传》记载,桓帝拓跋猗陁辅相卫操曾“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轩辕之苗裔。”⑨
公元4世纪初,西晋八王之乱事态扩大,颇有雄才大略的桓帝拓跋猗陁以卫操为相,将目光转向中原。当时主要存在着两大互相敌对的政治势力:一是以匈奴刘渊为首的反晋势力,一是以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为首的西晋地方官的反匈奴势力。304年,晋惠帝被成都王司马颖逼留于邺,匈奴刘渊反于左国城,十六国大乱爆发。刘渊出兵支持司马颖,司马腾向猗陁乞师救援。时卫操曾劝拓跋猗陁明确政治立场,匡救晋室。拓跋猗陁率军两次击退刘渊,司马腾上表奏闻,西晋加猗陁“大单于”号,金印紫绶,这是拓跋鲜卑受封晋朝的开始。穆帝猗卢在位时,又进行了两次援晋战争,受晋封为代公、代王。不难想象,在拓跋猗陁死后,卫操因援晋事而将拓跋氏列入西晋臣属,攀附汉族血亲,从此改写拓跋部“族源历史”,称拓跋为“轩辕之苗裔”。自立碑之后,这段历史成为拓跋部口耳相传的“代歌”中的一部分,被后人记载下来,这在《晋书》中《帝纪》《刘琨传》中亦可得到印证。此后,拓跋后人便模糊了之前的记忆,逐渐认为自己是黄帝后裔了。可见,桓帝援晋事正是拓跋部从“鲜卑父匈奴母”到“黄帝后裔”这一“族源历史”的转折点。
随着帝国的建立和疆域的扩大,北魏并不满足于自己仅仅是西晋臣属的角色。自338年一直到398年,北魏国号从“代”到“魏”的变化显示出了它与两晋政权的合分关系。338年,什翼犍立国,以“代”为国号,一则拓跋氏本居代北之地,另一方面是承穆帝猗卢受封代王而称。到398年(天兴元年),北魏政权已经从塞北扩张到中原,这时为了回应以正统政权相号召的东晋政权,拓跋政权才最终确定国号为“魏”,以承应曹魏,正式向东晋政权提出了挑战。⑩至此,北魏从“鲜卑父匈奴母”到“黄帝后裔”,再到“西晋臣属”,又至于跳脱西晋、直续曹魏,抗衡东晋,完成了其民族血统上汉族后裔的定位。
二、地理空间的占有
北魏的中原文化思维是伴随着地理空间的占有和扩张而产生的。纵观拓跋政权从边缘到中央的转移过程,“迁徙”“迁都”“兼并”“战争”是北魏中原文化思维背后的行动及武力支撑。
拓跋鲜卑原始居住地为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北段。东汉前期,当匈奴发生震动草原的南北分裂时,一部分鲜卑拓跋人在首领推寅(史称“第一推寅”)的带领下,由大兴安岭北段向西南方向移动,迁居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并在这里生活了大约100年左右,这是拓跋鲜卑的第一次迁徙。第一次大迁移拓跋鲜卑人从森林走向了草原。到了第七代献帝邻的时候,即东汉桓帝时,拓跋鲜卑举行了第二次迁徙,据载这次迁徙历经数年,方抵达匈奴故地,即阴山一带。阴山一带已经与中原汉族地区直接毗邻,拓跋人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拓跋力微在做首领的58年内,拓跋部迁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从此盛乐成为拓跋鲜卑的第一个都城。皇始、天兴年间,拓跋珪进兵中原,于天兴元年(398)七月又把都城迁往平城。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期间,北魏北讨柔然、西征夏国、攻灭北燕、消灭北凉。
北魏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便有了南侵的野心,频繁与南朝交锋。太武帝拓跋焘甚至声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而孝文帝也表明了自己吞并南疆的立场和决心:“密迩江扬,不当早晚,会是朕物。”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此时,北方的威胁已经解除,孝文帝的战略目标是南伐齐朝,统一中国;其次,统治区域的扩大,必须加强中原地区的控制;但最重要的是,平城保守实力强大,不利于汉化改革。诚如《魏书·任城王澄传》中孝文帝所言:“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难焉。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北魏迁都洛阳,深入到汉文化的核心地区,这在十六国中并非孤例。前赵、前秦、后秦均不约而同地立都在象征大汉文化正统的汉代首都长安,这不仅是一种归属感的表现,更大的意义是诉诸于地域本位,从地理空间的占有上达成对自我的界定,以拥有汉代首都为凭借,企图取得真正的华夏正统地位,为一统中国,经营宇内提供合理的依据。
三、历史文化的继承
北魏逐鹿中原的策略,无论是民族血缘关系的攀附,还是地理空间的占有,这些手段均非北魏所独创。至少前赵、前秦、后秦这些政权也都在这两方面有所努力。事实是,仅在血亲、空间等外在方面努力,仍难以转变汉人心中以东晋为正统的思维,甚至连一些少数民族也认定东晋才是正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始至终向东晋称臣的前燕鲜卑慕容氏。如前所述,北魏与十六国相比,最为突出的方面在于北魏帝王自拓跋珪至孝文帝均意识到,若想要永续地经营中原地区,就必须得到汉人的充分认同,从文化层面获得汉人的接纳。最早有这个意识的是拓跋珪。率领拓跋鲜卑进入中原的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因为幼年曾有流落内地七八年的经历,他本人具有相当程度的汉文化修养,这是他将鲜卑拓跋部领向中原并引用汉晋制度立国的思想基础。
汉文化对拓跋鲜卑统治者的震慑和改变在史书中有一段微妙的记载。据《魏书·贺狄干传》记载,鲜卑族人贺狄干奉拓跋珪之命出使长安,结好后秦,后两方交恶,滞留长安,“狄干在长安幽闭,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初,太祖普封功臣,狄干虽为姚兴所留,遥赐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及狄干至,太祖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这里所谓“羌俗”实即“汉俗”,贺狄干原本为“功臣”,却因举止风度有似“儒者”及语言衣服同于中原人而遭杀身之祸,并成为天兴二年汉化改革出现历史性倒退的引子。但贺狄干的例子也隐约折射出,以拓跋珪为首的统治者意识到了文化于族群的改变是成本最小同时又是效力最大的一种政治手段。此后,历任拓跋统治者均不同程度乃至不遗余力地推行汉化,从文化血统上模糊族群的客观特征,这个过程既打破了“戎狄不能为帝王”的观念,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定律,可谓抓到了文化战略的核心。兹举三件较为典型的事例说明北魏汉文化的融入和传承过程。
首先,定国号与国家行次。北魏定国号为“魏”,以区别于“代”,这是北魏立国的顶层设计。自晋室之后,各少数民族在北部中国建立自己的政权时,其所取名号,或据封国之称,或因所起之土,或附汉氏之亲。北魏从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四月改称魏王到天兴元年六月,拓跋政权的称号始终悬而未定。最终拓跋珪采用汉族士人崔宏之议,定国号为“魏”,意为北魏上承曹魏,行次从土德,意在承汉火德。定位明确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国家制度上的改革。通过建宗庙、定官制、改律令等,北魏逐渐具备了汉族王朝的特征。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北魏政权重定行次,进一步理顺了承续法统,明确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划清了与晋的依附关系,从此以后,便“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了。
其次,用行政手段改变民风民俗。定国号、定行次、改革制度等属于官方行为,对于彼时信息不畅通、传播不发达的情况,只是依靠这些手段力图推动拓跋平民汉化恐怕是不够的。那么,孝文帝的效率在于使用行政手段强力推行一般百姓的转变。其中包括迁都洛阳,彻底剥离拓跋鲜卑人原本的生存环境,还有一系列的强制措施。例如,禁说鲜卑语的规定,“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已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罢官,所宜深戒”。禁穿鲜卑服的规定,太和十八年,孝文帝令“革衣服之制”,并责令驻京官员督促京城百姓着装改旧从新。太和十八年至十九年间,改拓跋氏为元氏,同时改代人诸姓氏为汉姓,等等。孝文帝使用行政手段从语言、衣着、姓氏等百姓易感易见的事物改变起,迅速推动了民风民俗的转变,这种改革无疑最直接也最有效。
最后,用“拿来主义”移接汉族文化。例如,平城营造太庙、太极殿,孝文帝“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北魏太庙、太极殿完全是模仿魏晋形制而来;用“拿来主义”方式套用汉族文化尽管有时也会有偏差,如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进入北魏的褚緭参加北魏元会看到的大臣的服饰时曾作诗加以讥讽,“帽上著笼冠,裤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但这种模仿的方式毕竟是改革从形似到神似的捷径。
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不但居于中原的士族对北魏的发展引以为傲,“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南人亦钦重北人,陈庆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北魏统一北方之后,一再透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文化传承去标榜北朝的正统地位,使得南朝已经不能再置之不理,因为如果再不据理力争的话,很可能会丧失历史的解释权。因此,即便是刘宋经由原本具有正统地位的东晋禅位而来,其优势似乎已经未若前朝具有绝对性,是以必须积极地与北方胡人政权争夺正统,并极力否定北朝政权的正当性,除了斥北朝为“索虏”或“魏虏”(《南齐书》)之外,更史无前例地在史书中增设《祥符志》或《符瑞志》以渲染天命。这说明北魏从边缘到中央的正统化战略对南朝的威慑力是相当大的。
影响所及,其后的北方政权,诸如北齐、北周、乃至于隋,皆循此思维模式,理所当然地承接先朝周、汉帝统,这种政治现象亦足以说明自北魏洛阳时期以后,北方人逐渐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正统主义。正如高明士在《隋代中国的统一——兼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一文所指出的:“在北魏分东西以后,看似衰败,但因西魏、北周乃至隋朝,都努力从事文化建设,进而树立其向心力,这一方面,无疑的,长安的北朝政权是越做越出色。如西魏所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北周以《周礼》建国、隋朝的‘依汉魏之旧立国政策,均用以作为‘文化认同的号召,结果,关中政权成功了。”可见,北魏在与汉族交涉中所形成的“血缘关系的攀附”到“空间地理的占有”再到“历史文化的传承”策略,从此也成为了少数民族入主华夏的文化思维战略模式,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中,为隋唐的统一和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出版社,2001年,第289—319页。②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五章《秦汉正统论的发展及其与史学的关系》,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第149页。③杨家骆:《新校本晋书并附编六种之六》之《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前赵录二·刘渊》,鼎文书局,1995年,第7—8页。④杜士铎:《北魏史》上编《拓跋魏国家的创建和疆土的扩展》,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第36—150页。⑤邢义田:《天下一家——传统中国天下观的形成》,《秦汉史论稿》,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第26页。⑥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五章《秦汉正统论的发展及其与史学的关系》,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第165、149页。⑦魏收:《魏书》卷一《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⑧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31、247—248页。⑨《魏书》卷二三《卫操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99页。⑩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沈约:《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32页。《魏书》卷四七《卢昶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5页。《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澄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64页。邓乐群:《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何德章:《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六九《魏纪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2186页。《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咸阳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36页。《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179页。陈开颖:《北魏冠服制度的三次改革》,《兰台世界》2013年2月。《魏书》卷九一《术艺·蒋少游》,中华书局,1974年,第1971页。姚思廉:《梁书》卷二O《陈伯之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315页。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城东·景宁寺》,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8、119页。高士明:《隋代中国的统一——兼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5年,第117—118页。
责任编辑:王轲中州学刊2014年第10期试论宋代对不孝行为的惩处2014年10月中 州 学 刊Oct.,2014
第10期(总第214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