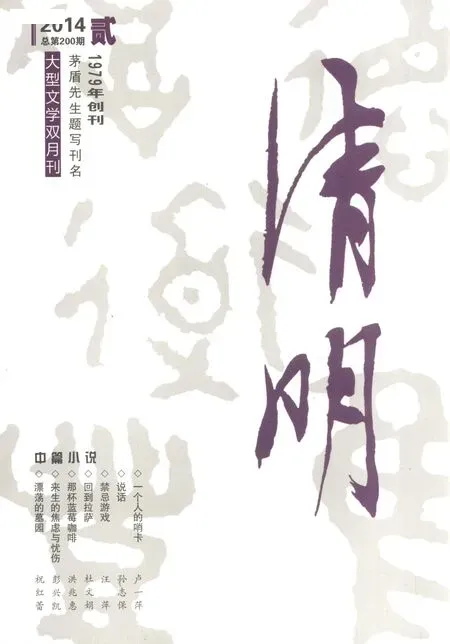羊
木莲
羊
木莲
雪中羊
一望无际的准噶尔盆地被茫茫白雪覆盖,与天浑然一体的雪闪动着银光。阳光下,一阵眩晕,我立刻闭上了双眼,再睁开时,眼前出现了飞舞闪耀的星辰,大脑一片空白。那是洁白带来的恐惧。我已经看了一个上午的雪了。这片雪原,天际是白色的,云朵是白色的,大地是白色的,空气是白色的,大块的白覆盖了双眼,覆盖了整个世界。
雪地里走来一群羊。羊从雪地深处走来,又向雪地深处移去。在空茫的雪野里,羊仿佛掉进了雪中,雪染白了羊,羊与雪融为一体。巨大的白,使目中一切成了目空一切,世界失色了,失真了,人进入了空虚。原来,美丽纯洁的雪具有如此强大的杀伤力,它用一个上午的时间,与羊联手作案,肆意地占有我的视野,瓦解着我的意志。终于,在最热烈的阳光中,我丧失了基本的分辨能力。以一种美好的事物去扼杀另一种美好的事物,人,常常会被无半点瑕疵的纯洁所击倒,就像这片雪原,纯洁变成了一笔沉重的负担。这世上越是美好的事物似乎越是沉重,沉重得容不下丝毫错误和疏忽,让人无以承受,陷入现实的苦难,抑或走进“虚”或更大的“无”的境地。
我再次闭上双眼,大脑中回放着移动的羊群,我以对雪的怀疑挑剔着每一只羊的行踪。一群羊,本该是一场壮观的移动。他们一度出现在广阔的草原中、荒疏的野地里、披绿的山坡上、蜿蜒的河道旁,他们绝少散步在雪地里,更不会像此刻的羊,既无秩序又散乱,走得松松垮垮,势单力薄。以白色的外衣去配合白色的雪地,在雪地里星星点点,起伏荡漾,似乎存在,又似乎消失,他们与雪保持着同一性,是雪的同谋,一起制造了世间的混乱。
雪下得强大无比,包罗万象,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沉浸在雪的怀抱里。在雪中,每一只羊只是一声叹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符号,可以存在,也可以消失,可以有价值,也可以无意义。他们飘摇无力,纤弱无助。从车窗望出去,羊群毫无章法,但他们依旧是一个集体。牧羊人是他们的首领,他们绝不轻易出局,始终在牧羊人能够掌控的范围内。
牧羊人穿着深灰色大衣,与雪形成鲜明对比。他慢慢地移动,不时停下来,掉转头向遗落在远处的羊看一眼。他的出现改善了我的视觉压力,为我紧绷的神经放置了一道舒缓的悬梯。我从悬梯上一步步走下来,双脚重新获得了土地。在重新找回的理性中羊不再虚幻,变得具体清晰起来。
羊是畜类中的特殊群体,虽然顶着一支形似男性的武器,却有着十足的女性思维,线性,胆小,跟随,对人莫名地信赖,没有善恶标准,一味地按照别人的意志和指点行事。一群羊中,头羊做什么,群羊跟着做什么,哪怕刀山火海,头羊跳了进去,其他的也会跟着跳进去。这是羊的执行力,也是羊的道德准则,更是羊缺乏个性、善跟风、认死理、小心眼、缺乏独立意识的案例。但是,这只是羊的一个侧面。羊也会执着,执着是羊的另一种性格。
仔细端详一只个体的羊,身着洁白的卷毛大衣,与雪混为一体,模特样的小型头颅,细窄的小腿下是三寸高跟金莲,特殊的还配以丰满的乳房。这类装扮,怪异且夸张,显出时尚的女性特征。羊是阴性的,柔性的,他们的牙齿不锋利,整齐地排列着,没有尖锐的锯齿,只能咀嚼,不能撕咬,这使得羊们没有爆发力,更缺乏力量。他们奔跑,却因为满身卷曲的皮毛,看不出漂亮的肌肉,跑不出健美的曲线。他们跟爱美的女人一样,遵循素食主义,素食使得他们性情温和,体格纤弱,连叫声都是糯糯的吴侬软语。可羊又似乎没有女人幸运。女人可以变换衣着,可以长袖短袄,绸衫缎裤,皮草棉麻,可以佩金戴银,珍珠钻石,可以熠熠发光,引人注目,羊却不能,羊只有一套装束,白色的卷毛大衣、细窄的高跟鞋,配以头顶竖立的长角,像防身武器,却不能吓住任何一个对他有所企图的人。
羊大为美。汉字的美,自羊而来,羊便是美,美便是羊。羊的美与女人的美是一致的,在于善良,还在于温顺。某些时候,温顺能够缓和矛盾,制造和谐,感染大众。温顺属于善的范畴。羊善,甚至是无原则的善,善得使人心痛,因为他们在命运面前几乎不做任何反抗。
但是,在一片草原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只狐狸追逐一群羊,羊们撒腿跑开。一只跑掉的母羊看到狐狸盯上自己的孩子,掉转头来试着去顶撞狐狸。她低着头不顾一切地冲向狐狸,发疯似的横冲直撞。狐狸不怕羊,但怕不要命的羊。几次冲击后狐狸败下阵来,站在草原的风中,思前想后不得结论,最后,拖着尾巴离开了羊群。母羊被激起的仇恨迟迟不肯散去,斜视着败走麦城的狐狸。羊做了顶天立地的事,却无法顶天立地,她立不住,妩媚地蹬着高跟鞋,侧身在风里,草原是她的T型台,她是走秀人间的芸芸过客。
母羊的爱人是公羊,公羊有着与母羊相似的装束,同时配以尖锐的羊角。这种矛盾的相貌必定是受了造物的戏弄,造物让一只羊成为雄性,予以锐利武器,又为他配以尖足小脚,这类变态的造就,严重损伤了公羊的自尊,使他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的处境。见到狐狸后他立起尖脚拼命地躲避,躲避是公羊保护尊严的一种方式。
母羊有母性,既本能又伟大,在孩子受到危险时,有以命抵换的精神。相比之下公羊似乎不太有血性,看着自己的孩子被追咬,静观决战中的母羊,像看一场事不关己的杂耍。然后掉转头,没事人似的走了。
这只公羊运气并不好,没走出多远,自己也面临了威胁。一只比狐狸更强势的虎看中了他。虎站在高高的山冈上,早就看到了刚才的一幕。虎也是有敬畏感的,他不怕一只羊,但他懂得敬重一位母亲,鄙视一个父亲。看到没有责任感的公羊离开与狐狸格斗的现场后,虎尾随他走向草地深处。虎不急不躁,胜券在握。感觉到被跟踪,公羊的腿软了,他心里明白,他连狐狸的对手都做不了,拿什么来抵御猛虎呢?不用过招,他只想撒腿跑,奔跑是他唯一的出路。但是,他的腿好像灌了重铅,还未起步,就被虎扑倒了。他蹬蹬四条腿,没有丝毫抵抗的动作,便断了气。
从车窗望去,散乱的羊群渐行渐远,与其说是一个个移动的白点消失在白色雪原中,不如说是融化在雪野里。雪原空旷,无人无物。无,在这里表现为寂静,准噶尔式的寂静,比起它的白要生动得多,也使人在几近绝望的迷失中突然眼前一亮。雪地里,深陷的脚步发出吱吱声,寂静就是从雪的吱吱声中发出的。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静原本也是可以用声音表现的,真正的静不是无声,而是空旷中呈现出的缓慢的脚步、轻柔的手势、均匀的呼吸,是空气中随意游走的风,是心灵慢慢地散步。静是需要聆听的,听不到的声音不叫静,听不到而使劲听,不但不是静,反而是骚动,是好奇和不安分。
我想,当这个世界从纷争混乱中停住脚步,当万事东流,一切回到起点时,回忆被悄然唤醒,唤醒的旧事中必定有一种柔软感染着人们的心智。羊安静地跪伏在雪地上,用他善念的双眼打量着从前。面对一只羊,人会恍然梦醒,羊性格中的失败在历经了众多纷争后,却赢得了命运里的胜利。这人间的事孰是孰非,这世上的人何德何能,审视一只羊的性格和命运,也是我们对自身价值的一次重新思考和整理。
宰羊
羊不能说杀,要说宰。猪才说杀。屠夫常会杀猪不死,刀在脖子上来回抹,不利索。猪又不老实,死不了嗷嗷叫,满院子乱跑,淋下一地血。不像羊,羊被宰了,没死,但羊不叫,默默地躺在地上,眨眼,静听,等待最后时刻的降临。羊死得安详,仿佛生来就是为赶赴祭坛的,这一刻合情合理,理所当然成了羊的归宿。
羊死了,但不瞑目,睁着眼睛,温柔地看着你。
屠宰是在葡萄园进行的。
那是一个仲夏日。一群朋友相约在葡萄园消夏,有人在园子里散步,有人在葡萄架下纳凉,有人在蒙古包里玩牌算命。孩子们走到园子深处的野草中,站在吃草的黄牛旁谈话。年幼的女孩问年长的女孩,吃草的牛是女牛还是男牛?路过的大人替年长的女孩回答,跟你们的妈妈一样。孩子的妈妈们正坐在蒙古包的地毯上说家常。
没人相信葡萄园里也会有阴谋,光天化日之下的阴谋。一些人来到一块草坪,指指点点,品头论足。一群羊中,最活蹦乱跳的那只被选中了。上帝选人去死,爱选那些年老的、上了岁数的、生命力正在衰退的。人选羊不这样,人要选健康的、活泼的、充满朝气的。上帝选人不为自己,选中了交给地狱就完事了。人选羊却是嘴馋,老的不能选,肉质粗糙,嚼若干柴;病的不能选,病从口入,会引发疾病。有人更过分,大喊,挑没有结过婚的。没结过婚的羊叫羊娃子,羊娃子就是羊羔,人要吃弱小的、稚嫩的、正在旺盛生长的。人的规则与上帝的规则存在天壤之别。
那只选中的羊被拉着一只角往屠场去。羊好像预感到了不祥,四条腿撑在地上不肯前行。羊角被猛烈地拉扯,羊拼命地低头,下颌快要抵到胸前,拉羊人费尽了力气,嘴里咒骂着,骂羊不听话,死到临头还这么倔强。另一只羊尾随而来,看不出是悲伤还是愤怒,仿佛在为同伴送行。宰羊人说,他们一起来的有四只,两只已经先行一步走了。我推测那一起来的该是一母四胞,那样才对生死有感应,才会前来送行。送行的羊已经有了两次别离的经验,这经验于他是刻骨的。他或许内心动荡不已,但却不溢于言表,平静地跟在第三只即将赴死的羊后面,为他送上顺应天命的安慰。
送行的羊转头凝望一群人,又回首望向其他羊,依旧没什么悲哀,没什么愤懑,像死滩中的水。人不知道羊的想法,更不明白自己的做法会使羊生出什么样的想法。人的想法混乱不定。这使人忽然发现,正在绝望的不是羊,而是人自己。
屠场地上的青草早已被践踏,纷乱地伏贴在地面,草被血液粘连在一起,变黑、变硬、变得纷乱肮脏,有淡淡的杀气泛起。血迹是早先而去的羊的同伴们留下的,宰羊人说后面那一群的结果也将是这样。
羊终于被拉到了屠场。人轻轻一推,羊就倒了。羊闻到了血腥味,立刻意识到了什么似的“咩咩”叫了几声,像是问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将要发生什么。人不语,埋头准备自己的事情。羊知道了,沉默了,认了,没有站起来,而是继续躺在地上,眨着漂亮的双眼皮看着人去准备刀子、绳子、接血的脸盆。
羊看上去比人淡定,做好了充分准备,剩下的就是等待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人,眼神温和极了,脸上看不出生的快乐和死的恐惧。宰羊人拿了一把刀来,又去取第二把,拿了脸盆来,又忘了绳子。宰羊人有点紧张,有点慌乱,在羊面前不够从容。
宰羊人来齐了,一共三个。三个人把羊的三条腿绑起来,留出一条。据说,羊在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时候,魔鬼会来捣乱,人就只绑羊的三条腿,留下一条腿来踢魔鬼。羊善良而不分是非,被人宰,还要替人去踢魔鬼。
刀放到脖子上,羊歪着头,不叫,只是有节律地、不停地替人踢着魔鬼,直到踢不动为止。宰羊人不够自信,致命的一刀迟迟无法捅进去,抑或,在众人面前他有所顾虑,上帝的眼睛正越过云层看着人间血泊,而围观者中或许正潜伏着一个密探,等待着匕首刺出的那一刻。宰羊人的心乱了。他已经宰了半辈子的羊,不像是个新手。推倒羊的动作、摁住羊的姿势、捆绑羊腿的方法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他是一个有经验有能力有业绩的屠夫,是一个职业杀手。但是,此刻,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他好像过不去内心的关口了。
宰羊人住了手,长出一口浊气,沮丧地扔掉手中的刀,转身回了毡房。围观的人感到了疲倦,他们对那一刻向往已久,他们的身体里早已注满血气,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他们渴望感受血腥事件,在利器刺向脖颈,热血汩汩流出,腥气腾空升起,以及疼痛抽搐的过程中获得释放。此刻,他们失望地看着宰羊人转身离去的背影,鼓涨的激情顿时泄了气。他们精神上没了刺激,身体里没了力气,感到了匮乏。
围观的人抛下绞杀场的羊,走了。羊独自躺在草地上,无人问津。我过去,蹲在羊的身边,从地上拔起一撮草,送到羊嘴边,我想对即将死去的羊表示一份慈悲。羊领情了,深情地嗅嗅青草,又深沉地呼吸了几下,然后将眼光伸向远方,看看装腔作势的人们,最后抽缩回来看看眼前虚情假意的我,轻轻闭上了双眼。
差不多二十分钟后,宰羊人从毡房出来,重新洗干净手,从地上捡起刀。刀子忽地进了羊脖,鲜血顺着脖颈喷涌出来,一股股流向草地,流进脸盆。羊大口地喘气,依旧不见痛苦的表情,他的平静使我心生惧怕。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灵,平静到能面对死亡?他的本能在哪里,上帝为他施过什么样的魔法,连本能都不动声色?
羊大口地喘着粗气,渐渐地,他的双眼失去了灵光,越来越涣散,越来越捉不住事物。
终于,羊的整个身体瘫软下去。宰羊人说,死了。大家对视一下,无语,转身回房了。
剥皮,开膛,分解。
火架起来了,锅里沸水翻腾。两个小时后,人群集中到餐桌前:真鲜,真嫩。天黑的时候,羊的尸体全部转移到了人的身体里。
如果羊有墓志铭,应该这样写:
羊,男性,毛色黄褐,略卷,大尾,性情温良,与世无争,2004年6月25日逝于葡萄园,终年不足一岁。
黄羊
越野车奔驰在广阔雪原,前方是被大雪覆盖的土丘高台,周围生长着梭梭柴、骆驼刺。汽车发出机械的噪音,虽不大,却搅乱了安静的雪原。远处,出现了一只奔跑的动物。车上有人喊:野驴。大家伸出头,追看消失在雪野土丘后的野驴。不一会儿,又一只动物奔跑而过,有人解释:不是野驴,是羚羊。当第三只动物从眼前快速闪过时,全车人都看清了,不是野驴,也不是羚羊,是黄羊。
显然,黄羊被打扰了。他们快速逃窜,看上去急切,不知所措。黄羊有着优雅的身材,即使是惊慌失措,奔跑起来时也从容美丽。他们向前冲,胸膛直挺,耳朵竖立,四条腿有规律地前后换动。
唯独一只小黄羊,没有跟随父辈们离去。准确地说,他是跟着他们转身了,跑了几步之后,又停了下来,掉过头,看车,以及车上的人。这辆车应该是他见过的第一辆车,一个白色的庞然大物。他纳闷,不解,紧盯着白色机器。在一扇扇透明的玻璃窗上,他看到了人的脸庞。他的脑袋在高速运转,想知道这是什么?为什么?怎么了?他与人对视,抱以好奇,又流露出十分的信赖。无知无畏的小黄羊站在雪野里,显出了世界的纯洁和无瑕。
车缓缓经过小黄羊,又缓缓地离去。小黄羊不知道,他能够站立在雪野中,便是以极大的勇气告诉我们,人类依然可以被信任,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这是一个不被信任的世界,人被怀疑,被质问,被批判。
小黄羊凭什么要信任人类?因为幼小,不懂事理,尚未接受来自父辈的教诲,未曾见识过泣血的场面。他那么小,那么稚嫩,站在荒原上,却像一座警示的丰碑,以单纯和静美唤醒了罪孽深重的人们。
在所有沙漠动物中,黄羊是很独特的一种,他们有美丽的眼睛、漂亮的身段和飞烟样的身影。在荒漠中,他们不似骆驼的拖拉、家羊的慵懒,以及爬行动物的城府,他们是荒漠中最积极的因素,在僵死的大漠中风行穿梭,带动着生机和活力。我与黄羊的每一次遇见都匆忙,急速,我看不清他们的真容,留在眼前的仅仅是一个局部,一个倩影,一次华美的转身。
我对黄羊的概括空洞乏力,没有任何细节可以复述,这就是瞬间吧,瞬间造成的效果,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只有嗖的一瞬间,一只黄羊的片段被快速剪切,未及定格,便没了踪影。对于一种以奔跑见长的动物,要想描述出来,至少该有三个内容:步态、神情、肌肉的走向。但是,对于黄羊,这些内容全被瞬间打包成一体,成了一闪而过。
冬天,塔里木夜色笼罩着青灰的大地,公路旁一只黄羊掀动草丛,微微凸起的臀部,蹬直的后腿,拉出了漂亮的肌肉。借着月光,黄羊为我的眼睛截留了下半身,我真切地看到了一只黄羊的一部分,虽是局部,却有使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惊艳。黄羊的臀部展现出纯野生的质感,光亮的皮毛、精瘦的肌肉和强健的骨骼如此完美地构架出一只野生动物。他的后腿坚定地立在草丛旁,像钉子扎进水泥,没有丝毫软弱和犹豫。
对照人的迟缓和迟钝,黄羊高超的掩身技巧一次又一次诠释出时光的魔法,一念之间,转眼之间,刹那之间,尚未开始已经结束。佛语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弹指一挥间,趋于平静,而那一瞬间的定格,却是长久地萦绕着我。在我脑海中,黄羊是一阵风,携带着秋天的色彩;是一段影像,快速切换层叠的缤纷;是一沓魔法师手中的纸牌,三下五除二,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出神入化。
责任编辑 刘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