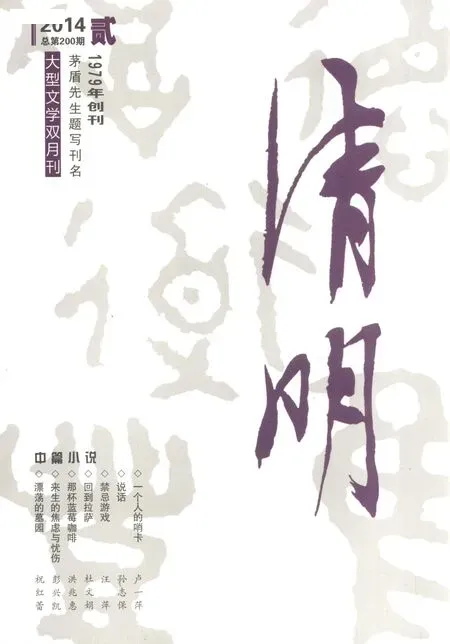多公小记
王达敏
多公小记
王达敏
多公,学名王多治,笔名治芳。多公获此尊称,源于何人何时,无人考证,亦无从考证。
这是一个生性达于极致之人。在我的同事中,其个性色彩之显、轶闻趣事之多者,多公遥遥领先,无人出其右。身材偏矮,行走作冲锋状,一头爱因斯坦式的自然卷发是其独有之标志,学生私底下称其为“金毛狮王”。说话口无遮拦,放言无忌,常常让人瞠目尴尬,怒亦不是,恨亦不成,都知道他心直口快,没有坏心,也不去计较。他的长处是知错就改,说了过头话,不该说的话,事后回想不对,便急忙检讨“我说的不对,别在意啊!”性急,心里憋不住话,好与人说,每每得知不能与他人言说之事,他总是第一时间告诉朋友,先对张三说,并一再告诫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转身又对李四说,同样告诫他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别人都遵守着他的告诫,唯独他自己不遵守。往往是不出一天,他知道的事,朋友们都知道了。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毕业,由国家分配工作,系里成立分配领导小组,领导找他参加,他问领导要不要保密,领导说要保密,他说我不能参加,因为我不能保密。他率性自由散漫,一向淡薄名利,他有一句名言广为流传:“除职称外,凡是需要申请才能得到的东西,我一概不要。”就连有时送上门的好事,他也婉言谢绝。平生最崇拜鲁迅,愤世嫉俗,眼中揉不进沙子,年轻时如此,过了古稀之年仍“江山依旧,本性难移”。常示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此论世断人,感慨系之而终归于慰己慰人。
他有三大嗜好,抽烟、嗜辣、玩牌。据说他曾经嗜烟如命,整天烟不离手,一支接一支,常常是一支还没有抽完,又点上一支。后来年岁大了猛然戒烟,乱了生理,心脏出了问题。好事变成坏事,变不过来,但烟也不敢再抽了。又嗜辣,几乎是无辣不食。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能吃辣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人是德国波恩大学汉学家顾彬教授。一次到火锅店,他嫌辣味不够,索性直接喝火锅里的浓汤。他饭食简单,一碗米饭,一份辣椒,再来一份米粉肉或者红烧肉,就是最好的美食。我了解他,每次吃饭都给他点这两道菜。心脏搭了支架后,我对他就有所控制了。他从不沾酒,原因是不能喝酒。在酒界,不能喝酒的男人不能算男人,充其量只能算半个男人,朋友们以此戏言他,他亦以此自嘲,自称是“半个男人”,因此也拦住了别人的劝酒。久而久之,他就成了人人皆知的“不喝酒的男人”。他吃相生猛粗野,大口扒饭,裹食极快,近乎吞咽,大有梁山好汉大口吃肉的痛快淋漓。他不喝酒,可以先吃饭,经常是菜未上齐,酒未三巡,他已饭毕。他不擅长娱乐,读书教学之余的唯一爱好是玩牌(打麻将)。教授玩牌,好说不好听,多少有点不雅或不务正业的味道,他深知世俗的偏见,不理睬,任人说道。心底里,有时难免有些在意,但架不住他好这一手,于是,我们就时常听到他不无羡慕地转述梁启超的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当然还有梁公的高论:“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而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据说梁启超任报社主笔时,很多社论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的。多公述此,意在说明,玩牌大有健脑益智之功效,国学大师作如是说,我辈岂敢误解。每当此时,大家会心一笑,彼此意领。
中文系历来是卧虎藏龙之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安徽大学中文系确实有几位名声远播的教授,多公是其中的明星角色之一。我和他同在一个学科、两个教研室,1997年合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合并之后的学科发展达到最盛状态,其标志是,学科7位教师全是教授,这在全国也不多见。恰好教研室有4位功夫优异、特色彰显的教授,学生美誉为“四大天王”。先在中文系传开,及至校内又校外。“四大天王”中,多公年长居首位,我年少居四。现如今,“四大天王”已经退休三位,巧合的是,学科经过新陈代谢,又有两位王姓、两位汪姓教师,“汪”字提高一个声调读“王”。我之外,他们三位都是饱学之士、博士加身,昨日的辉煌还能再现吗?
作为大学教师,多公的强项无疑是教学。多公知识广博,记忆力特强,上课基本凭记忆,没有正规的讲稿。他采用旧式教学,一支粉笔,一杯浓茶,开讲设问,渐入胜境。因极其投入,故充满激情,魅力四射,兴奋之时,往往庄谐并作,妙语连珠,听者入迷,堂上堂下其乐融融。他是真正的教学名师,其精彩有口皆碑,一经演绎流传,几乎成为神话。好多学生毕业多年,每每谈起多公,均以聆听过他的课而自豪,而后来的学子为再也听不到如此名流教授的讲课而遗憾。
作为学者,多公的入手功夫是诗,先是诗歌创作,后是诗歌研究。多公年轻时写过好多感情充沛的诗歌,因喜欢诗,从中获得了对诗歌的一份特别的灵悟。后来他走上治学之路,虽不再写诗,但诗歌修养了他诗人的气质和才情。诗是精灵,它能够放飞人的情感和思想,但治学则需要脚踏实地,为多公治学立根基的功夫,是以博学致广大,阅读成为他的终生事业。他的阅读范围主要在文学和历史,再广涉能够引起学人兴趣的多学科著述,还有刊载时事新闻的闲书报刊。他有天纵之才,上天给了他过目成诵、记忆超强的特异功能,直到今天,他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名篇佳作。他曾经很自负地说,我能讲中文系很多课程。此话不假,就我所知,他至少能够讲授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大学语文等课程。
阅读兴趣广泛,知识可以通广博,对于教学是一大优势。而对于专家学者治学,却不一定是好事。多公诗人气质,任性而为,又率性自由,超脱名利,再加之“生性疏懒”和贪玩,故阅而少作、述而不作,致使知识“广博”而专业不能“精深”。我们常为他遗憾,可又有谁知道,这种性格使然的做法难道不是他的追求吗?
多公是个有趣之人,我知道大家想听听他的轶闻趣事,下面录三则故事。
第一个故事:多公上课有个传统,就是讲到朱湘的《采莲曲》时,一定要请班上最符合这首诗歌气质的美女来朗读,学生们都将这视为班级荣誉的头等大事。那时中文和新闻还没分家,很多课程是一样的,两个班暗地里竞争激烈。有一年,新闻班先上中国现代文学课,班上美女多,全班学生都盼着多治老师能点到其中的一位女生,可他扫了全班一遍后说:“算了,还是我自己来读吧。”男生哄堂大笑,女生尴尬无语。
第二个故事:多公上课喜欢提问,学生高度紧张。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学生多半回答不出来,而这时,他总要大发恨铁不成钢、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并含有几分嘲讽的意味。一次给研究生上课,他一连问了几个问题,学生都没有回答出来,他气愤地说:“一个个戴着眼镜,人模狗样的,连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知道,不配读研究生。”现在的学生抗打击能力强,你骂你的,气生在你身上。还有一次给在职研究生上课,学生多是高中语文教师,当他问他们问题时,一个学生壮着胆子问他,“老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给我们说说。”他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下课后师生互相敬烟,一派和气。
第三个故事:多公上课没有时间观念,无论是几节课,一口气讲下来,中间不休息,且每次都拖堂。一次给97级上课,上午三四节,那时是冬季,学校食堂一过12点就没热饭热菜,所以一般都提前十分钟下课。饭点到了,多治老师还在讲,团支部书记忍不住站起来说,老师您拖堂了。他看了一下表说:“我的表还没到时间呢,还有三分钟!”又继续讲,三分钟后,团支部书记腾地站起来说:“老师,三分钟到了!”多公砰地把书一摔直接冲下讲台,上前动手掐团支部书记的脖子,两人扭打在一起,男生们急忙上去拉开。辅导员知道此事后,很生气,叫团支部书记写检讨赔礼道歉。团支部书记写了很长的检讨,下次课一开始,他站起来就读检讨书,说: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安徽大学、对不起王老师,等等,总之拔得很高,还没有读完,多公就笑着走下讲台给学生一个拥抱,说:“不打不相识,打完我才知道,原来拖堂你们就没法吃饭了,所以是我不对,不用道歉,再说是我打赢了”。
这就是有趣又有味的多公!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一篇题为《即将消失的风景》文章中,感叹老一辈学人逸事多,“有韵”且“有味”,后来的学者因长期压抑,有趣味的人不太多,有故事的人更少。刚进北大时,在未名湖边流连,学长指着老教授的身影告知,此乃北大校园最为“亮丽”的风景。如今,秋风凋碧树,风景日渐黯淡。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还会有博学之士不断地进入大学,但年轻一辈的学者,虽然也有在专业领域卓有成就的,可就是不如老先生“味道醇厚”。一刀切的退休制度,使后来的学生再也享受不到七老八十的老先生纯美的味道了。
一年一度的春节将至,我以这篇小文敬献多公,以了却我十年的一桩心愿,为他作一素描。
责任编辑 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