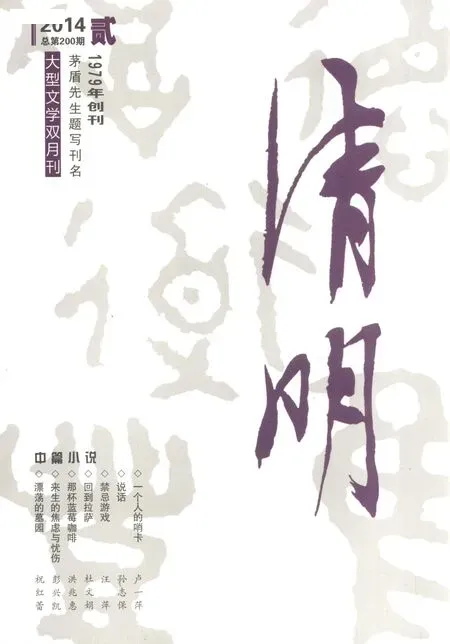一些念想,关于河流
乔叶
一些念想,关于河流
乔叶
问河之源
那条河,已经看不见了。河的名字,叫济水。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第642页关于“济”的第一个词条就是济水,如此解释:“济水,古水名,发源于今河南,流经山东入渤海。现在黄河下游的河道就是原来济水的河道。今河南济源,山东济南、济宁、济阳,都从济水得名。”
现在,此刻,我就在济源。在济渎庙里。
渎,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第336页如此解释:沟渠,水道。网上又搜索了一下,说是古人把有独立源头,并能入海的河流称为“渎”。《尔雅》中提到的四渎:江、河、淮、济,就是古代四条独流入海的河流,“济”指的就是济水。那时的皇帝常按惯例祭祀名山大川,名山即五岳,大川即四渎。在唐代,大淮为东渎,长江为南渎,黄河为西渎,大济为北渎——淮河,长江,黄河,渎的这种气势才更符合我的想象啊。
这是第三次来济源。1997年之前,济源属于焦作辖区。第一次去济源的时候,是在1993年,那次去的是邵原镇的原始森林,晚上露宿在山中,那是我第一次露宿山中,只觉得青山碧通,红叶醉透,树木葱茏,野趣丛生。第二次去济源,是2001年,我刚调到省文学院,那年文学院的工作会议是在济源开的,时间很短,又是去开会,来去匆匆,便没有什么印象。这次,是以客人的身份正儿八经地来欣赏济源的风景名胜。就从济渎庙开始。虽是客人,但和其他同行的朋友相比,我跟济源到底十几年前是一家,也因了第一次那些美好细节的积攒,我心里便多了几分同地之谊的温暖。
济渎庙,全称济渎北海庙,位于济源市西北两公里济水东源处庙街村,公元582年也就是隋开皇二年开始建庙,之后一千多年来一直被不断扩建修葺,直到现在。以典型的正史腔来总结的话,一言以蔽之:“济渎庙是古四渎唯一一处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现存最大的一处古建筑群落,被誉为中原古代建筑的‘博物馆’……一部济渎庙兴衰史,也是中国古代水神崇拜史的缩影。”
历史风云安安静静地睡在纸上,我眼前只是这一座宏阔庙宇。在济渎庙里一路走来,红墙碧瓦,亭台楼榭,雕梁画栋,琉璃脊兽,碑碣林立,曲径通幽,端的是朱门重重,庭院深深,更有那绿水脉脉,静聚成池。既是因水而建的庙,自然离不了水。连每一道门的名字也都和水有关:清源门、渊德门、临渊门、灵渊阁……在灵渊阁,我看到那一泓清池底冒着泉水的气泡,问讲解员:“这就是济水的源头么?”
讲解员说,济水的源头是在王屋山上的太乙池。源水以地下河的方式向东潜流七十余里,到济渎和龙潭地面涌出,形成珠河和龙河两条河流向东流去,很快便交汇成一条河,叫水,水河又流到温县西北才开始叫济水。济水成为济水之后,第二次潜流地下,穿越黄河而不浑,在荥阳再次神奇浮出地面……三隐三现,百折入海。真是一条神奇的河。
“那么,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去看看济水了?”
讲解员有些尴尬地笑着,说济水这条河,已经没有了。早就没有了。她在东汉王莽时出现旱塞,唐高宗时又通而复枯。黄河又多次改道南侵,逐渐冲入济水河床而入海。如今的济宁市就是原来济水中间北上的地方,黄河下游地段以及大清河、小清河,就是原济水故道。
故道而已。
那么,还祭祀她干什么呢?
讲解员说,这个问题,唐朝时期就有人问过,发问的人是唐太宗。济水通而复枯后,唐太宗问大臣许敬宗说:“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水甚细而尊四渎,何也?”——天下那么多宽阔雄浑的河流都没有被供作祭祀,济水干涸,几近消失,为什么还能位列四渎?许敬宗答曰:“渎之为言独也,不因余水独能赴海也,济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
许敬宗,死后被人如此总结:“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唯闻于黩货。”释曰:敬宗是以他的才能得到官位的,而且历居清贵枢要之职,但是他竟把自己的长子丢弃在荒凉的边疆,把自己的女儿嫁到蛮人的部落,他们本该学习些诗文和礼节,可是他却没有尽到父教的责任。对于女儿的婚姻大事,只是听人家用多少钱财来交换……再加上他扶持武则天当皇后,可谓是一个经典的小人。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翻开唐史,我居然屡屡被他惊住:唐太宗率军征辽东时,城中矢石如雨,有一勇士率先冲锋,主帅李勣指着他对许敬宗说:“这人何等勇敢。”按常理许敬宗只需随声附和,但他却说:“头脑简单的人才这样不知死。”说这种不合时宜的扫兴话,自然不得上峰赏识。后来更因在长孙皇后的丧礼上看到欧阳询穿丧服的难看样子想到了“沐猴而冠”这个成语而放声大笑,结果被贬官洪州。李世民曾问过许敬宗:“我看你这人也不错,但为什么人家都说你不好?”许敬宗对曰:“春雨如膏,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光辉,天地之大尤憾而况臣乎?臣无肥羊美酒以调和众口是非,且是非不可听,听之不可说。君听臣受戮,父听子遭诛,夫妇听之离,朋友听之绝,亲戚听之疏,乡邻听之别。人生七尺躯,谨防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谁人面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
虽然屡屡被他惊住,但对他我一向是无好感也无恶感——历史是笔细账,我努力不按照正史给我划定的大规则去粗算。如果没有能力细算,那我就不算。但是,他对于济水列渎之问居然有这样的应答,真是让我喜欢了。我愿意相信,很大程度上,正因了他的妙解,济水便被称为君子之水。济渎的存在,也便成为了君子精神的象征。“状虽微细,独而尊也。”——因独立而尊贵,而尊重,而尊严。
灵渊阁是济渎庙的最后一景。怀想着许敬宗的话,我跟着众人正要离开,讲解员忽然说左侧还有一个小门,从那边走出去就是一眼很大的泉水,叫珍珠泉,这珍珠泉曾经和太乙池一样,是济水的一个重要源头。
“现在还是活泉,各位要不要去看看?”
那就去看看。
好热闹的泉啊。来到泉水边,我的眼睛简直就不够用:洗衣服的、游泳的、洗脚的,还有围在泉水边看的……泉水被一个大水泥塔压住,压成了很多不规则的水龙头,每个水龙头都在向外喷水,洗衣服的妇人们说笑着,游泳的男孩子们扶着一块塑料泡沫在畅快游戏,还有小小的男孩子全裸着,女孩子们则要文雅得多,她们说说笑笑地在泉水里低撩着裙子洗脚乘凉……
可是,现在的济水既然已经不见了,那这珍珠泉又流向了哪里呢?
讲解员说,珍珠泉的泉水流出去之后,形成了一条自然河,灌溉了很多农田,在灌溉的过程中,越流越细,越流越细……说到最后,讲解员笑了笑,做了一个“你懂得”的表情,沉默。
然后,就消失了。我知道。
同行的人都走了,我还留在泉边,一个老太太驾到,我便和她聊起天。她指着泉水里的一个光腚小男孩,说是她的孙子。她在看护孙子。我问她这泉水有多少年了?她说不知道,她小时候就有了:“可多可多年了。”
“没有被哪个矿泉水厂收了去?”
“说过这事,老百姓都不答应。”她笃定地说,“俺们还都要来这里洗衣裳呢。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这里洗衣裳。还来这里接泉水喝。这水,舀起来就能喝,甜甜的。”
聊了一会儿,兴致上来,老人家居然还当起了讲解员,给我讲起了讲解员刚刚给我们讲过的发生在珍珠泉下的故事:一个老农月下观泉,左观右观,上观下观,觉得泉水实在是好,就吟诗道:泉泉泉泉泉泉泉。然后就无语了。正在郁闷呢,忽然听到有人接句:冒出珍珠颗颗圆。老农大喜,觉得这句子好得不能再好,于是问道:可是诗仙李太白?对方答道:然然然然然然然。
我笑。讲解员讲的时候,我没有这么笑。我必须得说,这个老人家比讲解员讲得有意思,有趣致。她讲得好——讲解员说“观泉”,她说“看泉”,讲解员说“好”,她说“不赖”,讲解员说“吟诗”,她说“唱歌”,讲解员说“无语”,她说“没话”,讲解员说“郁闷”,她说“愁劈了”,讲解员说“大喜”,她说“高兴毁了”……这个坊间故事让这个老人家一讲,怎么就那么生动?怎么就那么别致?怎么就那么可爱?是因为她的民间语调么?这典型的民间语调,简直就是珍珠泉本身啊。
忽然想,这济水的源头,到底在哪里?是太乙池还是灵渊阁?不,都不是。济水的源头,就是庙堂外的这股泉水,是这股任什么都压不住的活泼泼、活生生、活鲜鲜的泉水。还有泉水边的这些人:洗衣服的妇女、光腚游泳的孩子、撩起裙子洗脚的少女……水为民用。水即是民。“人民”这个大词,此刻,和水结合起来是如此适用。正是他们,一砖一瓦地盖起了济渎庙;正是他们,夯实了轵城的城墙;正是他们,孕育了愚公、荆浩、聂政、裴休……他们就是大明寺千年婆罗树上生生不息的绿叶,他们就是奉仙观坚若磐石的枣木柱和荆根梁,他们就是枋口广济渠守护河流的不朽堤岸,他们就是土地,就是一切的源头……可是,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就是这水?这泉水?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就是济源之源?也是文明之源,中华之源?
不由得笑自己问得矫情。难道不是么?他们知不知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永远在。也因此,已经不见的济水,就是一条永远也不会消失的河流。因为,源头的活水永在。
河岸之玉
新疆,新疆。在新疆的日子,我经常会神经质地念叨着这两个字。新,疆,真是一个好名字啊,尤其是那个疆字——只有新疆,才能担得起这个字。这个辽阔、苍劲的字。
没错,这个字,必须得用辽阔和苍劲来衡量。辽阔的地方不少,比如内蒙,但草原的柔美也只有用“原”这个字才最恰当。而只有在新疆,才是辽阔和苍劲兼容的。那是一种坚硬的、有力度的辽阔。无论是戈壁滩还是沙漠,无论是山峦还是河流。
额尔齐斯河也是这样。
在北疆的行程中,额尔齐斯河的波浪始终都陪伴着我们:在去喀纳斯的路上,在去禾木的路上,在去布尔津的路上……那时,在支流的局限下,这些波浪不得不暂时从属于布尔津河,后来一到北屯,这些波浪便拥有了享用终生的名字:额尔齐斯河。
那天下午,吃过饭后,我们来到了额尔齐斯河边。
首先看到的是那些大树。它们都已经死了,但仍然保持着它们的雄浑和粗壮。据说是因为额尔齐斯河的水量减少之后,它们缺了水,被渴死的。而额尔齐斯河之所以水量减少,是因为被人为地分流了出去。这样人为的干预,不仅让等待河水滋润的其他地方深受困扰,也让额尔齐斯河流域本身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这些死去的树,就是改变的结果。
这样的树,还能用来做什么呢?除了成为标本。我走上前,轻轻地抚摸着它们,这些大树。忽然想起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它们很像某些不合时宜的天才,诞生下来却百无一用,就是为了最后遗憾地死去。
河水少了,河岸的石头就多了。在北疆的每个小城,都可以看到“戈壁玉”或者“彩玉”的门店,据说卖的都是戈壁滩和河边的石头。
“捡玉吧!”朋友说。
于是,我们便在额尔齐斯河河边分散开来,捡玉。河岸很宽——额尔齐斯河这样的河,河岸肯定是很宽的,比河还要宽。我们几个分散开来的身影,远远地看去,很快就显得微如草芥了。不对,是微如石头。
石头真多。我蹲下来,去捡。一个,一个,又一个。石头们被河水冲刷了那么多年,都很光润。大的大,小的小,黑色、铁锈红色、土黄色,更多的是一种青灰色,像浩浩荡荡的额尔齐斯河河水。
我捡一个,丢一个。再捡一个,再丢一个。好不容易挑了一块满意的,看到了更满意的,就把手中的放弃了。我看同行的人,似乎也都是这样。我们都默不作声地捡着,捡着,只要听到某人惊呼,就知道他有了“艳遇”——遇到了自己喜欢的玉。
这么捡下去,也是能让人上瘾的。捡啊,捡啊,都知道该走了,明明也有人一遍遍地说道:“走吧,该走了。”但声音过后,大家还是会默默地捡下去,再捡下去。捡着,捡着,我的心越来越静。我问自己:你能捡多少呢?捡回去又能怎么样呢?放在你的案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看着满眼的额尔齐斯河石头,忽然觉得:对于捡它们的我们来说,这些与其说是石头,不如说是一种充满诱惑的嘲笑。
最后,我放下所有的石头,停了下来。这时的我,已经离河水很近了。被分流的额尔齐斯河依然有着让人敬畏的气势——可想而知它以前更胜的风采。这样有力的河流注定是不会太清澈的。它带着特有的厚重和浑浊向前默默地流着,流着,验证着孔老师的那句名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忽然想起一个小说的名字:《额尔齐斯河波浪》。那个敦厚的作家名叫红柯,他在小说中这样形容额尔齐斯河的波浪:“在晚霞烧红了整个额尔齐斯河两岸的黄昏时分,额尔齐斯河两岸的密林全都消失了,天空和大地也消失了,额尔齐斯河无比壮丽地流进太阳的洞里,太阳很快就被灌满了……那么大一条河都流进去了,太阳的肚子咕嘟嘟响一阵就没声音了。”
离开河岸的时候,我两手空空。
“没有喜欢的?”朋友纳闷。
“都很喜欢。”我说。
“原来是没法子挑了。”朋友调侃,“那就随便捡两块吧。”
“不想随便,干脆不挑。”我随着他说道。
是的,是都很喜欢。但是,我就是不想把这些石头捡回去。
“我知道了,你娇气,怕沉。”
“聪明。”我笑答。
离开河岸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些石头。就让这些石头待在河岸上吧,就让它们和额尔齐斯河在一起吧。就让石头归于石头,让我归于我吧。
在河之歌
那天,船在湄江河上缓缓地行着。船下是碧波清流,两岸是峰林茶坡,不时有白色的黔式民居闪现出来。看到我们的船渐近,三三两两的乡民停下了手中的劳作,立在河边默默观看,神情既庄重又闲适。那一刻,我忽然想,年年岁岁河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湄潭这个翠润的域名上,除了土地,还有什么事物能和这湄江河的河水一样长久呢?如果有的话,也许只有湄潭的那些民歌了吧。
第一次听说湄潭民歌,是从湄潭作家肖勤口中。作为东道主,她嘴巴不停地向我们历数湄潭的宝贝:茅贡米、湄窖酒、翠芽茶……说起采茶时人们唱的民歌,她引了几句歌词,一下子就把我震住了。其一《糠兜跳到米兜来》:“太阳落坡又落崖,丈夫赶场不回来。但愿丈夫摔崖死,糠兜跳到米兜来。”其二《不要死我的野男人》:“凉风绕绕天要暗,老鸹叫唤要死人。要死就死我的毛老公,不要死我的野男人。”毛老公,即亲老公,也是丈夫。即便肖勤解释说这种歌都是解放前包办婚姻女人没地位、和老公没感情、被老公欺凌才会有此怨毒之言,但是,如此赤裸裸地诅咒丈夫,这也实在是够狠。当然,也实在是直率得可爱。可爱的程度可与陕北民歌《兰花花》里的某个段落媲美:“兰花花我下轿来,东望西照,照见周家的猴老子,好像一座坟。你要死来你早早的死,前晌你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
湄潭几天逛下来,才知道还有更狠的,如《生要连来死要连》:“生要连来死要连,不怕雷打火烧天。火烧芭蕉心不死,阳间打死阴间玩。”又如《生一堆来死一堆》:“昨晚和哥住一堆,今天有人说是非。咬儿咬女任他咬,生一堆来死一堆。”“咬儿咬女”这个句子把我吓坏了,以为要拿儿女拼命,有多少灭多少。后来听肖勤解释说“咬”是诽谤之意,“生一堆来死一堆”的意思就是说要生死在一起,才稍微释然。
有多狠就有多爱,有多爱就有多柔,所以就有了这些甜蜜的比喻:“哥喜欢来妹喜欢,哥妹年纪是一般。妹是金鸡才开口,哥是小马才配鞍。”又有如此绵绵的询问:“月出东山明又明,情哥坐在斑竹林。学声猫叫来通信,要妹出来吐真情。”且有了这样软软的应答:“金竹篾条打提兜,提兜好打口难收。哥要情妹说实话,叫妹怎么不害羞……”还有如此坏坏的调子:“妹子生得嫩又娇,胸前鼓起两个包。哪天落到我的手,只见肿来不见消。”
如此宽阔的世界,当然不仅是男女情爱,还有如此单纯优美的抒情——《半夜起来望小星》:“半夜起来望小星,小星还在半天云。小星还在云中走,哥们还在路上行。”《恐防青苔顺水来》:“好久没到这方来,这方凉水起青苔。心想捧口凉水吃,恐防青苔顺水来。”还有如《栽葱要栽四季葱》般简洁的俗理:“栽葱要栽四季葱,栽花要栽月月红。四季葱来不怕冷,月月红花过得冬。”更有如《人别世间永不还》般的苍凉感叹:“人道老年一天天,好比日头落西山。日落西山明东起,人别世间永不还。”
后来得了一本《湄潭县民间歌谣、谚语集》,1989年出版,隶属于《中国民间歌谣谚语集成》书系里的“贵州卷”,我最先看的是书后所附的湄潭民间歌手小传。我是多么喜欢如此风格的简介啊,文理虽然不尽通顺,其中的赞美却充满诚意:“张福清,男,1923年生,不识字,洗马乡老水泉村民组农民,能唱上百首山歌,是村里远近闻名的闹师。”——春夏时节,湄潭的农民在田间坡头干活儿的时候习惯请人打锣鼓唱山歌用来鼓劲,打鼓唱歌的人,就是闹师。还有这个:“黄大军,男,1933年生。黄是道教的掌坛师,讲民间故事能手,也是著名的花灯手,是本地车车灯缺一不可的法海最佳人选。唱花灯和山歌更是见籽打籽,即兴创作,并会对歌。”该是多么英俊的男人,才会是缺一不可的法海最佳人选?该是多么智慧的歌者,才会见籽打籽,即兴创作?
集子分了好几辑。除了劳动生产、男女情爱,以及用在婚礼、建房、丧葬等仪式上的民歌,还有一辑是“时政歌谣”,当头一首是《清清流水一满沟》:“妹家当门一条沟,十多年来无人修。政府领导修水利,清清流水一满沟”。还有《毛主席指示合作化》:“毛主席指示合作化,天下农民笑哈哈。贫农带头朝前走,中农随后也跟他。”再往后就是《责任制来好处多》:“责任制来好处多,不计工分不啰嗦。出工不用干部喊,责任田里各做各。”歌颂合作化之后又歌颂责任制,对比得有趣。也有批评的,如《在斗大队当权派》:“那边开会站排排,在斗大队当权派。心想说句公道话,又说我是保皇派。”还有针对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共产主义大食堂”的《一进食堂门》:“一进食堂门,稀饭几大盆。边边起波浪,中间淹死人。”还有那些几乎可以读出跳皮筋般的节奏感的儿歌,如《一朵红花红又红》:“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真英雄。过去是个穷孩子,现在是个女英雄。乒乒叉!”又如《一把抓住周扒皮》:“周扒皮,五十一,深更半夜去学鸡。小朋友,做游戏,一把抓住周扒皮。乒乒叉!”
而最年轻的时政民歌,自然当属《十谢共产党》。这是兴隆镇龙凤村田家沟农民自编自演的花灯戏,在湄潭广为传唱,几乎人尽皆知。在田家沟的那个夜晚,就着熊熊燃烧的篝火,我看着舞台上的乡民用浓重的地方口音唱着《十谢共产党》:“一谢共产党,翻身把你想,以前我们做牛马,现在人人把家当;二谢共产党,吃饭把你想,以前忍饥又挨饿,现在温饱奔小康;三谢共产党,穿衣把你想,以前穿的蓑草衣,现在毛料新时装……六谢共产党,照明把你想,以前照的桐油灯,现在电灯亮堂堂……八谢共产党,看病把你想,以前有病无钱医,现在医药能报账……十谢共产党,养老把你想,以前抚儿来防老,现在丢心政府养。”丢心,湄潭方言,放心之意。
他们淳朴到近乎笨拙的表演让我莫名难过,几欲堕泪。说实话,无论新旧还是褒贬,这些时政民歌我都不喜欢。在我的心目中,这些都是伪民歌,都是“丢心”的民歌——把心丢了的民歌。一直觉得真正的民歌不应该有政治的影子,它应该是生活于土地最根部的人们在吟唱劳动,吟唱情爱,吟唱天气,吟唱岁月,吟唱人生,它应该如这湄江河一样,是一泓清水。政治的介入仿佛是一股异流,让它的成分和气味变得可疑……但是,且慢,难道政治不是这些人生活的一部分么?我怎么可以用自己单薄狭隘的喜好来做框定呢?——《诗经》中的“风雅颂”,“风”,就是民间歌谣。“颂”,套用当下的词语,应当就是所谓的主旋律。“风”漫漫而行,至四野八荒,凭什么就不能刮到“颂”呢?把“颂”从“风”里剔除干净,“风”难道就是最纯粹的“风”了么?这难道不是另一种矫情么?
所以,还是让这些民歌就这样存在吧。哪怕它们真是所谓的伪民歌,也是这里的人经历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与其他民歌参差交杂在一起,成为印证。正如集子的序言里所说:“……反映了解放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原貌,是难得的社会风情化石。”
风行水上,风声猎猎。船行河上,河水无声。肖勤介绍说,湄江河属长江流域乌江水系,发源于遵义市绥阳县的小关乡山羊口,全长151.7公里,自北向南几乎流经了湄潭县全境,是湄潭的母亲河——至柔至刚的河流,是大地上一切生灵的母亲,也是这些湄潭民歌的母亲。这些湄潭民歌顺着湄江河的波流,已经唱了不知多少年,更不知还将被唱多少年……渐渐地,似乎有粗粝劲道的吟唱飘至耳中:“你一声来我一声,好比先生教学生。先生教学皆有本,山歌无本句句真。”
我微笑。山歌怎么会无本呢?山歌有本。本就是世道。世道过处,秋波有痕。那痕就是这些民歌啊。那么世道的“道”又是什么呢?我家表哥是个老师,他曾如此对我说:“‘道’也就是真理,在天地间默然运行。”
河边吃鱼
其实,吃鱼是次要的,哪里不能吃鱼呢?重要的是去黄河边。
一直看见黄河,因在黄河边生长。有时候打开自来水,会想:这是黄河里的水。但是也就是这么想想而已。自来水的水是如此清透,被过滤过无数次,还被放过消毒粉……这水,和黏稠得似乎流不动的黄河水,不仅无法消毒还经常被排毒进去的黄河水,是两码事。
无数次从大桥上看过黄河。仅仅郑州市境内的黄河桥就有两座,一座称作黄河大桥,一座称作黄河二桥,简称大桥和二桥。大桥旧,二桥新。我经常过的是大桥。每次车从大桥上飞一般地过,我都有些微紧张,会控制不住地畅想:这桥上要是出了事,车是躲也没处躲的。只有撞向桥栏杆,只有掉进黄河里去。
黄河水看起来总是不大的,十里长桥,总是走着走着就会疑惑:怎么还看不见河水呢?待要觉得桥快走完的时候才会看见河水:那亮白亮白的一大缕光闪进了眼睛,越靠近,光越强,光带越宽。然而看见的时候,河水也很快就过去了。本来就不宽的河面还被泥沙淤出来的小滩涂分解得三岔两股,简直不成个体统,毫无威势可言。
但是有一次,过黄河桥的时候,车有小问题,下车查看,倚着桥栏站了一会儿,就感觉到了桥的柔软和孤单,似乎在风中摇荡的长桥只是一根不扎实的飘带,这流淌的河水倒是雷打不动的万年基业……那时候,看着黄河,微微觉出了异样。知道这黄河,和我平日里过桥看的黄河,不一样。
从市里出发,开车不过三十分钟就到了赫赫有名的花园口,上了辅道,我们便往堤岸深处走,走,再走。我总是有些担心,一遍遍地问带路的朋友:“那饭店是在黄河上吗?不是在滩地上吧?我不要在滩地上。也不是在小支流上吧?我不要在小支流上。”朋友一遍遍耐心地回答我:“是在黄河上。放心,是在黄河上。”
因是大雨初过,一路的树叶十分清新。在清新里,终于到了黄河岸边。几艘红红蓝蓝的渔船远远地立在河里,“张三渔家乐”“刘四渔家乐”“张铁蛋渔家乐”……每一家都挂着俗艳的招牌。
已经黄昏了。想来在别的地方应当都是一寸光阴一寸灰的,但在这黄河岸边,天色仿佛被凝固了一样,就那么亮着。坦白地,大大地亮着。
在船和滩地之间,搭着窄窄的过板。滩地很泥泞,大约是刚下过了雨的缘故。一脚踩下去,却也并不滑,只是深深地陷了下去。我穿的是布鞋,鞋帮周围霎时镶上了一道厚厚的黄边儿。脚也感觉润泽起来。这是黄河的泥呢。这么想着,飘飘然地欢喜起来。
上了船,我便只做一件事:看河。
河边宽得超出了想象,对岸的树像一圈矮矮的蕾丝花边儿。黄河水在船下无声地流着,却让我止不住地心惊:非常快,且有无数漩涡。浩浩汤汤,向东而去。不时夹杂着树枝之类的杂物。虽是极快,但河水却也是非常从容地、悠然地向东而去,只向那水天连接处——从地理方位上,我知道这河水会先到山东,然后是大海,但是,此刻,那河水只到的是水天连接处。
此时才觉得黄河有些黄河的意思了。
忽然想,要是跳进黄河里呢?“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说的是黄河的浊。但黄河,它是用来洗澡的么?
黄河,母亲。黄河,是母亲河——这些我当然早就知道。虽然早已经对动辄就把什么和母亲联系起来比喻的句式审美疲劳到了无动于衷的地步,但此时,此刻,看着黄河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比喻真是传神。
为什么黄河是母亲河,长江不是?我问朋友,朋友顺嘴说了很俗套的一些话,什么古代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暖和湿润得多,加上黄土质地松疏,利于耕种,十分适宜人类居住之类的话,说仰韶遗址、二里岗遗址、殷墟遗址,说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以及农业耕作、饲养家畜、制陶冶炼等等技术,比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因此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这些官话,不听也罢。其实我更想提的话头是:这是一个怎样的母亲?那些官话如果是凤冠霞帔的诰命夫人,我心里想的黄河,则是一个粗布跣足的自然之妇。她是如此家常,宛如天地里最一般的母亲。
——她当然不是一个最一般的母亲。
她气性大,甚至可以说是暴戾得很。不用查任何资料,口口相传的关于黄河的民间桥段我听了不知道有多少:蚩尤炎黄大战、大禹治水是最古老的版本,但我听到的大都是很残酷的,是开玩笑的那种残酷——黄河发大水,开封是钦定的黄泛区,现在的开封城下还有三层城,城摞城,城叠城。黄河水淹开封的时候,那里只剩下开封铁塔的塔尖。周口也是黄河亲密的泄洪区,那里的人以前都不养鸡鸭,房子都盖得极度简陋,衣服都没有装柜的习惯,随时准备着黄河发水抽身走人。而在与郑州遥遥相对的黄河北岸,有一座黄河第一道观,叫做“嘉应观”,就是为了镇水而建。黄河的水是滚地龙,河道变换无数,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到这里,几十里几百里都是她的地盘。黄河里的滩地都是看黄河高兴不高兴,高兴了就让人收粮食,不高兴了她就自己把粮食吞掉,因此滩地从来免交一切税费……当然,她也用她的水喂养了两岸的无数土地,一代代人。
这就是母亲河。
看了很久,很久。看不够。
去挑鱼。有条非常大的鱼从池里蹦了出来,鳞片闪闪发光,美极了,也有力量极了。
做好之后,有黄河的土味儿。
忽然明白:跳不跳黄河,都是洗不清的。因为一生下来,我就在黄河里了。我的血液和心脏,全都是黄河的基因。
已经八点多了,照片里的黄河依然很亮。
想起那个小说《深河》。
——靠近那条河,走进那条河,被那河接纳,成为那河的一部分。我是多么,多么想。
而其实,不用想,我已经是了。在黄河边吃鱼的我,生下来就已经是黄河里的一条鱼了。
现在,我吃的是我自己。
责任编辑 苗秀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