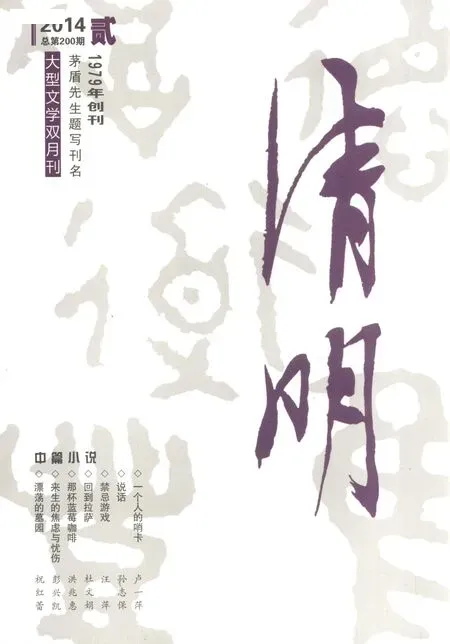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姜琍敏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姜琍敏
母亲的状态一天不如一天了。
到底是快八十的人了,虽然没什么大问题,老年人会有的麻烦她都有。血压高,血糖高,半身不遂,食欲不佳,精气神也每况愈下。原先还愿意让阿姨推着轮椅到街上晒晒太阳,着了回风寒后,轻易也不肯出门了。成天不是坐在电视前打盹,就是倚在床上发怔。汶川大地震让她振作了几天。几乎成天就那么眼睛也不眨地盯着电视,摇头、叹息、嘟哝,纸巾擦了一堆又一堆。阿姨悄悄告诉我,她还好多次逼着问她信不信人死以后有来世?还说,人这一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越活越不明白了。你说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那砸在废墟底下的老老少少,难道都是坏人不成?
我心里发毛,劝她少看点负面报道,少想些玄乎的事。她点点头,第二天竟再也不往电视跟前去了,就那么从早到晚歪在床上,睡一阵,醒一阵,嘀咕一阵又迷糊一阵,还老跟阿姨说她心里闷,净做梦!这显然还是不对头。我们三兄妹都怀疑她是不是患上老年忧郁症了,正商量着哪天劝她去看看医生,周末下午她却突然自己挪下了床,让阿姨打电话叫我们三兄妹下班后都回趟家。然后便坐在光线迅速昏暗下来的客厅里等着我们。阿姨让她先吃饭,她不吃,让她喝水,她也不喝。等我们三兄妹都到了家,她一本正经地让我把她推回卧室,指了指五斗橱,提出个让我们都大吃一惊的要求:
把那盒子葬了吧。
她指的是父亲的骨灰盒。父亲躺在里面已经超过二十年了。二十年里,无论我们还是亲戚朋友都劝过她无数次,她就是不同意下葬。每天亲自动手揩抹一下灰尘,也成了她雷打不动的习惯。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先斩后奏,买了一个双人墓穴,以新世纪的名义劝母亲同意下葬,依然无果。
没想到老人家竟主动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们焉能不为之惊诧?
更怪的是,下葬那天,母亲能下地,还坐着轮椅,亲手捧着父亲的骨灰盒,送到汽车前。临上车却坚持说她头痛,不肯同去墓地。这又是为什么?
直到我们从墓地回来,这个谜才得以揭开。
母亲说,有些话,再不讲你们就永远听不到了。虽然这些话我曾经打算带到坟里去,但好些天来,我总梦见你们爷爷。看来,他不肯让我就这么糊弄下去……
我的人生也许该从十七岁算起。
十七岁以前的我,好像早就死了。多少年了,我记不得,也不愿意回想十七岁以前的一切。倒是这两年,老了老了,旧事却越发清晰起来。许多事不断地浮在脑海里,压都压不住。但我还是不愿意多想那时候的光景。
我十七岁那年,正是老家解放的时候,1947年。
县城一夜之间成了解放军的天下。国民党县党部的牌子被解放军劈开烧了,换上了人民政府的新招牌。城关镇上到处是敲锣打鼓、挥舞着花花绿绿纸旗子欢庆胜利的人群,还有一连响了好多天的鞭炮和扭秧歌的队伍。扭秧歌的人中间有老百姓,也有打着结实的绑腿,穿着灰黄色军装,精气神十足的解放军官兵。
本来,这一年也可能是我的劫日。幸好父亲在此之前就有所准备。他把我托付给我幼时的奶妈、后来的帮佣,让我随她回到县城家中生活,对外面就说是自己的女儿。而他,作为四桥镇上的敌伪镇长,在观望了一阵以后,草草收拾了一些金银细软,带着母亲和小老婆,在解放军占领四桥镇前夜,逃之夭夭。
我那时并不很明白父母的感受,只觉得自己在县城的日子比乡下有趣。在此之前,我作为家中的千金,常年闷在镂花细格子窗后面,过着井底之蛙的生活。家中的种种清规戒律,让我的日子枯燥、阴郁而沉闷不堪。来到县城,心灵一下子获得了自由。又赶上这么个到处喜气洋洋的时代,顿时像一只挣脱樊笼的小鸟,满心欢喜。
但是那些天里,我也常常会无端地心慌气促。后来我明白了,我是在为自己的前途而迷茫。我不知道在这陌生的新社会里,自己这样的人能干什么?今后又该怎样活下去?
奶妈家后门外不远处,就是县学堂的操场。经常有解放军在那儿开大会,操练,讲演。口号声、军号声、喇叭筒的喊话声成天灌满我耳朵。
解放军的团部就驻在和县学堂一街之隔的玄清观里。
那里成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流连一番的地方。因为玄清观门口的空场上,经常有解放军的宣传队排练节目或者演出活报剧,宣传革命思想。我的脑海里很快就灌满了革命、解放、翻身做主人、男女平等、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等新鲜而充满强烈诱惑力的词汇。尤其是宣传队里那些剪着短发、穿着神气的军装,和男战士一样意气风发的女队员,她们可不是尽情呼吸着平等自由的新鲜空气的幸运儿吗?要是我也能像她们那样当个光荣的女兵该多好!
没想到,我的愿望竟轻易地成了现实。
我发现有个比一般战士长相老成的解放军军官经常出现在宣传队里,对他们的排练发表各种意见,举手投足间透露着坚毅英武的气度。他那笔挺的腰板上总挎着支驳壳枪,一看就是当官的。不知为什么,看到他,我的心总是有点乱,竭力回避他的目光或者掉头溜走。我很快察觉,他似乎也早就注意到了我,一出现在那儿,炯炯的目光就会穿透人墙,时不时地在我脸上扫来扫去。我不知这是为什么,更担忧他看出了我是敌人的女儿,心里总是像揣了块石头,沉甸甸的。
有一天,我又要躲开的时候,那个军官忽然穿过围观的人群来到我身边,把我叫到了一边。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方凤玉(这是我跟奶妈生活后改的名字,一直叫到今天)。他又问我读过书没有,父母是干什么的,我都按照和奶妈约定的说法一一回答了他。他又问我上过学堂没有,我说没有,但跟大人学过一些字(其实我是跟父亲请来的私塾先生学过几年的)。他转身指着远处一条横幅让我念。我张口念了出来: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翻身做主人。他哦了一声,问我天天来看演出,是不是也喜欢唱歌跳舞?我老实说不会跳舞,但会哼几句歌子。他立刻要我唱几句给他听听。我虽然很害羞,但直觉告诉我将会发生些什么,于是红着脸唱了几句“好一朵茉莉花”。
他的眼里大放光芒:很好很好!还会唱什么?革命的歌曲会唱吗?
我也兴奋极了,脱口就唱起刚从他们宣传队那里学来的新民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歌还没唱完,他重重地拍了下巴掌:唱得好!我们解放军就是刚从新四军改编过来的。怎么样,你想当解放军战士吗?
我的眼泪一下子飞了出来:想是想……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太阳被薄薄的云絮遮挡着,并不很亮。但是,它在我的泪眼中却陡然放射出万道金光,整个世界突然间就亮得如火如荼!
后来的事情,就像你们早就知道的一样,我不但就此成了光荣的革命军人,而且在宣传队和那个军官的教育引导下,很快明白了更多革命道理。参军三个月以后,就在那个军官的亲自培养和鼓励下,顺利地加入了共青团。
见我们兄妹三个都咧着嘴互相挤眉弄眼的样子,母亲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红晕:我知道你们笑什么。没错,那个军官,就是后来成了你们父亲的矫延山。当然,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当时他是解放军的团政治部主任,年龄比我整整大了十岁。我之所以后来会嫁给他,原因很简单,他是我新生命的缔造者,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我一开始就倾心崇拜的偶像。我们相遇那年,虽然他只有二十七岁,却已有了十二年军龄和十年党龄,还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培训过一年,亲耳聆听过毛主席的讲演……
小妹说:这些我们也早就知道啦。
母亲咳嗽起来,好像有一口痰堵在她嗓子眼里,憋得她满脸通红,眼泪直流。两个妹妹赶紧为她捶胸抹背。我给她端来杯水,她喝了几口后,长长地喘了几口气,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只是眼泪还是扑簌簌地流个不断。我劝她别说话了,上床躺着歇会吧。可是她推开我,拿纸巾擦了擦泪水说:不行!再不说,只怕没机会了——下面这些事,是你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我们面面相觑,一下子都挺直了身子。
人嘛,都会做梦,都喜欢做美梦。可是做得更多的是噩梦。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这场噩梦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也太残酷了!
就在1947年年底,我加入共青团没几天后,天真烂漫、成天沉浸在美好憧憬中的我,突然发觉自己已陷入了噩梦之中。
开始,是政治局势发生了不利的变化,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家乡一带开始了激烈的拉锯战,形势暂时向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演变。
时值隆冬,整日里寒风呼啸。满眼望出去,天上愁云密布,地上残雪斑驳,光秃秃的树林子里,只见枯黄的枝条向天乱颤,看不到一丝绿意。远处还断续传来闷雷般隆隆的炮声。
敌军一天天逼近县城。我们的宣传队早已停止排练和演出,正在配合团部机关,忙着做各种战略转移的准备。
一天晚上,熄灯号都吹响了,矫延山突然让哨兵把我从宿舍里叫了出去。他在前面大步走着,我在后面慌里慌张小跑着。很快,我们来到营房后的小树林前。借着清寒的月光,我发现矫延山的脸色苍白而严峻,锋利的目光定定地罩在我脸上,那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神情。我突然有一种恐怖的直觉,浑身上下遏止不住地哆嗦起来。
见我这种反应,他的表情松弛了些,但说出的话,仍然像晴天霹雳般在我心头炸响:方凤玉同志,现在我代表组织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你对我完全可以,也应该说实话。我机械地点了点头。他劈头便问我:你其实是四桥人吧?
我木住了。
你父亲是四桥的敌镇长李儒才吧?
我还是没开口。
一见我这个反应,矫延山嗨一声挥起拳头,重重捶在自己腿上。
我哇地恸哭开来。矫延山慌忙捂住我嘴巴:哭不得!让人听见就糟了。我赶紧强噎住哭声。矫延山安慰了我几句,见我情绪稳定一些后便说:首先我必须告诉你,团首长刚议过你的问题。根据目前的局势和你的实际情况,我们不会对你做任何处分,但是……你要被清除出部队。
我瞠目结舌,刚要哭,矫延山厉声喝止了我:但是,你还有唯一一个机会,如果你能经受住这个特殊考验,我向政委保你留下来,估计还有可能。我赶紧问是什么考验。他尖锐地逼视我好一会才说:不管怎么说,目前,你已是一名革命军人,对不对?我用力点头道:矫主任,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死也不愿离开部队……矫延山一挥手:这就好。所以你要经受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团里刚决定,在战略转移前,要处决一批在押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恶霸,其中就有……你爹。他是前不久被地方武装从山里抓到的,昨天刚押到县里来。押送他的有一个四桥的地下党同志,他无意中见到了你,所以揭发了你和他的关系……
天旋地转中,我根本听不清矫延山后来都说了些什么,只模糊地明白,他给我的特殊考验是:作为一个共青团员、革命战士,我必须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用大义灭亲的实际行动,和反动阶级、反革命家庭彻底决裂,才能获得党和革命军队的谅解——他要我在明天上午的公判会上,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和控诉父亲的反动罪行。他反复启发我说:革命军人是最大公无私的,我们党的好多同志都是大义灭亲的楷模。因此,你要忘记他是你的父亲,要多想想他的反动罪行。你要认清,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长期欺压剥削劳动人民的大地主、大恶霸。而且,他还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国民党镇长、民团团长,直接参与过屠杀新四军和地下武装,双手沾满了革命军人的鲜血……
那一夜我根本没闭过眼,一直在被窝里偷偷地流泪,在极度的矛盾中煎熬着。虽然我当兵只有几个月,可是通过不断的教育和熏陶,阶级斗争、革命、共产主义理想等观念和对新生活的渴望,已经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相信矫延山是真心在挽救我,我也清楚挺身而出大义灭亲是一个革命战士必须具备的阶级立场。但我毕竟还小呵,而且,李儒才毕竟是我的父亲啊!过去那短短的十七年中,由于父亲经常不在家,我对他似乎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毕竟血浓于水,平时他对我也还是呵护备至的。因此,他在我心目中无论如何也不是一般人眼里的地主、恶霸、吸血鬼。我家是有不少地,父亲也常年做着贩卖棉麻的生意,但印象中的他,无论对我还是对外人,总是笑眯眯的,一脸和善相。当然,这可能是剥削阶级的伪善,但家里的佣工们似乎也没有流露出什么怨恨。我清楚,父亲当国民党的镇长和民团团长并不是他情愿的,是县上多次诱逼的结果。我并不知道他究竟都干了些什么,让我揭发,说些什么呢?
辗转矛盾中,我好几次想爬起床逃走。但每当此时,矫延山的音容就会浮现在我眼前。他的神情和言词又让我重新获得了勇气。何况,我能逃到哪里去?就算逃出去了,顶着个逃兵和反革命、恶霸女儿的帽子,我又如何活得下去?
仿佛倏忽之间,公鸡嘶鸣,窗纸泛白,军号也响了。这平时让我分外振奋的军号声,此时竟像催魂令一样让我心惊胆战。我一跃而起,草草洗漱过,一口早餐也吃不下,就揣着颗怦怦乱跳的心,随着队伍来到了刑场……
母亲顿住了,双手紧捂着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庞,泪水从指缝中簌簌滑落。
我们都不知所措,只好尽力安慰她。我说:妈,你别内疚了。毕竟都是那个时代的事了,我明白你当时的处境,换了谁都……
母亲拍了我一下:谁也别安慰我。我是过来人,道理我不比你们懂得少。我后悔的并不是那天的揭发,而是……
刑场就在玄清观后面山坡下的一小块断壁前。团政委和矫延山威严地坐在一张香案后主持会议。与会的还有一部分团部机关人员、全体宣传队员和一些地方代表,大约一百多人,围着长案排成个半圆。矫延山宣布公审开始后,战士们把父亲和另外六个待决犯押到了会场。全部都是五花大绑,背后插着写有打了叉的名字的纸牌,一个个背朝崖脚、头朝下跪对着人群。父亲跪在正中间。
整个过程,直到宣读完对每个罪犯的公审词,我都一直低着头缩在人后,心惊气促,头晕目眩,浑身抖个不停,一个字也没听清,一眼也不敢向父亲那边看,更不敢接触矫延山的目光,甚至暗暗希望他会改变主意,不再要我上前揭发父亲。可是突然之间,矫延山离开香案,大步走到父亲面前几步远的地方,向着我一招手,大声说:现在,由方凤玉同志揭发国民党伪镇长、大恶霸李儒才的反动罪行!
随着脑袋嗡地一响,我的呼吸仿佛突然停止,脚也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挪到父亲跟前的。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面对我时那一刹那的怪异表情。只见他挣扎着抬起头来,先是万分惊愕而凄苦地望了我一眼,当确认是我时,他的表情竟瞬间化成一丝欣慰的惨笑,随即深深地埋下了头。
呵,他的脸色是如此憔悴,头发和胡须也不知有多少时间没有理过了,如果不是那一丝惨笑,完全就是一具死尸!
我心如刀绞。如果不是残存的一点理智牢牢抱紧了我,我真会扑上去,搂住他,亲吻他,扯掉那些绑得他像只粽子的麻绳。甚至,用胸口挡住那些即将钻进他肉体的子弹。
你,你,你这个恶霸……你这个地主……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欺压人民,剥削农民,你罪大恶极……我要和你彻底决裂……
大脑一片空白的我,完全是背书似的硬吐出那些在心里强行默念了一夜的词语。令我方寸大乱的是,父亲竟应和着我的控诉在不住地点头。当我中断无语的时候,他竟还小声而急切地说:说呀,赶紧说呀闺女……
我彻底崩溃,张口结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了。
方凤玉同志——耳边传来矫延山焦躁的喝声。我无力地看了他一眼,只见他眼中灼灼如火,狠狠瞪着我,那神情分明焦灼而紧张。我更恐惧了,身子打晃,无数金花如蚊群在眼前狂舞——就在我即将倒下去之际,矫延山一把扶住了我,并迅速拔出驳壳枪,哗一下打开机头,塞到我手中。我朦胧意识到他的意图,倏地挣开他,随即软软地瘫倒在地。
失去意识之前,眼中掠过的最后一个情景是:父亲本能地挣扎起身子,似乎想来扶我——但与此同时,啪啪两下枪响后,他像一截突然被伐倒的枯树,一头栽倒。
血,我清楚地看见了父亲头上巨石击水般喷溅的血光……
那两枪是谁开的?我们异口同声叫起来。
当然是矫延山。
太不可思议了!
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李儒才的死是铁定的,无非是谁开枪而已。别说他那时还没有和我明确恋爱关系,别说他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革命军人,就是一般老百姓,就凭着地主、恶霸、阶级敌人这样的字眼,你叫他杀掉一个李儒才这样的人,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可是,李儒才毕竟是你父亲呀,为什么你后来还要嫁给他?
为什么我不能嫁给他?他那么做是为了挽救我,开枪也是因为他误以为李儒才要扑上来伤害我。而且,如果不是那一次的表现和他的竭力维护,我必定会被逐出部队。作为一个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女儿,离开部队我寸步难行。在接下来的战争和一项项运动中,我不死也必定会脱几身皮——当然,我后来的人生也依然充满了坎坷和磨难。我再也没能加入共产党,矫延山也因为娶了我而备受牵累。早就是团政治部主任的他,此后又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八年多,最终只当到副团长,转业到地方后,一直到死都是个副局长……
谁都没再出声。
母亲反倒平静了,仿佛是一下子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她轻松地出了口长气,然后轻抚着胸口,久久地凝视着窗外迷离的夜色。
窗外赤橙黄绿,远处光焰烛天。无数高楼大厦的灯饰都在争奇斗艳,天空上还交互划动着条条镭射的光柱。相形之下,圆圆的月亮显得黯然失色。
天上是不是也这么红火呀?
母亲忽然冒出这么句话来,我不禁感到脊背上一阵发凉,走过去拉严了窗帘。
母亲笑了笑,目光又挪到搁在柜上的父亲遗像上,默默地看了好久,说:老头子,索性让我把什么都说了吧。
父亲向我们微笑着,似乎表示着默许。而他这副我们看惯了的慈眉善目,此时却让我备感异样。
其实,刑场上的一出,都是你爸预先设计好的。
让我当众控诉父亲的罪状,只是一个序幕。在他看来,当我慷慨淋漓地揭发以后,顺势把枪给我,我亲手结果父亲的性命,是革命意志坚定的最好证明。他没料到我竟表现得那样软弱,于是便亲手击毙了李儒才。虽然这不是他的职责所在,但也绝不是他后来向我求婚时对我辩称的那样,他是误以为父亲会扑上来伤害我才开的枪。他清楚当时父亲的心理。但是他有这个权力,也完全符合正义。他这样做,无疑可以在将来向公众证明,他作为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女婿,早就选择了正确的立场。
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有了那一幕,他仍然饱受牵连。但谁知道呢,如果没有当年的那一举,他娶我作妻子,付出的代价恐怕会更加沉重!
记得那天我问过他这么一句话:你怎么在当时就会考虑到那么多?
他的回答是:因为见到你的第一眼时,我就看上了你!
这些,都是他在临终时亲口对我说的。那时,他作为走资派、地主恶霸反革命的孝子贤婿被批斗、游街几个月之后,又查出肺癌晚期。但因为上述身份而得不到正常治疗,只能痛苦万分地躺在家中等死。
他还说,他之前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年那一举,因为从他的身份和立场上来看,当时他不仅有权力那么做,也完全符合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判断。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于是,我又问他:既然这样,为什么你现在又告诉我这些,干脆把它们带进坟墓不就得了?
他的回答是:我品尝到了作为一个敌对分子的滋味是怎么回事。而且,我现在才更深地意识到,对着一个阶级敌人开枪,和对着一个自己心里清楚他实际上将是我未来岳父的人开枪,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希望得到你的谅解……
——这就是我后来始终把他的骨灰盒放在身边的缘故。
妈,能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想的吗?
母亲脸上微微地泛出一丝红晕:原因我不是都说了吗?而且,当年我也是第一眼就看上了他。
那么……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为什么你又突然要把他下葬呢?
母亲不住地摇起头来:好些天了,我总是梦见父亲,清楚地看见他那胡子拉碴、惨不忍睹的脸,那最后一丝惨笑和那喷溅而出的血光……也许,这是他向我要求什么吧。
说着,她吃力地挣了一下,我们赶紧将她扶到床上躺下。竭力劝慰了她一会后,准备关灯退出,她却又叫住了我们:该知道的,你们都知道了,最后还要请你们答应我一个要求:等我死后,别把我埋在你爸那里,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如果老屋附近有地方,就在那儿找棵树埋了。如果没有,把骨灰撒到屋后的山上,就让我在那儿陪陪父亲的孤魂吧……
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据阿姨说,她走得很平静。后半夜还叫阿姨喂了她几口水,天亮时再看她已经没气了。这就是无疾而终吧。
真的无疾吗?
我们不愿细究这个问题了。处理完后事后,我们兄妹仨有过一场小小的争执,但最终达成了一致。我们还是决定违背母亲的遗愿,将她送到父亲的双穴墓里。
相信母亲不会怪罪我们。
想来,外公若是地下有灵,也会理解我们和母亲,甚至,还有父亲。
地下和人间应该是不一样的。
没准,他们现在就聚在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吧!
责任编辑 刘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