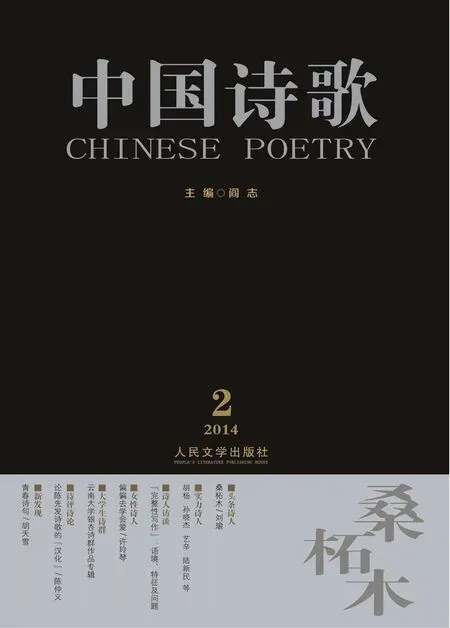陆新民 的诗
在知觉中,忙碌与迷路
风在无知无觉地吹
风很有些暖
我遗失的手又被找了回来
一道遗失的还有我的声音
它也回来了,从那座
我思忖谋面的危楼里
幸好,它没如无数老弄堂消失
现在我用手拿着声音
打开三分苗圃,风大口喘息
说这里没有人
我有些不信
春天正沿着燃烧的花径
趔趔趄趄
在看春天扶着这些草儿的腰杆
这些草儿不同于女贞
这些草儿在听到某个召唤后
才开始慢慢返青
这些草儿从土中伸直腰来
睁大了明亮的眼
是的,这些草儿
草芥,可有可无
轻如尘埃
人们一向视而不见
当它们在严寒里流泪时
天空与大地一样灰暗
清晨,我在三楼
隔着玻璃看草儿
草色好看
一阵神秘的风吹过之后
天空也开始好看
在雨中奔跑
二月的雨不紧不慢地下着
我在雨中跑着,跑湿了衣服
我还是跑在了雨的前头
我跑进了宿舍,雨只能在后面
徒劳地追着
它一定不只在追我
事实上,它已把一些随意
喷在了我的头发之上
衣服已忽略了
两分钟的路,它让我记住了它
以及无处不在的深渊
我很少这样奔跑,在二月
在二月的雨中
这不是跑步的时候
我一旦静下来想着这段经历时
才发现自己,与雨实在有些相像
在疲惫的状态,被红灯纠缠
它的光是温柔的,却比铁还硬
它分分秒秒,在死去
活过来
它是机械的。这座城市
有比它急躁的声音,在提醒
没有人在意,须处处在意
它已融入了社会的命
然,它极是自由的
一种遨游天地的大自由
在我忽略它的时候
你忽略它的时候
我们忽略它的时候
它在笑。我是说
假若有一首写它的诗
陈腐,冥顽,打上火的烙印
在凛冽的风中读一本诗集
一叶在飘,青青的叶
风把它从树上摘下来
一首诗也在飘,风
让我们聆听,并且记住了它
迁徙的喊,还有
难以觉察的小地震
它何其敏感,多疑
它伸出了手掌
我们记住了足踝
灵魂如沙画,如烟
在火的法则里,一句偈
世界,在你的注视下
变为灰烬
一柄很亮的斧子,一片青瓷
讨论存在
遮蔽的涅
泛着情欲的蓝
风在啄啮晚钟
崩溃责求、欲望
一句偈语挤出缝隙
百灵鸟打开月光
在中交二公局项目部高歌:桥乃水中捞出的路
感谢那只江鸥飞过
带着它的桥
那只疑似唐朝的鸟
让桥更像一粒种子
多么朴素
清晨,薄雾如雨
一粒种子
很多人在描述,在理解
但谁能有我这般深情?
在高高的白玉兰树若隐若现的香息下辗转
整个晚上我都在想着那棵树
白玉兰树。我从未见过这么高的
香花簪满夜空的树
它高过毗邻的五层楼,它的浓荫
淹没了停放的考斯特、别克、凯美瑞
和一台风尘仆仆的巡洋舰
一些花瓣落在这些车上
暗暗的白,寻常粗野的铁家伙们
仿佛也变得温柔
想那些玉兰花儿是自由的
也是高不可攀的
想一定会有很多人
徘徊在它若隐若现的香息下
譬如我,一个晚上都有所思
在愈甚的夜色中
它只为自己开放,而
大自然的采撷之手
也将与它一同消失。只我
辗转,与
一个风雨大作的桂林
在到处漏风的夜听一只蝈蝈
弱弱地,叫了
穿过窗帘,轰轰作响的空调
夜也活泼了几分
只叫了几声
就把我抛在阳台上
孤独大了,窥伺
(蓦然想起,熄了灯的萤火虫
蝙蝠拿去当了点心)
谁的目光如此之空,欲填平
到处漏风的夜
噤声。我已逸出
在寥廓的流年,流转
一骑轻裘,将你
从百里之外载来
约见,一段风云诡异
向美,向恶。而我们假设运道使然
轶事合上卷宗,只把花信暗丢
承接者却如此难耐
如空手接一滴想象中的雨
锦水汤汤
情如柳丝徘飞
心如深藏的岩礁
印证属于海平线
说困厄,月华试图扼守?
无异,词锋
削成旷世沉默
在状态
一小撮光在前方不停地闪着
一列车整体不动,举行庆典
椰叶轻拂,弯拐得有些温柔
蜗牛在不经意的踌躇中
一脚破门
日子挑上黑亮的睫毛
一股股水,嗓门儿分裂
在梦魇之上
吼声又起。好看的路
生出无数花木小径
来自古罗马的小伙捏着绿球
神情肃穆
而,这个方位将适度移交
结尾是一只水老鼠,偷采莲花
余音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