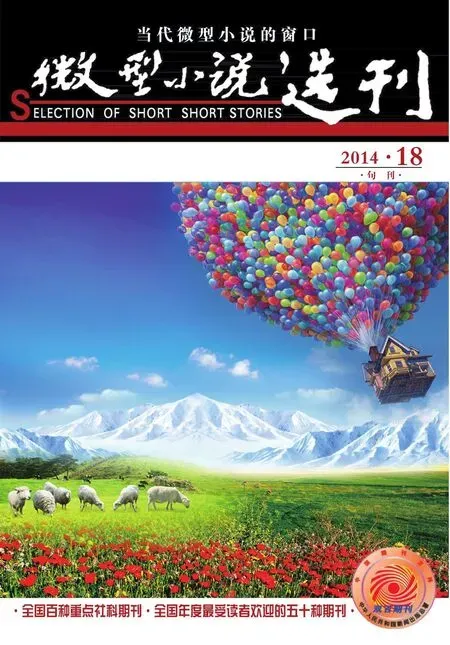弥 补
□猫郎君
弥 补
□猫郎君
冲动是魔鬼,无端的善心,也许也是。
我的第一个朋友自杀后,我辞掉了在工厂里组装手机的工作。他死前告诉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木偶,但我知道他不是,他从楼顶跳下,摔出了很多的血,在冬天里热气腾腾。
我决定去抢点什么,直截了当地改善或毁掉我的人生,我搞到了一把假枪和一把真刀,这已经是我能力范围内的极限了。我先是想到了银行,但银行更像是一座坚固的城池,我单枪匹马,应该难以打破它。于是我决定退而求其次,去洗劫一家相对柔弱的金店。
我选择的目标在一家商场里,确切地说,它算不上一家店面,只是几个围在一起的玻璃柜台,两个懒散的年轻女孩把守着它。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勘察地形,拟定计划,当这一切都万无一失后,我却胆怯了,一连四天,我每天背着挎包,坐在商场供顾客休息的塑料座椅上,盯着不远处的珠宝柜台,积攒着冲上去砸碎玻璃的勇气,但这勇气就像绵软无力的海浪,涌上来很快就退下去。我孤零零地坐着,仿佛被搁浅在这里。
我是从第二天开始留意到那个女孩的。那天,她从外面走进来,经过珠宝柜台时停住了脚步,弯下腰朝柜台里看。她穿着一件廉价的红色收腰外套,那是一款城市女孩不太可能会穿的衣服,被她洗干净同时带点土气地穿在身上。我想起上午曾在门口见过她,她鲜艳地坐在一棵刚刚被移植到马路边不久的银杏树下,用一种纤长的草叶编织蜻蜓、螳螂和蚂蚱,摆在一块花布上以两元一只的价格出售。她很沉默,手指却异常灵活,草叶的边缘很锋利,在她手上留下了许多细小的伤口。
第三天和第四天,在差不多的时间,她都短暂地出现在柜台边。我知道她看的是项链,那个柜台里只有项链,铂金的,戒指则是在下一个柜台。她想要一条项链,但却不能如愿,只能用眼睛隔着玻璃抚摸它们。那天下午,我站在路边默不作声地看她编了一会儿蜻蜓。她想用这些草来换一条铂金项链,这太难了,不是不可以,只是太难,难得让人心寒。
我回到商场,从挎包里拔出榔头和塑料手枪,走向珠宝柜台,只一下,玻璃就碎了。周围开始有女人发出尖叫。我丢下榔头,手伸进柜台,抓起满满一把黄金白金塞进挎包,转身朝商场深处冲去,那里有一道员工进出的小门,平时虚掩着。我飞快地穿过这道小门,再翻过一道墙,从楼后的小巷顺利逃离。大概是看在那把塑料枪的面子上,没有人出来追我。
一周后,我戴上口罩和风帽,打了一辆车来到商场门口,她还在树下编织着昆虫,身形同那株不知能否成活的银杏树一样单薄。我走过去,弯腰把一个扎着绳结的小盒子放在她面前。她抬起头,诧异地望着我,嘴巴里忽然发出啊啊的声音,双手飞快地比划着,像是在询问我,我木然地盯着那两只用来说话的手,转过身离开。
几天后,我离开这座城市试图南下,半路上被抓,接着被判刑十年。第二年,我结交了一个新来的狱友,他叫白彪,我只知道他是个杀人犯,被判死缓,对他的入狱原因,他一直讳莫如深。
每年都有一两次,我会梦到那个女孩,她带着我送她的项链,看上去很开心。在梦里她还是十八九岁的样子,但我知道,十年过去,她最少也该二十八九岁了。如果在街头偶遇,可能我已经认不出她了,除非她还坐在商场门前的银杏树下用草叶编织昆虫。
出来后不久,我去了一次那里,树还在,她自然不会在,十年那么久,天涯又那么远,谁知道她会去哪里呢!
我找了份在物流公司搬运货物的工作。又过了九年,我唯一的朋友白彪出狱,为他接风的酒桌上,他喝得有些醉了,终于说起了入狱的原因。
“我原本只是想偷她那条项链,从没有想过要杀人,可那个哑女拉住我不放,情急之下,我只好捅了她一刀。”他叹息,“被关了十八年,就为了一条破项链,怎么想怎么不值。”听到酒杯落地的破碎声,他抬起头,诧异地问我:“你怎么了?”
(原载《新聊斋》2014年第5期 吉林李仁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