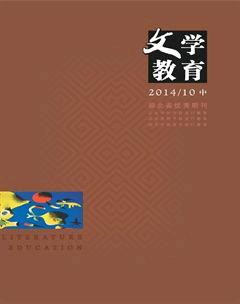王维融禅入诗浅议
[摘 要] 王维融禅入诗,源自士大夫的审美习惯与生存理想。禅宗思想对王维的影响体现在闲适静谧的生活情调、直觉彻悟的艺术思维和层层疏离的诗歌艺术上。通过对言、象、意的多重潜藏,王维营造了高远澄明的艺术境界。
[关键词] 王维;禅;生活情调;艺术思维
王维诗歌所营造的禅境正是士大夫渴慕流连的精神家园,而其中的禅意禅趣既使他们难以把握,也刺激他们反复探究。禅宗思想对王维的影响除了体现为生活方式上的亦官亦隐,更多是对其思想、情趣的熏染,特别是对其艺术思维的重塑。通过对言、象、意的多重潜藏,王维巧妙地澄清了杂虑,营造了高远澄明的艺术境界。
一、生活情调
王维字摩诘,其字来自佛典《维摩诘经》。经载:维摩诘混迹于宫廷市井,吃喝嫖赌,但精通佛理,“深入微妙,出入智度无极”;“虽为白衣,奉持沙门至贤之行……有妻子妇,自随所乐,常修梵行”,于是最终成佛。《维摩诘经》宣扬“无缚无解,无乐无不乐”的人生境界,提出“宴坐”的修行之法,把禅定变得随意方便。正是因为喜爱这种修行方式,王维才取此经之名为字。
他的早期诗歌就已经呈现出诗、禅结合的特点。《淇上即事田园》约作于开元十六年,诗曰:“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三曰:“右丞诗长于山林。‘河明闾井间一联,诗人所未有也。‘牧童、‘田犬句尤雅净。”对这个评价,许印芳很不以为然:“右丞诗笔,无施不可,特以性耽丘壑,故闲适之诗独多。虚谷遂谓其长于山林,岂知右丞哉?”[1]从禅的追求来说,许印芳的眼光明显高于方回。中国化了的禅,不要求人们执著,执著即是障。士大夫既想混迹于朝市,也想流连于山野,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无疑是最能打动他们的生存状态。然而出处升沉,并不为自我掌控,即身在何处需要忽略,则追求自在自足的心理闲适就有了特别的魅力。
“朝隐”方式由来已久。西汉时,东方朔曾经作诗自嘲:“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2]王维的“朝隐”思想却不同于前人。东方朔的行与藏由外界所决定,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在禅宗影响下,“朝隐”获得了佛理上的支持,变得明确清晰起来,成为士大夫立身与处世的双重保护伞。
朱光潜在《诗论》中说:“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3]王维的思想历程,就其个人来说,有艰难不得已的成分;就士大夫群体来说,却是一个成功榜样。他亦官亦隐,居士而僧,僧而官。不论穷通,皆能自得其乐。他始终能逃离纷繁外界,时时沉浸到自我世界中,在静谧观照中体悟生命,获得艺术灵感。因此,不仅身在何处需要忽略,连自身都要忽略,那么,庄子就不必标榜怀才隐居、桀骜落拓了:他应该无才无德,和光同尘,彻底融入自然,达到涅槃之境。
入宋以后,士大夫心性更加规范,士人群体开始追求禅风禅趣。禅融入了中国士大夫的生存智慧、思维习惯和审美定势。王维被尊为“诗佛”,正是得力于浓郁的禅风禅趣。
二、艺术思维
禅虽然帮助诗人获得了“心源澄静”,也使诗歌艺术更加难以为普通大众甚至文人学士所理解。面对这种必须凭借直觉体验才能把握的诗歌,如果没有与之相同的文化素质、艺术思维,就难以领悟到其神秘内涵。
禅宗特别重视“诸佛说心”。这个“心”,一方面是个体独特的内心体验,不足为外人道,即使道了外人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另一方面,它就是禅宗所宣扬的“宴坐”之法:通过静谧观照,把握内在本真,从而彻悟通达,获得大智慧;这也是言语所无法传达出来的一种心理体验过程。
禅宗心法非常切合士大夫的审美情调:禅宗鼓吹“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一阐释方法,神秘、朦胧、主观、含蓄,符合士大夫沉默内省、宁静闲适的情调。因此,禅影响的诗人,一方面其感受非常空虚,因为这个感受非常模糊,难以明确说出,诗人自己也未必真的已经有了什么明确感受;另一方面,其感受非常灵活,它强调顿悟、彻悟、妙悟,在沉思冥想、直觉体验、模糊把握的状态下,获得艺术的自然自足。
魏家川在《审美之维与诗性智慧·前言》中说:“就审美思想的历史文化语境而言,中国古代审美诗学经历了子学期的‘求言内,玄学期的‘求言外与禅学期的‘求意外,飘逸灵动、高情远韵、无言大美的庄禅诗性文化,是其美学底蕴,呈现为道的不落言筌、禅的不可凑泊、诗的不著一字这种道、禅、诗三位一体的异质同构,孕育出中国古代审美诗学‘但见性情,不睹一字白色神话般的空灵含蓄之美。”[4]相对于儒家的比类直觉、道家的意会直觉而言,妙悟直觉具有不可理喻的神秘特点。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诗人的情思意趣,往往超越功利、不问逻辑、直指内心,成为特定情境下冥想的展示。这一点,在王维画中的表现就很突出。宋人沈括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5]
王维不顾外界的客观局限,着力表现一己情怀,颇有点“我思故他在”的味道。雪里芭蕉,现实中不可有,但禅化的士大夫心中不可无。这样一种超越实体、彻悟把握的努力,正是士大夫高雅艺术让人疑惑不已又让人赞叹不绝的原因所在。
三、艺术经营
受禅宗影响,王维在作品中传情达意的方式是否也有其独特之处呢?笔者认为,这个独特之处就在于潜藏,或者叫做偏离,包括言、象、意三个方面。
其一,言的淡泊
王维诗歌语言总体上透过了对语式的消解而超越于形式之上,显得非常单纯明晰。尽管诗人以淡语经营,却能有力地传达出浑厚思想与静谧情思。为什么要努力追求这样的语言风格,我想禅宗思想也许给过他明确启示。
《青源惟信禅师语录》载:“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禅师所经历的思想变化,虽然仍旧回归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过程。因此,要想把握诗人隐藏到文字背后的哲理情思,就需要获得某种类通的彻悟,才能捕捉其淡泊之外的浑厚绵长。endprint
如《辛夷坞》:“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本诗语言浅淡异常,但其内在情思非常浑朴深厚:
山涧寂寞清幽,毫不影响花朵的蓬勃生机。它在寂寞中开放,又在寂寞中凋零。它得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它没有追求,没有哀乐,泯灭了时空界限,给诗人心灵带来了巨大震颤。这空谷中的花开花落,像极了王维戏剧性的一生。作为一代才子,他少年得志,名闻遐迩。但终其一生,颇多坎坷浮沉,仕途极不顺利,竟至险遭杀头之祸。可以说,没有经历过生之烂漫,何来落寞与感慨;没有品位过生之寂寞,何来自在与洒脱。
诗人眼中的花,是其人格理想的寄托,是其内在精神的外射。这样一个幽深、空寂的境界,正是“静虑”佳处。诗人心随境寂,安禅入定,忘掉了现实纷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份宁静柔和之境,把了无牵挂、四大皆空的禅意表达得一览无遗。
宗白华认为:“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二元,也构成‘禅的心灵状态。”[6]69可以想见,诗人一看到这盛开在山涧的孤寂花朵,他的神魂就为之钩摄,他的情绪若惊若喜,霎时心无旁骛。诗人以极平极淡的语言,展示其对生命的直觉体验,领悟到天人一体、物我同构的大千精神。
其二,象的疏离
王维的辋川系列,写景而志不在景,其笔下之景乃胸中之景,却不等于诗人眼中之景。以《辛夷坞》中的“芙蓉”为例。首联曰:“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诗人模糊了物象,引得后人曾争论这到底是木芙蓉还是辛夷花。表面上诗歌只是说,花朵高高地站立在枝条顶端,象一支婷婷的荷花箭;花朵的红艳明媚,“木末”的瘦劲枯涩,映衬出一种孤芳高绝的气质。实际并不这么简单。
诗人为什么要以“芙蓉”来代指?原来,芙蓉即荷花,乃是佛花。禅宗传说:世尊释迦牟尼欲传妙谛微言,于是拈荷花而立,只有摩诃迦叶心领神会,微微含笑,于是佛祖便传法于他;摩诃迦叶遂为禅宗初祖。王维专勤佛事,又诗画兼善,以“木末芙蓉”比喻辛夷花,既使花之形神飞跃,又衬人之心理意趣,可谓绘形又取神,心深而意邈。
禅的整体观照思维甚至影响了诗人观“象”方式。宗白华曾举王维《北垞》分析说:“在西洋画上有画大树参天者,则树外人家及远山流水必在地平线上缩短缩小,合乎透视法。而此处南川水却明灭于青林之端,不向下而向上,不向远而向近。和青林朱栏构成一片平面。而中国山水画家却取此同样的看法写之于画面。使西人诧中国画家不识透视法。”[6]
“以大观小”,以我观物,远近取与,俯仰自如,而外在宇宙遂而融通为我心中之宇宙。所以,西洋人难以理解的观照之法,在中国诗人、画家看来却意味深长。
其三,意的潜藏
在诗歌中,王维往往努力潜藏其主观思想。王维始终没有离开过官场,他的诗篇却一直以隐士面目出现。诗人并没有真的要逃遁,逃遁姿态是作给读者看的。尽管诗人从未认真去追求像陶潜那样“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但他笔下的世界似乎毫不在意人世的升沉荣辱,完全忘情于自在自然的山野。诗人努力诱导读者偏离物欲思想,同时又潜藏自己的物欲思想。读者从诗歌中感受这种诱导,并为此留连忘返。于是,其诗歌完成了从写作到阅读的价值生成过程。
即便是官场唱和诗,王维也隐藏了自己的仕途经济,努力营造超脱旷达的唯美意境。如《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田雯在《古欢堂杂著》卷二《论五言古诗》中说:“摩诘诗恬洁精微,如天女散花,幽香万片,落人巾帻间。每于胸念尘杂时,取而读之,便觉神怡气静。”贺怡孙在《诗筏》中进一步评价了由此带来的艺术特质:“诗文中‘洁字最难。……诗如摩诘,可谓之洁。惟悟生洁,洁斯幽,幽斯灵,灵斯化矣。摩诘之洁,原从悟生,而摩诘之洁,亦能生悟,洁而能化,悟迹乃融。嗟乎!悟、洁二者,今人弃如土矣。”
物欲需要潜藏,即便是非物欲的禅意追求,同样需要疏离。禅宗要求潜藏个体的强烈欲望,一旦这种欲望得到张扬,哪怕是禅意的过分宣泄,也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淡淡的禅意,淡淡的悲喜,才是恰到好处。王维以淡语、口语营造禅意禅趣,其诗歌对禅的引入始终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所以显得既有禅的余味,又无禅的枯涩。赵殿最(见赵殿成《笺注》卷首)曰:“使人索之于离即之间,骤欲去之而不可得,盖空诸所有,而独契其宗。”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也评价说:“王右丞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
然而,当王维偶尔过分执着于禅的时候,他的缺陷也开始呈现。《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第二联一向为人称道,而末两联也不少诟病。从艺术角度看,后四句枯燥说教,纯粹是宣扬佛教教义。正如李梦阳在《空同子·论学上篇》中所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奉佛之应哉!人心系则难脱。”联系全诗,可谓兼而有之。这也说明,诗、禅融合,是永无止境的艺术追求。
结语:在王维的世界里,禅已经融入其生活、思维和创作中。在旁观者看来,这个世界非常独特,充满诱惑又难以把握,值得模仿却难以企及。“艺术要求自我孤立的欲望对于集体的控制来说是一个威胁,因为……这样的孤独任何人都可以利用。”[7]宇文所安认为,独特和追求独特,是一代代诗人吸纳累加、不断往复的艺术追求。禅在静谧之中观照自我,排斥同流;诗歌也正要追求不同流俗的特立价值,二者融合更促进了遗世独立的旨趣追求。这种孤芳自赏的诗歌技艺和自得情趣,又激励诗家追求完善自我,彰示才情,凸显价值,从而烙下别具一格的人生印迹。王维融禅入诗,努力疏离各种浅层欲望,但也造就了一座“诗与欲望的迷楼”。
参考文献:
[1][明]顾可久注,《王维诗集》,抄本。
[2][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
[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4]魏家川,审美之维与诗性智慧,首都师大出版社,2000。
[5][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
[6]宗白华,美从何处寻,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7][美]宇文所安著 程章灿译,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三联书店,2003。
作者简介:索凯歌(1977—),女,汉族,江苏省邳州市人,上海市华师大一附中初级中学,中教一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