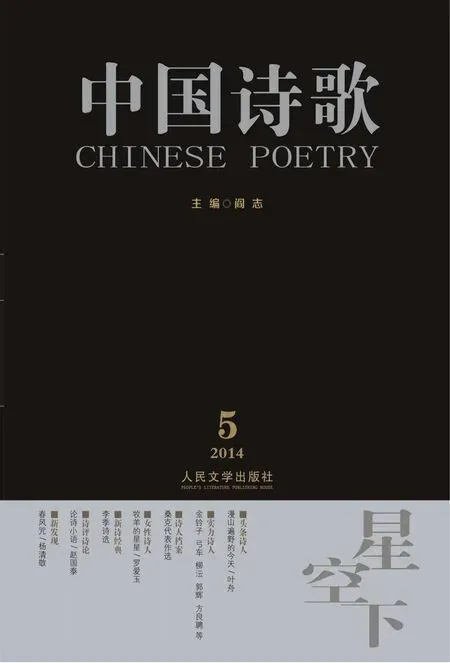论诗小语
■赵国泰
论诗小语
■赵国泰
其实,这样的诗人就很幸福,就算不朽了——活着的时候,被人遗忘;去世以后,被人长久地记着。
就在你为自己无情可抒而发愁的时候,在你身上蕴藏着的感受正处于沉睡状态,或者是正急迫地在寻找着上升的出口。这时,你剩下的工作就在于准确地找到出口处,大胆地将这诗魔放纵出来。
真正能产生广泛影响的诗,一般都带有行为色彩,也就是说,这种诗已经不仅仅在于供人欣赏,它更多的是能咨询和参与人生。
最好的诗,都往往是由于一种遗憾的人生情境引起的,如两地悬念、两情违和、物是人非等等,都可能成为好诗之坯。
诗人啊,愿你是人类的情人,世界的哲人,诗的“匠人”!
情人是指对人类的热爱,哲人是指对世界的概括,匠人则是指对诗的规律的遵循。否则,涅克拉索夫就不会那么殷切地吁请诗人,像铸造金币那样铸造诗吧!
由于我们对“匠人”的蔑视,结果受到相对应惩罚:既当不好情人,更当不好哲人。
一茎新绿和一片绿海相比,一茎新绿更能激发诗人灵感。尽管二者都是具有生命情调的自然景观,但由于后者充塞于我们的视野,给人既成的满的感觉,满则无诗;而前者正惟其“量”少,便展开了一片期待视野,呈示出一种新生美,从而提供给诗人以更空阔的想象空间。
大家在于天才,
天才在于忍耐。
人问沈从文创作奥秘,答曰“耐得烦”,即此意也。
重要的诗人、诗评家,首先表现为作品产量至丰至巨。这是精品与垃圾杂出,奔涛与泥沙俱下的一道长河大川。
写出一首一首好诗、一篇一篇好文章,使我们在诗坛慢慢地变得重要起来。
哲云:“危在于累,势在于积。”“积渐为雄。”能不信欤?
讲究群体效应,必定是每个诗人都以牺牲自身的风格、特质为代价,或干脆就是以无风格、无特质为前提,消融在苍茫无涯的群体宣言里。
诗坛群体效应成为非个性化的根源,尽管它不无人才学意义。
对朦胧诗从以“古怪”相侃,到以诗美相誉,其间几乎用了八年抗战的时间。
时间使价值浮现,论争使本体澄明。
雾区能见度渐次加大,朦胧诗与读者相互被发现。尽管在论争文章里都免不了硝烟反应。
后之诗是否能通过同样的过程完成它与读者的精神联系,只好留待时间卓裁。
一个诗人一个诗评家,如果拥有一千名读者,并且恒久地保持着忠诚,那么这个诗人、诗评家就是幸福的了。
定量分析、目标管理,可以给予我们更科学的迷狂,更清醒的自足。
然而,我们,有吗?
当诗歌处在假大空的非诗时期,诗歌远离读者,人们多么渴望诗歌作本体回归啊!而一旦诗歌与本体接近乃至重合,即沉溺于文体实验了,诗的读者便再度远离了自己的家园。
是否至少应该有部分诗歌在似与不似之间为佳呢?我们是曾有过这种黄金时期的啊!
诗歌创作是一种沉潜的个体劳作,在诗坛浮躁的今天尤其应该这样。让我们回到各自的村庄,隐姓埋名,朴素地生长。
但这并不排斥诗人们宁静的集合,如同风中稻菽的交头接耳一样。
从现在起到未来无穷个世纪,诗歌的民间性色彩会愈来愈浓。民间性预伏着它的生态危机,也规定着它的朴素和坚韧,同时也教给它一个生存法则:自己浇灌自己。
假设诗人是一粒石子,他被缪斯女神丢进奇妙的湖里。当他通过湖面时,便扰乱了湖上的纹圈;而当他落到湖底时,他就变得十分宁静。联云:“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此独学者为然耶?
我们大多数诗人正在通过湖面。其中有的人也许只能宿命般地在湖面漂浮,成为宁静的骚扰者;
已经或开始接近湖底的只是少数人。
当生命找不到一个哲学家来说出她的心思的时候,她就产生一个歌唱家来唱出她的心情。
所以,我们常能在诗歌中感到哲学的“累”,也就不奇怪了。
敢于涉足各种文体的诗人,无疑是勇士;而敢于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点诗,这个诗人更具有勇士的纯粹。
大诗人里尔克尚且讲:一个诗人经过毕生用心,也许能写出十行好诗来。
难道我辈还不该对此表示出足够的敬畏,对面临的各种诱惑,投以果毅的拒绝么?
赞美劳动这很重要。劳动创造世界。赞美劳动的诗流通世界。于是,我们用诗“风景着一种劳动”。
不过,你的诗“劳动”过了吗?
诗人往往首先观照距离他最近的对象。当他发放出了持久的、足够的光芒时,他发现并深入了审美对象,读者则发现并深入了他。
世界的内在奥秘,最初往往只有少数人知道,这少数人就是诗人、先知和美的揭示者。
假若诗人必须直率地说话,那么就直率得漂亮一些;要不就沉默下来,像一盏灯、一面矿壁或某个象征体。
能引起一般读者吟诵的冲动,
能引起其他诗人写诗的欲望,
这样的诗,往往是好诗。
一首诗不能给人一个敏锐的新质点,势必遭到我们视觉的放逐。
诗止于说出了某个独特的东西,非诗止于说出了某个东西。
一名中年男子或一位半老徐娘,在一番整饰后,自我感觉是良好的;而一旦进入少男少女中,就无情地被区别开来了。
少男少女一首诗。在他们年轻湿润的声音中,我开始感伤自己的衰老。较之他们,也许我们多了一点什么,但肯定少了一点什么。那是什么呢?
我们的老辣,功力,沉稳;
他们的清新,自然,活泼。
在和青春的残酷对弈中,让我们一起把自己输掉!
在每日每时的生活进程中,诗人都会遇到一些“小火花”、“小激动”。有的诗人遇到一个写一个,写得再多,小的也大不了。有的诗人则加诸积累,使之成为诗情的霞光,成为大激动。前者是量的增加,后者是质的变化。在一座不显眼的分水岭上,界划出一般诗人与优秀诗人。
每一首诗都应该是仅有的,尽管它也是共有的。似乎可以说,“共有的”给予诗以物化或外显的普遍形式,“仅有的”则给予诗以主导美学性格。每一种仅有的表情都丰富着诗的微笑。
最清浅的诗歌往往能够把握最广大的读者。
咱们老百姓的情感是容易被俘虏的。但他们又还拥有强大的直觉能力,对于不得其入的艺术“黑洞”,常常表现出一份拒绝的疏离。
从本质上看,中国人民仍然是诗的人民,因而也就需要人民的诗。当然这应该具有无比的丰富性,因为一朵花主宰四季的年代早已成为了旧布景。
做一只翱翔天空的鹰和做一尾沉潜水中的鱼,对于今天的诗人来说,似乎更应该做后一种选择。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的形而上的天空,现在需要的是对生活海洋的投入,而且它正在汹涌起伏地等待诗人从中汲取养分、力量和自由。
诗坛已经变成一座大客厅了。诗人们都讲着“客厅语”,并配合着耸肩、鼻音和高雅的手势。
“工人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我很想将这渐渐远去的诗声拽回来,借助黄钟大吕的震荡,让“客厅”出现哪怕只有片刻的宁静;
“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我多想借助这种伟力,将“客厅”移到民间,以清新刚健的气息,实现哪怕只是局部的弥漫。
以诗的文体规定性论,以诗的传统论,以诗的优势论,在这风雷激荡的时代和瞬息万变的生活进程中,诗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样式之一。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诗的功能、诗的效应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可怕的弱化。昔日的荣耀正在黯淡,王冠已被历史无情地摘去。
放下芦笛、举起号角和放下号角、举起芦笛,作为一种提倡,它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具体到一个诗人的操作,其在转换的实现上则是困难的。因为长于芦笛的往往拙于号角,长于号角的常常短于芦笛。因此,诗坛在遵循庄严而崇高的美学导向时,还应允许每个诗人将自身风格发展到一种极致。惟其如此,才有可能酿成诗中丰富的交响。一片芦笛或一片号角,对于历史的内在要求、人们的审美需求,同样是单调的和缺乏力量的表现。
诗与社会的关系就有这么奇特: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讲,我们不提诗歌为政治服务,它们不再是臣属仆从的关系;然而从诗歌本身的角度而论,却不能不把触角伸向政治。这是因为,从现在起到未来的一百年,中国最大的政治是改革。它与诗歌——这人类情绪最直接、最敏感的记录员,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缘关系。兹事体大,关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诗人是应该很“投入”而且甘愿“投入”的。何须问,这些年来诗歌地位的崛起与陆沉,诗歌发展史已经写明: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如何,将决定着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科学的抽象使世界失去了血肉,诗则把血肉还给世界。由于互补,世界才理性而丰满。
如果我们老是呆在别人的作品和理论里,那么,对于诗的认识,将会总让我们莫衷一是。其实,你的最好的一首诗就包括了诗的全部奥秘,它像琥珀是自然和历史的浓缩一样。你的发展的逻辑起点就从你自己的这首诗开始。
一方面,我们要拥抱现实。可是,要让现实飞翔起来,必须借助现代意识、现代技巧的武装,才能实现这种飞翔。
另一方面,诗歌中的抽象、玄奥、形而上的因素过剩,而现实生活的成分则越发稀薄。
作为诗人,我们要如一位老诗人所劝诫的那样,对上述情形作出如下调整:
让现实更现代一些,
让现代更现实一些。
填补空白,其实这是指思维框架、思维成果是“空白”,而用以作为思维的材料还是潜在的,既存的。难怪有哲人断言太阳底下无新事也。当你欣赏自己的空谷足音时,不要忘了传播回声的石头。
人文论战,百鸟清音。但在日益啁啾之中,人们陷入多元的困扰。什么论题都难以归于认同、共识,乃至任何认同、共识都会遭致模式、僵化之讥。这就影响到理论的形成,规律的揭橥,学术的完善发展。“多元”在思维上表现为发散状态。发散了还须收束,收束即意味着认同、共识的结晶。若发散而不收束,包括诗学在内的人类思维,势必流放于无序、混沌之中。
你感到渺小:这诗坛有几人熟悉我?
你为什么不抚膺自问:这诗坛有几个是我熟悉的?
我们评论一个人的诗,不是要看他写到了一些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写到了一些什么独特的东西。陶潜诗云:“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二理一揆。
不会淘汰,也就不会选择。
不会选择,是因为还不懂得哪些必须淘汰。
一个人的佳肴是另一个人的毒物。在为青年诗人制定“食谱”时,诗评家可得当心啊!
有艺术抽象特点的诗,一切都在一种虚化状态下进行。往往具体物象很少出现,多为一些观念性形象,即意象或形象本身带有某些约定俗成的社会寓意。这类诗不宜多写,否则就会逐渐将艺术生命“抽干”,以致变为一具空壳。
意象的叠加形式,能形成境界上的“多雾”,造成结构上的多维,酿成韵调上的多味。
长期专攻某种体式,戴着脚镣跳舞,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应该算是冒险的选择;但同时也应看到,这是具有当代意识的,与古典律绝和现代律诗等诗歌传统的深层衔接,它对于无边无际的现代派诗歌是一个可贵的反拨。
如果说,让喻体与本体之间故意“对不准”,是诗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在本体与喻体之间表现出准确而绝妙的对应关系,则一定是诗歌把握世界的基本的、有效的方式之一了。
哲学惯于冷智,即高贵,冲淡,精确。在认识的主体与对象之间,表现为“一纸之隔,一点就破”,但又不同于率直,是有起伏地显出反差,从反差中倾出剖切的快感和解颐的韵致。
诗歌则惯于炽热。常常表现为妄人谵语,云天雾地,读者见怪不怪。一旦冷智,这诗便成为哲理诗,或诗中的理论部分了。
一名年轻女子偏要嫁给比她年龄大几层的男人,结缡为老夫少妻。有人阻挠,她则死活不依;有人白眼,她便报以一瞥冷傲。这是她情感和意志的表现。
有人写实验诗,对旁人来说同样是没法子的事儿。这种诗是作者审美情趣之所在,是主体生命展开的一部分。倘不让写,这不等于要了人家的命么?!
勿矫情,乃作诗百戒之一。如果谁坚持认为,矫情也是一种个性特色,那质朴就只好保持沉默了。
清浅的人难得深刻,深刻的人难得清浅。清浅理应获致公正的价值判断,因为拒绝艰深、崇尚清浅已越来越成为艺术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似乎有些逆势飞扬了。
凡是出行必有邂逅,而且邂逅便是一种新的关系。诗往往就诞生在这种幸运中。它与封闭型诗人无缘。
诗中需要概括部分。全身浑圆者给人以虚浮感,而某一部位出现铜干式肌块,非但不会让人感到干瘪,反而只会给人以力量美。诗的概括,会给诗带来紧致、犀利乃至高贵的精神气质。
对于诗歌,当文本有了某种深度时,人们往往批评它没有接受美学意义上的宽度;而当作品有了一定宽度时,人们又嫌它缺乏文本深度。其实,能拥有任何一样优胜都是可贵的。它失去的恰恰是它得到的;或者相反,它得到的是它失去的。
“回首”,是人类对自己的历史,社会的、心理的历史加诸检视的虚化姿势。这种姿势频频晃动在诗歌中,是诗歌产生历史感的根据。
现代诗着重于智力结构的建设。这当然是对读者智商乃至智慧的挑战。人们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和新古典主义的触目即是的感悟,而是凿壁偷光式的破译。美感在艰涩中酿成。
或许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认可:晦涩也不失为诗歌的一种艺术风格。造成晦涩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它的咏叹是超验的,对超验的内容如果绳之以经验的理解,料必难以认同;其次,域外诗歌文化的渗透也会使作品呈现斑驳风貌。晦涩的诗如果从果园里长出来,一定是槟榔。
一般在时空交替期、转折处,人们易于产生心理变化,这也正是诗的产生的契机。成功的诗篇,都是诗人及时地把握住了契机的产物。
读者从有些名家笔下,只看到愈来愈多的方块字,而发现愈来愈少心灵的皱褶……
在诗中,人们可以说的是一件事,指的是另一件事。
本质上是双关的或多义的象征艺术,常常能产生这种阅读效应。
形而下的处境,决定了有一类诗人的创作,势必有向高处飞翔的生命欲求,尽管大限带给他的常常是遗憾的艺术结局;而追求形而上意蕴的诗人,久之,总得返回结实的地面,因为他的心无法解脱那象形了千年的炊烟的维系。这是两股气团的对流,它标志着人类精神的流动与互补。
“在某个晴朗的冬天”。“某”字是诗人用来造成模糊层面的指代符号。它的通体洋溢着一种酒神精神。醒是文心,醉乃诗趣。对精确性的漠视,起源于对诗的不定性的重视。
小麦。麦地。玉米。农业。这些语象以全新的光芒直射过来,使我们变得敏感,也使我们变得脆弱;客观存在养育了我们,也娇惯了我们。人们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对重复、拥挤、模仿报以不安和隐忧。
一次性不是文化的特性。造物的敏感阶段并不意味着成熟。重复、拥挤、模仿是细嫩、密集而上升的窑火,它正在进行着定型、规范以及釉质的给定。理性教导我们,这样耐心地对待诗歌文化的创造和积累。
能从生活的灰烬里拨出一簇美丽的火星,这需要诗人的耐心、智慧和审美理想的合作。
感情的物质资料来自大自然。诗人一般不取都市意象,因为都市太过坚挺,过于物质化,难以提炼出和谐的诗美。
假如我们敢于承认——我只会写诗或只会评诗——那么,种种欲望和诱惑便会崩溃并迅速退出我的滩涂。然后在平静的海韵里,坚持弯下我卑微的腰,仅仅提供缪斯接受的天然风味。
当文学提不出什么问题的时候,其社会影响将会被削弱一半。
文学是一种艺术。如果把文学仅仅看成是一种艺术,就不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甚至会出现“0拷贝”纪录。
“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这就是魔术。”这一美国魔术理论,与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庶几相若,即艺术家最大的本领就是将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联系起来,并且勾连得那么好。诗人就有这类绝招,即“远取譬”,它特指比喻两者间的距离越远越有力。“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诗人把异质的事物通过想象叠加在一起,构成匪夷所思的意象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即魔术。
诗人深入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即寻访。若纯乎在一旁静观默察,便只能得到直觉印象,而不能触碰到抒情的活魂,即人的灵魂。因此,旁观者的创作,要么借助生花之笔,大描外部世界;要么有赖浪漫假想,纵笔雾地云天。
诗人对生活的接触,既像新闻记者,又如小说作家,似与前者更相迹近。这就要求诗人学一点记者的本领。当然,记者——诗人对生活的接触和把握的方式,不是同心圆,而是交叉圆的关系,即既有交叉、重合部分,更有诗人服从诗的规定性,描述世界的特殊部分。
某些寻访诗之所以装饰虽盛实则空泛,是由于作者当时体察不够,沉淀不够,酿制不够,及至搦管为诗时,就不得不离开描述对象的真实性和独特性,而以固有的对彼事物的印象来套取此事物,以装扮彼事物的饰件来装扮此事物,这便是事情的原由。今日之果,异日之因。
“通感句”是当代诗歌语言的一个突出现象。它特指感觉上的相互沟通与转换,词语上的相互挪借和指代,如从书包里掏出自己的书,变异为掏出鸟的翅膀;再如一头栽进失望,坐进孤独,捻着寂寞,是将作为宾语的名词变换为形容词。另一个特点是实化与虚化的互渗,如月光拍翅,是虚象(月光)实化(拍翅);又如,坐成山峦,则是实象(状态)虚化(缥缈)。
通感句的审美功能在于突破拘泥,翻空呈奇,这与虚实相生、意味隽永的诗歌文体要求正相切。难怪诗人用之成瘾、读者吟之心醉啊!
创造出新质的东西——在诗人那儿,有时是就他与整个诗歌审美潮流而言,有时是就他自身而言。也许,他正在进行着的,是审美潮流已经历了的过程,但对于他自身来说,则是在有过一番痛苦蜕变后的“接轨”。这时,“旧”的也仍是“新”的。
文学上的从无序到有序,从一种秩序到另一种秩序,往往就差一道勾连,一种范式,一次转换。完成它的,总是一位时代感受能力特强的作家。一部新感觉作品便能使人们蓦地安静下来,继而轰动起来。他是文学新秩序的天然组织者。在文学内空间(文本)已经失去英雄的时代,在文学外空间(文坛),却频频跃现各领风骚的英雄。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是一位杰出诗人,多年来为我国青年诗人喜爱而加以师从。这位总统诗人成年前一直受的是法语书面教育,并用法语写作。但他始终没有被异域文化所同化,不但未被俘虏,而且首先揭起“黑人性”的旗帜,写诗求本溯源——有历史感。其得力于:首先是“童年王国”这片丰饶的文化沃土培育了他,园丁是大舅、女诗人、巫乐师等;其次,同时汲取异域的文化精华,以本民族感情为底座,金字塔般超拔而起;再则是受到朋友的智慧烛照。这三点中以第一点殊为重要,所谓名满天下而根在“童年王国”。
儿童模仿前辈,这是顺乎自然的受哺法则;至于儿童之被模仿则要困难得多。有关学者就曾指出:“原始人和学龄前儿童的绘画自有其独特的,不可模仿的艺术魅力。”看来,中老年诗人乃至青年诗人,要保持童心将是徒劳的,表现在诗歌情调上的“中年天真”、“老年天真”,往往就很可笑。也许,在成年情思中适度掺入儿童天真的思路尚可一试。
记忆是相会的一种形式,审美记忆则是心灵对唱的一种形式。因此,许多在人生旅途中跋涉已久的诗人,不时闪回童年,俯饮这道珍泉,以解心灵的焦渴。
杰出的诗人,是长生不老的乳牛,对于一代代的读者来说,其奶汁从来是新鲜的。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斯蒂文森的《一个孩子的诗园》等等,正是这种新鲜奶汁。它成为一茬茬小读者心灵中最纯正的,永漾着的审美养分。
桌上摊放着出自一位少年手笔的诗集。当我读这册诗时,思路常常跳到别的金苹果上。那是少年普希金、叶赛宁笔下发出微响的蓝色小雪橇,是春夜稠李树静静吐着清香的农庄……那是少年顾城长久地凝望过的露滴,孩子的眼睛,安徒生和韩美林的童话世界……美好丰富的诗篇应该是人类声音的集合。一个少年人偶尔的抒情的颤动,兴许影响到人类的终古的情绪。隔代少年之间的感应,则是心灵自由飞翔中的美丽邂逅。
金石无言,因槌而响。这槌是诗人的化身,它从对象世界获得金声玉振的诗质。
草木无情,因风而唱。此风乃抒情主体的心语,自客观对应物获得抒情性和歌唱性。
西哲艾略特,以及好些港台诗人的写作模式:一边作诗,一边论诗。这样似乎可以互为参证,互为疏松。
寻访需要独自盘桓,反复体验,不宜大队人马来去匆匆,浅尝辄止。诗美的隐蔽性和感觉的有限性,决定了诗人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
西方诗重意象,东方诗重意境。意境的一大支柱是“遗憾的意境”。其通俗的定义是:先满意,后引憾;先甜蜜,后苦涩。美好的只存在于记忆之中,眼前的一切昨是而今非。遗憾的意境一般涵有悲剧之美。
忆念诗较之行吟诗,其异趣在于:前者意蕴亲切、细腻、深沉,后者则多有不逮。由此可见情感积淀对诗的助益之大。而时间是这杯美酒的最忠实的酿制者。
据说,美国某地有一条公路,急转弯处立了一块很大的路标,上面画了一位很美的姑娘,下面写了一行字:“我喜欢开慢车。”人们驱车至此,自然就慢了下来;而我们的公路急转弯处,却往往总是一个“慢”字,或一个“!”。警告虽然严厉,有的司机却视而不见,仍旧开他的快车。
诗人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写诗,用情不能太急、太切,表现不宜过直、过露,而应通过一种美,一种心灵美、人情美,去感化人和唤醒人。情在婉处求,意于曲中达。
诗歌要表达的是情感,表达不了的也是情感。所要“表达的”是诗的本质特征,“表达不了”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
文学理论年景颇丰,论家纷纷出来论衡说项。在几堆干草之间,怎么挑选?诗人是会饿死的。
“赤霞纱里跳着一炷笑”,“青铜鞘里跃着一柄笑”(朱大楠《笑》);“宁可死个枫叶的红”(朱湘《秋》)。此为减字艺术。以朱湘诗为例,减去的可能是“红色”,可能是“血红”,可能是“霞红”,给人留下的联想余地很大,权称之为“待字联想”。在一首诗里,也许正是由于有了一个或数个这样富于活力的部位,才给全篇注入了强健的活力。
写诗的时候,诗人的情感状态究竟是怎样的?有的是火山爆发式的冲动,激动得发冷发热发颤;有的是在一种愉快的心境中完成诗篇。正由于这样,才有了《女神》和湖畔诗,才有了《雷锋之歌》和江南曲,如此种种。这就是说,情感状态,既有沸点纪录,也有零度风格,更多的是温润如仪。概括地讲,它是以真挚为基准,尔后再分强弱与否。每一种状态都有可能产生好诗。
诗追求无言之言、无意之意的境界。在无声无息的地方,诗就是声音。
不要鄙薄流行性,也不要反感先锋性,只要诗人的艺术态度具有严肃性,就都有产生重要作品的可能性。
大自然在自视甚高的人类那儿,只是一枚小小的胸饰,而在富于童心的诗人和孩子的眼里,则是伟大而亲密的朋友。他热爱天上的一帕流云,甚至是大森林里小木屋上的一垄白雪。我们被流云和白雪唤醒的,除了纯洁情愫,还有灵动的思维和观念。
忽视我们难以理解或不能容忍的艺术现象,是一种软弱;粗暴的、简单的非议,同样也是一种软弱。
对主题题材渴望征服,一首诗,就是一场滑铁卢战役,它应该驯服在诗人的鞭子下;而一旦进发,它又萧萧跨跃于一种理想的范式里。
读者并不欢迎非诗意的模糊性,即思维上的胡天野地,语言上的笔力不逮,而需要的是诗意的模糊性。它是含蓄的深化,意味着把这一传统审美范畴推向了新的极致。
纪实文学是对社会的大曝光;散文随笔是对灵魂的大抖落;诗则是给梦赋予一个戏剧形式。
这样的评论家是睿智的——既要注意作家在“写什么”,也要注意作家“没写什么”。因为“没写什么”时,往往是作家正处于积累、酝酿、反思、突破的隐蔽过程,实乃不写之写。
诗人心境是一只气球,它需要元气内充;优秀诗人的心境则要三倍地充盈。
这时,你若分心去写散文、小说或别的什么,无异于在气球上捅了个窟窿。
诗用形象思维,这时诗是缪斯的灵性女儿。
而用抒情形象包装的哲学,则是她智慧的儿子。
社会已经不再需要诗呐喊,诗当然就彷徨乃至沉静下来,在理性和物质的扰攘中享受孤独。
而一旦需要诗人放下芦笛拿起投枪,那将意味着诗人的有幸和我们政治生活的某种失误和不幸。
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减肥,是祖国苗条的象征;诗人沉静,是社会安宁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