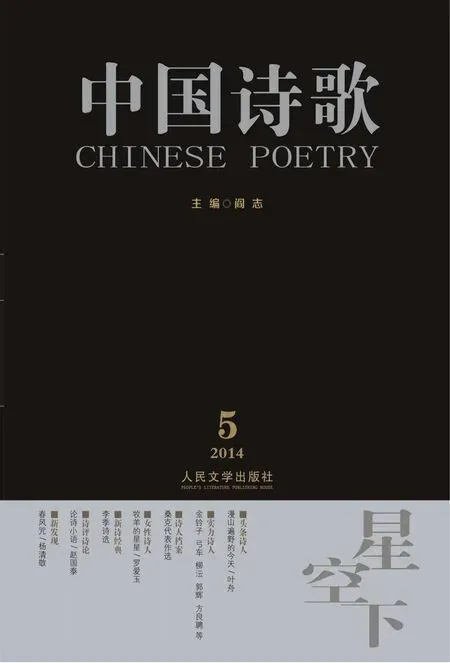漫山遍野的今天
叶舟
漫山遍野的今天
叶舟
叶舟一意孤行的抒情如语言的电闪雷鸣,是向内、向外的驰骋,诗与大地“漫山遍野”的通灵。他的口吻来自谣唱、祷辞、私语和誓言的混响,他的信仰是萨满、佛学、度亡经的混融,寂灭与绚烂同在,决绝与鲁莽找到了一位高超的骑手,突然的戏剧化转化为牧歌长调的庄严。诗人在语词的四壁之内点灯、取火、焚香,拓展了语言的疆域,于激越和嘹亮中,渐渐呈现出一种“辽阔的美”。叶舟的“边疆诗”,是诗对大地的供养,言辞对遗忘的拯救。一位坐下来抄经的中年,依旧保有少年“滚烫的体温”,并怀揣一个秘密:“将一本经书/砌在了天空的佛龛”。
——沈苇
漫山遍野的今天
我不想去纠正时间,实际上,
万物葳蕤,
银河无恙;我纠正的
是爱,一次回眸,
一粒暗夜中
疼痛的心跳;
我纠正的是火中的栗子,
风中的鹰,
一台无助的天平,以及
那个夏天遗失的
鞋子。
他们在诉说不幸,
但那是别人的苦难——
比如漫山遍野的今天,我写下
这一串忐忑的
省略号……献给你!
朝觐
在深处的大漠,一眼石窟一行热情的鹰
一介僧侣,抱着半本经无法立地
难以成佛。
——明月前身,遗址像一场干旱的夜宴
曲终人尽,充满寂灭。
我是最后一个走的,锁住灰烬的门
盖好水缸与龛笼
伸手拉灭灯绳,扛起了东侧壁画上的
班班诸神。
问答
谁把天空打扫得如此干净?谁用
海水晒盐,做出一块
信仰的玻璃?那一棵树上
挂着谁的战靴,像把全天下的失败
收归己有,秘不示人?
剧场空空如也,几只面具
一件红色的斗篷,
不像恋爱,而是谋杀,谁卸下了
主角的身份?
刚才还有人清空了嗓子,但乌云的
台词,闪电的罢工
险些来袭。谁在护城河的对岸
驱散了背信的暴雨?
早上,大象还骑着光芒,拖儿带女
此刻非洲的头顶,
谁发现了闪逝的彗星?谁在跺脚,
肩胛一震,令佛陀醒来,
看见了下界里的秋季?
——每一次仰望时,我都会流下
泪水,用它滚烫的体温,开始抄经。
飞越天山
白色的黑板,大雪沉积
埋伏着去年冬天的
一桩心事,
一座牧场空了,而另一座帐篷
也连根拔起,
罡风和蹄铁,像耻辱的
败军,踢开山峦,
走入信仰的森林;——飞越天山
一些沟壑,一些冰挂
悲喜交集,
仿佛鲁莽的狮群、鹰部落、豹骨与爱情
冲冠一怒,端坐课庭。
我知道自己心里,有一根粉笔,
要去点灯
取火,续写后记;——飞越天山
这一本亚洲思想的书脊,
如此庄严,多么修远,
而诗歌仅仅是一步悔棋
难以复盘。
读史
它停在了
那里;
停在三天之外,
与辙印、冻鸟、干草,
和蒙头盖脸的
冬日一起,
停在了我的念想
之下。
我还认得它,没变,
姓氏依旧;——它在二十四史中
就是一场雪,白发猎猎。
只是,合上书本的一刻,
滚滚而逝的落日
犹如雪崩,让傍晚走出了
苏武和羊群,
顺治与最后的一句
偈语。
敦煌报告
菩萨病了!
来自敦煌的消息滚鞍下马,惊喊——
壁画起泡,
酥碱突出,
石窟内的班班神仙,如今
面黄肌瘦,
纷纷停下了抄写和诵念,
等待援手。
菩萨病了。
只是,在这个飞沙走石的世上,
冬天日深,
乌鸦的翅膀带着寒凉,也难以
飞渡冰河之外的边疆。
春天时,我看见研究员刘恩科
拿起一支美国的
针剂,扎进了
菩萨的臀部。
谢天谢地。
雪中私语
雪多得要用47天,才能下完——
才能用八百辆牛车,六万支木锨,
一整个江布拉克草原上的
大声吆喝
才能慢慢下完。雪多得
要用一个天空,
从东到西的一场白毛风,一间
诚实的羊圈
一座婉转的北天山才能下完。
真的!雪多得要用
闪烁的鹰群
狮子、大象、狐狼和密林深处的
兄弟姐妹们
跺脚,呼喊,哀告,才能款款下完。
雪多得第一天下,和第47天下
没有两样。
——下雪时,我在寺院里校经
第一页跟最后一页
竟毫无差错。
梅花消息
梅花到来时,我在树下
焚香澡雪研墨
誊抄佛经,
顺手泼掉了碗里的残茶。
湖在不远,
那些壮烈的涟漪,犹如书卷
次第绽放,
析出天地间幽深的机密
与流沙坠简的
浩淼心绪。
暗香迤逦,帘后
一只孔雀苏醒,
如同旧年的家书,模糊不清。
惟有梅花成泥,吟哦:
“……田园将芜,
一切就此不同。”
誓言
桦林里,一个过去的老公主
在打水
我要把她领回家,改口称呼阿妈!
羚羊犄角上,挂着一副
窝阔台的旧箭囊
我去把它埋在坡顶!
晒烫经书时,一些字母和意思溜了
蜂拥下山
我不喊不是人!
春天有点乱,而秋天
第一个将羔羊抱上了祭坛
我的眼泪一定会哭成血!
不久之后,将有一群悲伤的大雁
来这里换衣
告别时,我的膝盖向天空下跪!
像一生那么久,和天真的老虎一道
守住天山——我的圣徒
我的教义!
经历
我背着一筐子土豆
去集镇;
一筐子土豆,像
败落的公子和王孙
叽叽喳喳
吵聋了我的心脏。
喝水时
我会吃一点盐;
见了喜鹊
我要故意避让。
路遇一位埃及来的理发师
披挂刀光,究问不休——
可是,沙漠中
没有什么缠头的法老;
塔克拉玛干的尽头,的确也没有
一座金字塔的村庄。
哦,我像秋天一样疲惫。
我像一筐子丧失了故乡的土豆那样,不知如何
作答。
草原之夜
可是,那些记忆。
谁在帐篷里游戏,一幕酒,
一场民谣
和无妄的偶遇;
你手中有一把羊拐骨,红是进攻
黑则一败涂地
剩下的白色,代表了
无功而返的爱情。
猜羊拐骨的正反:一个人的立场,和阅读
一截意志
以及一次猝然的澄明。
在斑驳的草原上
秋风吹入,万物枯黄——我捎上
一册度亡的经书,一番心旌
决定遁匿!
天山江布拉克一带
时值盛夏
这一面山坡生机皆无:
月球的表面,戽干的
池塘,史前洞穴
凋敝的牧场
将一张劫后的残破脸孔,搁在了
歌剧院式的旷野。
据说,这里有过麂子、麋鹿、狐狼
七肘长的金雕、三步宽的鼠兔
以及无边无涯的羊肉花;
信不信由你,还有过
吹着长笛的大象、杂技鸽子
敲锣打鼓的虎群
夜半宴饮
却在黎明的山崖上醉卧的恐龙岩画
甚至雪原上,一闪即逝的
蓝色鲸鱼;信不信由你
其实这里只盛产爱情,
午后,当明眸皓齿的姑娘走过时
一只羊便掏出肠子
绷上琴颈,大声漫唱起
青春和火辣辣的肉体。
据说,一场诡谲的大火刚刚熄灭
一次爱慕,刚踮起了
他们的脚尖。——信不信由你
路过江布拉克
我兜里的一盒火柴突然哭了
磷火的泪滴,像噙着一口热血
满含灰烬。
我不知这些幼小的野花姓甚名谁
就像我奔走天山,一次次
失败于辽阔的美——
白色的、指甲皮大小的、三瓣羊脂玉似的
这些无名的野花
一定是日光的雪崩、枞树王子、佛窟灯火
以及七世纪末期散失的经卷
不小心掉下的。这个午后
当它们无穷无尽地绽放,声情并茂地
坐在这个宽大明亮的人世上,那一刻
我看见,门在天空打开
并嗅见了上帝身上的一阵羊腥
喷涌而来。
羊肉花:此刻,我忐忑且诚实地命名。
将一件衣服,晾在人间
还不忘
在它的口袋里,搁上
一盒火柴。
羊肉花
你的样子
但火柴太暗,有时候
会不小心
把灯点亮;
那么,换成一支蜡烛
让它像心脏一样
搏动?
不,蜡烛太脏
光晕中
才会积攒太多的尘垢;
要么,搬一块肥皂
和它坚硬广阔的泡沫,像一个人
被狂飙洗礼,
徒留下一个虔敬的外表
别在天上?
不!其实留下一首诗最好,让风
一行行吹干。
可是,从左边
一直摸到了右边,我竟没有
找见原来的那个
口袋。
用一滴正大光明的墨水
用一滴正大光明的墨水,慢慢
褪尽黑夜
和鸦群;
在复写纸的谎言中
找见一枚地址、号码和邮编,以及
几个迟到的人,
告知繁星、晨风与怒河春醒的消息——
大雪歇停,
马车深陷;
理所当然,天空保管着
一部泥泞而广阔的
圣经。
这时,用一滴白发苍苍的墨水,
添油
剔灯。
祷辞
心在高处,恰如
一截沸腾的青春正值中途。
心在高处
一股电流,插在天空。
心在高处,一个人
没有理由犯下春天的错误。
心在高处
比如一座寺院,为黄金遮覆。
心在高处,有一本经书
被日光催问。
心在高处
十万青铜之马,在针尖上起舞。
心在高处,将悲痛的北方
和爱情一起砌入。
心在高处
易水之畔,刺客与英雄同驻。
阅读
将一个词
逼露
真相。
将一些繁复的笔画和偏旁
带着汁液
颂唱。
将云层拨开,看见
钻石
与煤炭的天庭——
那么久了,有关生活的段落
尚未
整理完毕。
乌鸦的夜晚,一位神祗
失落翅膀。
在后园,秘密的结社中
明朝的书生
蘸下
墨汁和心情。
当辞典里跑出了一匹羸弱的马
矗立平仄
之顶——
一准是世上的某架天平
取出了砝码
的灰烬。
翻过此页,看见手中的黄金。
翻过这一页,一定要迎头碰上这个时代
灿烂的
好儿女。
暴风雨之夜
我知道这个秘密。我知道一道闪电,如何
砍下霹雳。
有一本受伤的书,正在遗漏
但云朵的词典
走下坡顶。暗若青铜的夜晚
一只内心的风筝
马不停蹄——
大地如佛,雷霆的车辇上
惟有神圣的败北
一字不语。
是的,我知道这个美妙的瞬间,知道
菩萨
和上帝的脸。
一场春天的淋漓之雨,多么
踉跄且灿烂——
像艺术,宣喻了她的法则。
像共产主义,猝然来临。
——像微笑报答了爱情。
——像百合碰见了黄金。
姐妹
青草不爱你
羊群一定会爱上你。
春天不爱你
夏天一定要爱上你。
坡上不爱你
山下的英雄会爱上你。
老鹰不爱你
天上的太阳要爱上你。
不是央金
一定是你妹妹卓玛。
鞭子不爱你
骏马一定会爱上你。
昨天不爱你
今夜一定要爱上你。
喇嘛不爱你
念想一定会爱上你。
经书不爱你
下一世一定要爱上你。
不是卓玛
一定就是你姐姐央金。
另一枝花不在这里
另一枝花不在这里,人世鼎沸
草长莺飞,
它溜出了花园,撇下
整个春天,
束身,正冠,扪心
带着秘密的意志,划清界限
已经不在这里。
另一枝花不在这里,
供养的灯,夤夜而飞
不会于暗夜中熄尽,
有人打开了经书,但更多的人
抟土,烧砖,筑梁
在甘南的雨天,它用一双靴子
跑遍了半个夏季。
另一枝花不在这里,譬如
酥油脱离了水,
爱没有杂质,一个啼哭的女婴
找见了佛陀的奶瓶,
它一定不在这里,即使秋天溃败
半途而废,嗓子里也含着
一股庄严的惊悸。
例外
在一层铁锈里,黑夜怂恿
星光湍急;
在砖石与柱梁间,蚁穴
奠基,并使窗棂斑剥,
七年前的油漆,
驱散了夏日的仙鹤;
点一根火柴,
把水照亮,看见秋叶翻飞
新羽初生;
在一本过去的辞典内,一枚蜘蛛
用了闪光的唾液,
将字词粘合。
抱歉,我说的是时间——
此刻,墨水中
大雪纷飞,弦索激烈;
而我的车轮,
抱着北方,
亦不能例外。
一阵花香,是一堵高墙
将我拦在半途,
索要度牒,
并敕令我肃穆;
描述:一阵花香
被春天释放的,这一阵澎湃花香,
蔑视自由,
扔出九条绳索,将我五花大绑,
押往春天的道场;
我趔趄,鼻青脸肿,
依次和丁香、槐树、碧桃与海棠
走过焰火的广场,
先是窒息,而后戴上了
天空的氧气罩;
这一阵街角的花香,来历不明,
教堂里没有,
经书上也无,
像一种马不停蹄的忧伤,丢下我
站在空空如也的街上;
只因这一阵花香,菩萨垂泪,
一只忐忑的木鱼
看见一群红领巾,以及
满脸雀斑的孕妇们,
藏起了
腋下的翅膀。
一首诗早已慷慨赴死
你在洗墨,在褪尽
乌鸦的本色;
但你不知,它刚刚飞离了寺院,
将一本经书
砌在了天空的佛龛。
你在劈柴,
这深刻的冬季,有人咳嗽,
有人澡雪;
马背上停着一炉香火,供养
其实并不需要斧头来帮腔。
你在运笔,点染日光,
油漆黄金,
一个时代的败家子,带着期货和股市,
寻找那一架
高潮迭起的天梯。
你在喷洒香水,为百合,
以及静水;
这夜半的朗诵如此湍急,
一定有秘密的意志,
可在你心中,一首诗早已慷慨赴死。
刚才
鸽子走过的路上,佛刚刚告辞。
剩下一些脚印
开满莲花,
尤其在十二月的早上,新娘
披上了袈裟。
如果遇见了大红公鸡,回避、礼让,
还请三缄其口,
因为天光初现的那一刻,
有一群原始的鲸鱼路过此地,不免引起
面包紧俏,
物价飞涨。
——是的,鸽子也不愿意说出,
除了这首诗。
星空下
我知道十指连心。
——要不,那些黑洞,在宇宙的傍晚
多么消极。
我从河堤上走过的时候,
一辆自行车,开口向我
借一双翅膀;
在冬季,另有一个梦纵马而来,
带着恳切
与热烈的忧伤。
十指连心,这地球上的黄河,
正在撕裂,
一阕山河的合唱,率先埋下了
伏笔。
在这集体主义的星空下,一些真相
开始狰狞;
惟有一池枯萎的荷塘,敛下了
旷世的私语。
对峙
一句发音溜进了词典,
与页码对峙;
一介惊慌失措的偏旁,点灯进入
寻找一生的部首,
与思想对峙;这个冬天
落木萧萧,
与零度抗衡,和西伯利亚对峙;
空虚的鸟巢
带着羽毛的热泪,站在树上,
与内心对峙;
一封迟到的信,一挂马车,
如果南辕
能看见灿烂的北辙,
像闪烁的七星,那么就允许
信念和天空对峙;
门响了,一匹大象来做客,
可家徒四壁,
仿佛整个非洲与国际粮农组织对峙;
在徕卡的镜头中,一只秃鹫
耸起肩胛,
与饿孩子对峙;
12月的傍晚,一份精心的合同,
虚构情节,
鼓吹历史,
与黯淡的支出和消费对峙;
是的,这大器晚成的醒悟,
步履仓惶,
像一碗滚烫的开水,
与冰河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