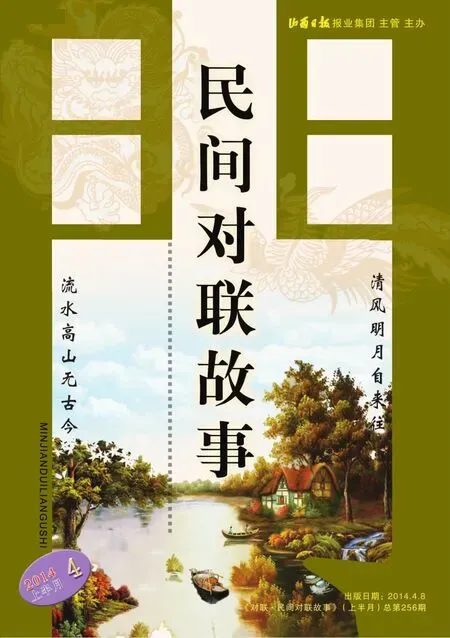对联创作为何要『贴着地面飞行』
——对联的现实语境暨严海燕现象写作研讨会发言纪要
(本刊记者傅海青整理)
编者按:去年五月,本刊刊登了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严海燕先生《我为什么要在楹联界提出“现象写作”的概念》一文,在联界引起强烈反响。
今年3月8日,西安财经学院举办“对联的现实语境暨严海燕现象写作”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对联理论研究者、作者、学者等30余人,聚集于长安古城,从不同角度畅谈自己的观点。本刊择其精要刊出,以飨读者。
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刘太品:
现象写作是一种信仰的引领
严海燕先生关于“现象写作”的主张,是站在严肃文学的角度,对当代对联创作进行的一种思考和实践,应该说,起码对联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但是,自从观点提出,就引发不少争议,也出现不少误解。其中一种观点,是认为现象写作只是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实际上,“现象写作”只是倡导面对客观现实的细节来写作,并不特指光明面还是阴暗面。就如歌中所唱:“为什么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这种以敏锐的感知,捕捉因社会转型而发生的失衡,因社会巨变而产生的失调,是直接指向世界的本身,指向我们的心灵深处。这种微妙和犀利,无法简单地用光明或者黑暗来概括。
对联文体,是由文学性、实用性和谐巧性这“三位一体”的方式构成。要追求实用,自然难以回避那些廉价的颂扬文字;要增强趣味性、追求谐巧,也难免会伴生内容空洞的文字游戏。这种既是优势,同时又容易滑向低俗的文体构成特点,加上在市场环境下,文学极易成为权势和金钱附庸的现实,使得我们很难纯粹从文学性上去把握对联的创作方向,形成既具有文学性,又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心灵的写作方式。
那么,在时代环境和对联文体特性的双重制约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力挺严海燕关于“现象写作”的创作理念呢?换句话说,“现象写作”有什么现实的积极意义呢?
在这里,我想用“信仰与心灵”的关系来做个类比: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信仰”似乎最不“实用”,因为它带不来任何“实惠”。但是,信仰对于我们的心灵却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对联是由文学性、实用性和谐巧性构成一样,我们的心灵,其实是由神性、人性、兽性这三部分组成。对联无法排除实用性和谐巧性而拔高为纯粹的文学性,我们的心灵也无法超越兽性和人性而完全上升到神性。所以,我们就需要信仰,因为只有信仰才是引导我们向上的力量,使我们永远趋向于神性。在对联创作方面,我们同样需要这种向上的引领,而严海燕先生“现象写作”的主张,事实上就起到了这样一种引领的作用。
对联理论界二十多年来,一直纠结于平平仄仄的低层次争论,亟需创作手法和主题内容方面的创新。我愿意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支持严先生的探索,让更多的作者理解这一观点,实践这一理念,以提升当代对联创作的境界和水平。
张志春教授(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大教授)点评:
刘太品先生从创作手法和主题内容层面,对于联界的创作弊端和理论误区,进行了具有穿透力的剖析,并对严海燕的联语主张予以肯定并支持。但是,联语构成是否能概括为文学性、实用性和谐巧性三要素,且这三要素能否与人的神性、人性和兽性相对应,提倡纯文学性是否就是对联语的拔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斟酌与讨论。
西安市楹联学会名誉会长解维汉:
“现象写作”是文人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的自觉浸染
一、“现象写作”的担当意识
严海燕倡导的“现象写作”,初衷是从转型期的生活现象出发,写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发现、思索和感慨。它无关乎个人利益的变现,也不受人际因素掣肘,着力跟踪和记录转型时期普通人的生存、各种文化的处境以及诗意化变迁。
这种“现象写作”的提出和初步实施,无疑反映了严海燕置身文学前沿阵地的高度敏感,对转型期对联写作的高度关注和深沉思考,尤其对社会和民生的全面聚焦,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责无旁贷的担当意识。我对严海燕的忧患意识和求索精神由衷叫好。
易生先生将严海燕的“现象写作”归纳为三点:一是自主性写作;二是现实性写作;三是本色性写作。我认为阐述得很精确也很全面。
纵观中国古代诗歌史,其实这种“现象写作”早已有之。杜甫的“三吏三别”和《北征》《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三首》等,都详尽而真实地通过亲历所见所闻,记录了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群众的深重灾难,因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等诗歌,也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沉重的赋税、宫室的盘剥、豪强的欺压对底层百姓的凌辱和掠夺。“一束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成为千古名句。诗人借助“田舍翁”的一声“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深刻社会矛盾和强烈对比的贫富差距。钟云舫在崇丽阁长联中呼唤的“且向危楼俯首,看、看、看,哪一块云是我的天。”集中倾吐了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家愁国难,抨击时政积弊,口诛笔伐污吏贪官,其犀利的笔锋,最后指向整个反动统治集团和维系其统治的思想体系和根本制度,闪烁着鲜明的民主性、战斗性光辉。继承前辈诗人联家深邃的洞穿力和犀利的战斗精神,是后辈学人的责任。目前,我们虽然身处改革开放的盛世,但同时也面对着诸多的时代积弊和社会矛盾,而回避矛盾的风花雪月之作太多、直面现实矛盾的作品太少,可能是严海燕振臂高呼的特定背景。
二、征联写作的功过研判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对联文化也迎来“盛世兴文”的鼎盛时期。与社会对文化的需求相适应,当代征联活动也此伏彼起、声势浩大、空前活跃。许多联人,已几乎将应征创作视为个人创作活动的全部。而因征联活动有时间、题材、体裁限制,又有奖金、奖品激励,带有明显的功利特征,严海燕将这种非自主性写作形态,称之为“遵命文学”和“材料作文”。
其实,在我国古代,也有应制诗和台阁体,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等,都写过应制诗,毕竟诗人不是在真空中生活,或朝堂奉命,或同僚唱和,都是促使他们写作应制诗的现实缘由。况且,应制创作也并非不能出精品,《阿房宫赋》、《滕王阁序》等,实际上都是应制而作,其中也不乏阿谀之词,但也彪炳千秋,流芳百世。
所以,应制创作与现象写作,在文学的本质上并不矛盾。文学脱离现实,一味风花雪月或愤世嫉俗,反而会显得空洞无物。当代征联写作的繁荣,是因为有着广泛的现实需求。征联单位有用联需求,联人有着以对联艺术造福当代、服务社会的使命,因而,提倡“现象写作”不可否定和贬低征联写作,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征联写作。需要警戒和避免的,是受功利所驱动,一味投其所好,刻意夸张,美誉迭加,极尽称颂,为征联主体评功摆好的肤浅应征作品。而在一些名胜景点和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的征联活动中,对于那些既具思想性,艺术性又较高,并充满爱国情怀、中华美德的作品,则应充分褒扬。
三、忧患意识的自觉浸染
读一些“现象写作”例句,感到文学性不是很强,有的还存在标语口号化倾向。一直以来,我都坚持一个观点:对联不是万金油。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自有其长处,也有其短板,扬长避短应是题中应有之义。相对来说,山川胜迹联、祠堂寺庙联、缅怀哀挽联、格言联、行业联以及春联等类别可以更好地发挥对联的长项,蕴育丰厚的内涵,彰显华美的文采。而一些抨击声讨性联作,相对就逊色一些,记得多少年前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楹联报上刊登整版的声讨对联,虽然义愤填膺,刀锋笔剑,但艺术性就欠缺许多。
由此我想,“现象写作”也不必刻意自成一类,有意去捕捉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社会表象进行写作。只有胸怀忧患意识,将大爱与责任渗透在一切对联创作之中,并变为一种常态化的自觉行为,才会保持恒久的艺术生命力。《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是由人内心的感发所产生的。一千多年前,陷于乱世,没有人给杜甫出题目,下任务,杜甫完全是一种自觉意识,写出不朽“诗史”。今天,我们仍然崇敬这种自觉的忧患意识。
张志春点评:
植物的茂盛,在于高低稀稠不同群落的汇聚与竞争;人文事业的繁荣,在于多元化观念的对谈与撞击。解维汉先生的发言,既肯定了提倡“现象写作”的优点,又从创作实际指出它的局限。这说明一种创作主张的提出,它期待的呵护与滋养,不是简单地捧杀与棒杀,而是疑义相与析——既要从学理上梳理以溯源分流,也需要与创作实际对接来检验与证伪。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益与完善,凝结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观点。
著名联家徐熙彦:
诗学精神之“兴观群怨”在对联现实语境中的缺失
文学性不只是对文学意趣的孤芳自赏,而应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关照。所以当下的楹联界,缺失的不仅是文学性,更缺失诗学精神。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是这样,作为“诗中之诗”的楹联也应当是这样。反思“兴观群怨”的诗学精神在楹联界的体现,我们很容易产生和严海燕教授共同的忧虑。我想,严海燕教授提出的在对联现实语境中的文学性表现,就是“兴观群怨”的诗学精神在对联创作中的体现。分开来看,“兴”和“群”相对体现得比较好,这两类对联的数量都很大,且不乏精品。“观”则体现得不够充分,只有对自然的“观”,而缺失“对”社会的“观”,这里的“观”不仅有心灵的观察,还有笔墨的关照。“怨”则很少得到体现, 类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样讽刺现实,传达民声的联语,更是严重缺失。很多在全国征联活动中频频问鼎折桂的好手很少有这一类作品,我自己也一样。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自觉不自觉地减少了参加全国征联比赛的次数,改而关注身边的事,关注家乡的变化和民生的热点话题,尝试用对联的形式反映民生民情。这是对严海燕教授“现象写作”的一种回应,也是对自己对联视野的拓展。借此机会,抛砖引玉,请大家多提意见,也希望更多的楹联作者,参与到“现象写作”的实践中来。
张志春点评:
作为一个国内有影响的青年联作家,徐熙彦将“现象写作”的内核提炼为“诗学精神”予以肯定,并将其与孔子主张的“兴观群怨”审美功能揉合起来。这当然是从纯文学的层面来展示的。而且,他还以创作上的实践表示对这一主张的呼应和支持。这是难得的。我觉得,如果要举出评判创作与理论的一个简单标准,那就是看你的创作能否击中读者心灵柔软之处,就是看你的理论能否为作家所折服,并心甘情愿接受你理论的指导。徐熙彦实实在在的话语,让我们对“现象写作”的主张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有了更多的期待。
原《长安联苑》主编李文西:
高层次对联,应以人文关怀为己任
就目前情况而言,各种征联热闹非凡,但对联文体的品格与作家的风格则不显。对联文体的品格,其个性特征就是亲近社会,亲近百姓。作家的风格就是要把自己写进去,要从身边发生的事情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我从生活现象与对联使命的角度,谈两点对“现象写作”的认识。
其一、风格多样化
二十年前,严海燕曾提出关于对联创作风格多样化的理由:“对于个人来说,他当然有权利长期乃至终身吟风弄月或者歌舞升平,但是对于一个有着讽刺幽默文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在社会问题迭起丛生的时候,依然让一种文体呈现出清一色的明亮,而少有‘我为人民鼓与呼’的作者,这无论如何都是叫人费解的。”
然而“风格多样化”这句话,说起来不易,做起来更难。对联不仅讲究文字凝练,而且与旧体诗词比起来,还多了实用性、游戏性。春联、婚联,按照民俗习惯是不可说败兴话的。劳累了一天的联友,晚上上网玩联时也大都喜欢风花雪月。至于征联参赛就更不用说了,人家出钱“买”联,你不投其所好而是多发忤逆之言,会有好果子吃吗?
但这样一来,那些不一定美丽但却一定真实的生活以及人们对它的真实感受,要想在当代对联格局里找到自己的栖身之所,就不大不容易了。二十年后,严海燕特意为这些不受待见的对联开辟了一个园地——“现象写作”专栏。无论你莺歌燕舞或者感叹忧愁,只要你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贴着地面飞行”,皆有希望入列其中。
其二、写什么
“现象写作”,一写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及个人际遇,二写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变迁。前一个是平民视角,后一个是文人视角。她不逃避现实,而是与时俱进,真正践行古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她只顾平实写来,不单纯倚重“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也不刻意追求“华丽、喜庆、浩大、诗意”的美学效果。
严海燕说,他曾看到一副《题找工作》的对联:“瞰四海千帆竞过,俯九原万马齐喑,应怜北战南征,偶曾梦话说三顾;相逢皆蹄虎之驴,所学尽屠龙之术,堪笑寒来暑往,无可奈何又一年”,并颇为欣赏,只是感到同类对联似不多见。
事实正是这样。当下更多的对联作者“热衷于对预设主题的集体表现”,“而放松了对身边变化的境况的个人关照”(严海燕语)。君不见国人正为米面油以及“菜篮子”是否安全而提心吊胆,而有些人却“不失时机”地引进“苏丹红”、“瘦肉精”等“高科技”;君不见风沙已大规模入侵长城内外,工业排废使中国无污染河流所剩无几,而某些官员却继续祭起“土地财政”的法宝不放;君不见上海290种原生植物或已消失,而不无争议的转基因大豆、玉米正涌向东北和广西;君不见中国贫富分化严重,原本属于革命时代的“土豪”一词重新进入流行词语之列,而社会底层人物却经常遭遇“被幸福”、“被平均”……对此,不少对联作者似乎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仍整天穿梭于各类征联之间,你有奇思妙构,我有华词丽句,赞美不担风险,附和只有好处,争奇斗艳,乐此不疲。难怪有人借来两句“格言”来进行调侃:“情,是用来维系社会的;才,是用来粉饰社会的”。
“文学是人学”,凡认同高层次对联属于文学的对联作者,都应以人文关怀为己任。建议优秀的对联作者,在进行其他品种的对联创作之余,不妨将自己的才华与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尝试着写出别样的对联来。也许,这是严海燕提出“现象写作”的初衷之一吧?
张志春点评:
李文西先生极其精警地强调联语的民本立场,强调联家的独立精神。或许我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会感到这一强调如同主旋律一般不断显现,但它是一种让有扭曲倾向的文化艺术活动走向正道的努力,仍然让我们浮想联翩,仍然透地气,仍然为现实所期待,这就值得我们反思,值得我们琢磨。
长安诗钟社名誉社长李文平:
“现象写作”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需要
“现象写作”,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把自己所观察所剖析的社会万象、社会乱象、社会怪象,以文人的良心,文人的忧乐情怀,文人的傲骨和秉性,把它构思成文学作品。旨在拨乱反正,除恶扬善,传递正能量。
“现象写作”,在先贤们的小说、诗、赋、词、曲、楹联中已有不少传世佳作,就是在最年轻的格律文体——诗钟作品中也屡有发现。如,鼎革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者、著名教育家严修(1860—1929),曾以《乐·新(七唱)》为题拈钟一首:“鱼跃正因添水乐;牛栖安识发硎新”。此钟上下句虽然都是白描,“跃”与“栖”动静形成对比,而“乐”含喜,“新”却藏悲。上句从“海阔凭鱼跃”名句化来。对鱼而言,自然是水越多越好,句意看是在添水,更是在为鱼添“乐”,当然是喜事了。下句的“新”字里却深藏着悲恨,因为着硎磨刀,以发新刃,牛就要挨宰了,悲恨愤然而生。字里行间暗示着某些社会现象,给读者留下了广袤的联想空间,发人深思,耐人寻味。又如,现代词学家、书法家、诗钟大师张伯驹(1897—1982),有《庸医·占卜(分咏)》诗钟一首:“新鬼烦冤旧鬼哭;他生未卜此生休。”庸医自古有之,于今为甚更为恶,假以伪科学坑人、害人、杀人。上句自杜甫《兵车行》中“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诗句集来。下句咏占卜,集自李商隐《马嵬坡》之一“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诗句。句意揭示他生难以预测,而今生先已休矣,直指占卜的虚无和迷信;同时,也是对在街头墙角那些搞占卜、弄神鬼、坑人、骗人、敛财者自身的一个辛辣讽刺。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水平突飞猛进,物欲在急剧地膨胀,人们的传统观念遭到挑战,文明道德的底线屡被冲破。所以,而今的社会现象则更为复杂纷繁,严重影响着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生活、生态和生存。我非常认同严海燕先生所说的:“我们深感自己有责任,同时也有权利放弃一切先入为主的东西,亲自跟踪和记录转型时期普通人的生存、各种文化的处境以及诗意的变迁。”也正如严海燕先生所提出的“现象写作”是“一种诉诸概念的提醒,一种‘贴着地面飞行’的写作方式。”当然,也是当代文人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时代在发展,语境在变化,文化艺术(包括诗、赋、词、曲、联、诗钟等等)也应当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敲着时代的鼓点阔步前进。严海燕先生关于“现象写作”的提出,为我们在新时代新的语境中,如何提高创作水平,如何反映揭示社会现状,贴近社会现实,开辟了一个探索和创作的方向。
张志春点评:
感谢李文平先生对“现象写作”定义式的表达,以及对诗钟的介绍。那些看似文字游戏的诗钟文体,实则是把作家观察且剖析的社会万象写成特殊样式的文艺作品。这确乎是贴地面飞行的诗意创造,是穿透人生的生命体验。而这里的举例则是从更深的时间长度中为“现象写作”搜集来了令人心服口服的创作依据。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安市作协副主席杨乐生:
中国缺乏影响世界的作家群,是因为不敢面对现实
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曲曲折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也正因此,中国不容易出现影响世界的作家群,因为我们不敢面对现实。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说,严海燕“现象写作”的提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来讲新意不多,因为我们现当代文学界一直在强调现实主义文学,也就是说它没有超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大框架,但对于对联界来讲“现象写作”极富意义。
对联界应该走进现实,走向现代,对联作品要有内容,对联作者要有创新。
就我个人看到的日常对联而言,模式化比较严重,陈词滥调较多,动不动“耕读传家”、“国泰民安”。你大字不识几个,也敢写“耕读传家”!
具体到征联,你当然可以征,问题是如何征。要防止伪文化,警惕脆弱的虚荣心。应该体现个性,发掘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对联属于大雅,我不同意称它为民间文艺的东西。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好对联都是大文人创作的。
张志春点评:
人常说西北大学是陕西的北大,乐生教授那种个性张扬的风采很有魏晋风度。他的话语没有拘束,海阔天空,坦率直爽,他有时甚至为了忠于自己的感受而不惜一任话语走向极端。但我们从他“‘现象写作’的提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来讲新意不多”,“但对于联界来讲‘现象写作’极富意义”的判断中,可以感受到清醒而视野宏阔的表达,感受到自在随意地宣泄中有着学术的严谨,有着悠远的意味。
西安财经学院教授、著名小说家马玉琛:
征联未必征不到好作品
我认为,征联未必征不到好作品。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带有“命题作文”的性质。关键问题在作者身上,作者要有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有了足够的营养,就有一定的高度。从清代纪晓岚的对联可知,对联讲担当,也讲情趣,不能总是讲担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语境不同,要根据现代汉语的特点,发掘它的现场感。
张志春点评:
马玉琛教授语浅意深,给我们启迪良多。他从创作层面道出了当代联家一个普遍的困惑,即生活在白话语境之中,却要创造的一个源于古汉语语音、词汇和句式的文体。这就是一种疏离。近现代以来国家种种内忧外患,文学艺术多讲担当而忽略情趣,又是一种疏离。现代人如何进入联语写作现场?如何像古人那样将学养融渗入生命体验之中?如何将眼前所遇、耳边所闻、心中所想、身所经历化为联作?这大概是当代联界所有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面对的问题。
长安诗钟社社长王小凤女士:
“现象写作”对诗钟创作也非常必要
今天大家讨论严海燕老师提出的“现象写作”这一话题,其实不光是对联界,对我们长安诗钟社来说,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在我们诗钟社的创作活动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提倡多写风花雪月,少碰敏感问题,怕惹政治麻烦。仔细想想,为什么古人的那些名篇能够历千年而魅力不减,而我们现在创作出来的一些东西有时遭人嘲笑,应该说,这与我们的创作一定程度脱离现实生活有关。
张志春点评:
感谢王小凤女士的介绍,让我知道了长安还有一个诗钟社,而且展开活动有十年之久了。她谈到自己创作时的胆怯和严海燕谈理论创新时的犹豫,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过去年代极左意识迫害文化艺术创造所带来的阴影。而这种阴影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边缘化,但却未能完全消失,这也是联语创作需要面对的语境之一。其实我们都知道,联语是千古事业,若无胆识,怎么能千古呢?
著名联家王天性:
我们要在接地气的情况下把对联写好
对联作为国粹艺术,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习惯密不可分。因为对联具有实用性、装饰性特点,说好话于是也成为创作的惯例。婚联如斯,寿联如斯,春联、贺联等莫不如斯!一个人去世了,不管他生前人品、功过,挽联也都表现出少有的宽容。虽然不同流俗者历代大有人在,其经典作品至今仍在流传,但我们依旧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有一种文体不顾真相而偏好评功摆好!这种状况让人尴尬,却很难脱俗。
楹联想要最终成为一种文学文体进入文学史,写作非实用性对联,不受传统对联爱说好听话的影响,全方位地描写看到、听到、想到的一切,淡化粉饰,强化写实,并力争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许是真正成为文学的必由之路。
作联要用真事,说真话,少写假话、空话、套话、大话!尽可能写得短一点。通俗不是流俗,文雅也不是让人看不懂。钟馗就是钟馗,西施就是西施。西施很美,钟馗顶多是另一种美,事实摆出来优劣自现,不要乱贴标签。评价人和事也要慎重、中肯,切莫让功利心主宰了判断,说其坏便是一无是处,要说好时连耳朵都给涂上雪花膏。
以社会现象、生活现象入联,无疑拓宽了对联的取材空间。“现象写作”关注现实一点不假,但也不是放弃浪漫主义,因为真正的浪漫主义是在间接地反映着现实。
其他文体能描写社会变迁,抒写人生的喜怒哀乐,对联当然也能!只要我们把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文艺创作的素材就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社会生活千形万象,反映到文艺作品中来自然应是丰富多彩。讴歌光明和批判丑恶,都能产生高质量的文艺作品。这就像有两堆土,先装在两只筐中是两堆土,后装进两只桶内,还是两堆土,只有将土放到窑里,放进南方的景德镇窑或者北方的耀州窑,才能烧出好瓷器来。杜鹃开在高山上,玫瑰还带着刺儿,由于花好备受人们喜爱;水田里的杂草和旱天里的杂草固不相同,但因干扰作物生长而同样令人厌恶!赞颂美是在肯定美,抨击丑也是在肯定美!我们就是要在接地气的情况下把对联写好。
张志春点评:
众所周知,王天性先生是国内有影响的联家。他的创作有质有量有激情有张力。于是我们从他的感悟中听出了来自创作实践的丰沛底气,感受到一种随心所欲不逾距的自由境界。他是以创作者的共鸣来呼应“现象写作”这一理论主张的。联语创作在突破粉饰现状的文化之膜,而要直面现实,他从创作体验中,道出联语和其它文体一样能应于社会转型,能表达繁杂的外在与内在世界。这是当代联家的一种文体自觉与自信。
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教师田子爽博士:
“现象写作”不仅开辟了一个认识欣赏对联的新颖角度,也提供了一个写作对联的方法途径
当今社会多元化、多语境的文化氛围中,对联日渐流于形式,不仅被社会主流意识所漠视,更是被担负着文化传承重任的青年一代所忽视。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年轻人的责任和义务。在对联如此尴尬之境地,严海燕老师提出的“对联的现实语境”、“现象写作”,认为对联应贴近现实生活,对生活进行心灵观察与笔墨关照,从而更加丰富对联的功能。这样的理念让我们重新审视对联这个易被忽略的文体,不仅开辟了一个认识欣赏对联的新颖角度,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写作对联的方法途径,对我们年轻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志春点评:
这位80后学者对对联文体有着特别的感悟。她意识到传统联语因与生活深切地关联而成为富有特色的文化符号,而今天联语为主流意识和年轻一代所忽视,症结恰恰在于这一文体空壳化、形式化。而提倡现象写作说就是为其恢复生命活力的方法与途径。时下多以年龄长幼来评估论说的深与浅,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年轻人厚重的声音。难得。
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教师张颖博士:
创作理论要成为创作实践的“领跑者”
严海燕老师是九十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但多年来,他似乎远离现当代文学而一直在从事古典诗词和传统对联的写作和研究。今天,从他提倡的楹联“现象写作”理论中,我似乎又看到了现代文学所具有的的现实性品格和当下关怀的潜流和回响。
当下的文学艺术研究中,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处在一种尴尬的跟随创作、解释创作的陪跑状态。今天会议上诸多楹联创作者对严海燕“现象写作”这一理论的呼应和认可,说明创作理论对创作实践有着敏锐的发现和及时的引导,它不只是创作的陪跑者,还是“领跑者”,理论和批评正是在与创作实践的互相砥砺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希望有更多的理论研究和批评争鸣者共同参与,不断丰富“现象写作”的理论内涵。
张志春点评:
作为80后学者,张颖博士对现象写作主张的评估放在了当代文学艺术总体格局内,放在了理论创造与创作实践的互动关系之中。这是一种宽阔的眼界,一种有所思的表达。
西安楹联学会副会长支胜利:
文学要客观反映社会,而不能选择性失明
严海燕老师的“现象写作”是在2012年《长安联苑》先行推出,后在《对联》杂志等媒体正式发表的。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成绩显著,问题很多,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但我们的对联作品特别是征联作品,很多却是莺歌燕舞,应景特征明显。文学要反映社会,就应全面、客观,而不能搞选择性失明。要在创作上“百花齐放”,就应允许理论上百家争鸣。针对联界的浮夸和跟风现象,严海燕老师保持着自己的清醒,以羸弱的身躯承担起一个沉重的话题。“现象写作”拒绝刻意迎合他人,拒绝虚假浪漫主义,同时也不矫情,不专门写社会阴暗面,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主张。
张志春点评:
支胜利先生告诉我们,“现象写作”主张最初萌生于《长安联苑》这样一个地方性的内部刊物,然后走向全国。这也启示我们,任何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创新,最初都需要一种呵护与扶持的土壤。哪怕它不太起眼,但很重要。倘想起唐代的诗人都是成群出现而卓然成家的,诗才获得肯定的平台是官场考场情场等博大的空间,我们就会心事浩茫连广宇。有一群可以切磋琢磨的朋友,有一个可以发声刊文的平台,就是联语作品与理论滋长的重要语境。虽说这是一种看似格局不大的语境,其实往往是很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会不断放大而显豁起来。
张志春教授总结:
本次研讨,极为充分地体现了三个关键词:现实语境、文学性和现象写作。
先说现实语境。诸位从生活疏离、文体疏离或观念疏离等层面展开,作了多角度阐述。而严海燕谈理论创新时的露怯,王小凤诗钟社创作时的敏感,都是怕扣帽子怕惹政治麻烦,仍有浩劫时代的阴影。这当然也是让我们俯仰古今感喟万端的现实语境。
第二个问题,文学性。过去人们不承认,不敢提,以为联语不过是生活中的小点缀而已。梁启超曾集联一册也只说是“痛苦中的小玩艺”。我自己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古今作家名联选》后记中强调其文学性,呼吁联语写入文学史。其实当时我也不明白联语具有双重的文学性,或者叫做联语文学的两个维度。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这一点今天都认可。它以文本为精准标准,讲究抒情性、意象性、意趣性和表达精美的音乐性,追求使人沉浸其中的意境。但联语还有一种性质,是民间文学性。民间文学大于文学,它更像多媒体一样立体状态的多向度展示,不是传统文学那样单向度。它在绝对意义上可以说不是文学。因为在学科上,它在二级学科上属于民俗学,一级学科属于社会学。如果说传统文学意义上的联语讲究精英立场的意境,那么,民间文学意义的联语则讲究民间立场,讲究仪式,而且更神圣。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没有哪种文体,像联语一样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岁时年节、婚丧嫁娶的人生礼仪,乔迁、自家书房,公众校舍庙宇,亭台楼阁山水,无处不联,无时不联。有人据此以为联语作为一种文体先天性的不足,似乎太实用了。其实不然。它讲究仪式就自然有一种尊严与自由,而不是依附式的工具。我们知道,在生活情境中,书写什么字体,纸张什么颜色,张贴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都有特别的意味,特别的讲究。即使有的联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天南海北地反复呈现,如祝寿的“福如东海常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春联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商家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等,那也是岁岁年年联相似,年年岁岁意不同,从纯文学上看或许会有审美疲劳,但从仪式层面来看,仍有神圣须得敬畏的一面。你敢设想大年时节给人家门口贴非红色的联语纸张么,或者居丧之家门联贴出非白色的联纸!纯文学没有这个讲究,而民间文学却丝毫不能马虎。所以谈文学性至少应该从这两个维度谈起。
第三点是现象写作。这是严海燕提出极有意义的联语写作主张。它的起根发苗或许兆源于现象学“不要想,只是看”的响亮口号,但我看他主要是有感于多年来国内联语创作积弊的登高一呼。它敏锐地暗示出联语创作与当下语境某种意味的脱节与疏离。它要求联语表达眼中所见、耳边所听到的生活本真情境,而不是路径依赖般借助陈辞滥调地建构出一层厚厚的文化膜,甚至那明显可看出有瞒和骗的东西。倘若从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关系来看,这一联学主张的新颖度和力度便陡然可见。在国内更多的文学或艺术理论被动地跟随在创作脚后,或为解释,或为圆场,或为包装,或堕落为伪创造的吹鼓手的时候,严海燕这一主张的提出,得到了理论界的呼应,引发了思考与争论,也引发了国内不少联家的创作,如徐熙彦、王天性等人的创作呼应,都是难能可贵的。
在我看来,严海燕“现象写作”的主张是从纯文学意义上提出的。他当然是为了提升联语创作的整体境界而考虑的,但却未意识到联语另一重要品质。“现象写作”其实是一种深刻的偏颇。倡导者既然拒绝本质主义,既然是从往昔美好的意向(大雁、乌鸦、萤火虫等)和语汇入手而反观当下,则不妨从西方现象学的角度对其“现象写作”理念予以完善。在民间文学层面,仪式方面是有禁忌的,更有表达理想的趋向。如春节不说破茬话,平常说话低调的人,春联上也会将自己的理想合盘捧出。事实上从来也没有一个观点能够涵盖一种文体的全部,只要它能引起联界的关注,引发理论界的反思,创作界或多或少的呼应,那就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所以我要说这种理论主张即便偏颇,那也是深刻的偏颇。比起那些没有棱角、没有任何作用却永远正确的话语,它更重要,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