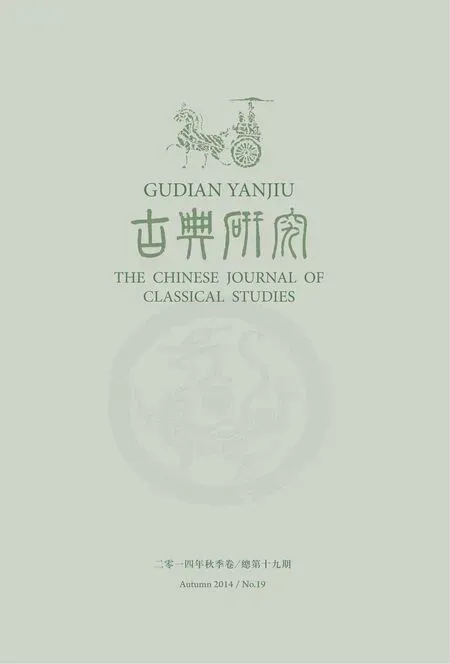一個非西方視域下的埃克哈特
——讀文森《無執之道》
龔 雋(中山大學哲學系)郑淑红 譯
一個非西方視域下的埃克哈特——讀文森《無執之道》
龔 雋(中山大學哲學系)郑淑红 譯
Meister Eckhar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onWest Reviewing Markus Vinzent s The Art of Detachment
Author:Gong Jun
is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Philosophy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Email:gongj@scnu.edu.cn[英]文森(Markus Vinzent)著,《無執之道》(The Art of Detachment,Leuven:Peeters,2011,406pp.),中译本由郑淑红译出,华夏出版社即出。
埃克哈特是西方神學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但他留下的精神遺產同樣可成爲非西方思想傳統中具有重要價值的參考文本。正如本書譯者所說,埃克哈特不僅代表了西方哲學的高度,而且向東方學者發出了邀請。實際上,這種邀請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經得到回應。作爲首位向西方系統推介東方禪學的日本著名禪學大師鈴木大拙,就在埃克哈特的神學中發現了大乘佛教、特別是禪的意趣,並試圖從中尋繹出極富創意性的對話。雖然鈴木對埃克哈特的論述正如他對禪的塑造那樣,具有相當程度的策略性,即他過分誇大了埃克哈特與禪思想中神秘主義與反智主義的傾向,但這一點必須放在那特定的歷史場景中才能獲得恰當的理解。
與東方聚焦於埃克哈特靈性學思想的立場不同,該書是以哲學和神學的論述爲主軸,力圖理智主義地再現埃克哈特的思想系統,呈現給我們的主要是作爲知識對象的埃克哈特。因此,對漢語世界的讀者來講,這本著作的翻譯出版,對我們重新和全面認識埃克哈特及其神學觀念無疑會起到相當積極的作用。閱讀過該書的人都有這樣的印象,即埃克哈特不僅是一位傳統意義上的靈修者,更是一位極具素養的神學大師兼哲學家。
我個人最初也是從鈴木的佛學論述中,意識到了埃克哈特乃至西方傳統中的神秘主義與東方思想之間可能存在的某種驚人的相似。於是,多年來自己也時常抽空去參閱一些西方神秘主義的作品。不過我對這些文獻的閱讀一開始就沒有考慮作系統和全面的學術論察,因而很少從知識史或哲學史的意味上作細密考究,更多地是想透過這些閱讀,經驗式地瞭解西方意義下的心靈修煉傳統,以爲那或許代表了哈多(Pierre Hadot)在其《作爲生命之道的哲學》(Philosophy as Way of Life: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中所說的、被西方哲學傳統所遺忘了的“作爲生命之道的哲學”。可想而知,我的這些閱讀終究不會結出研究性的果實。我發現一旦要落實到歷史與哲學的層面來作具體而微的比較與闡述,困難遠比想像得大。對我來講,閱讀的快樂遠勝於艱苦的比較研究。實際上,鈴木大拙所發現的那種埃克哈特與禪思想之間的“接近”,更多也是在經驗或體驗層面上的交會,學術史的論述並不完密。何況,我對於神學的歷史與思想,向來就缺少系統的學習與研究,因而對於比較宗教之論雖時有興致,卻從未敢作學術性的書寫。
這次有機會先睹這部《無執之道:埃克哈特神學思想研究》譯稿,不料竟然是一氣呵成地通讀完全書,並恍然發現這部有關西方神學史的論著,確實對於從事東方學研究的我發出了某種邀請,讓我很自然地再次聯想到東方佛學、特別是禪的傳統。於是,我重讀了鈴木大拙的相關論述,而這次也才比較切實地發現到鈴木所論尚有許多未發之覆,故不揣孤陋,簡拾一二,試著從一個非西方的視角,特別是禪的觀念來略陳己見,算是一點讀書的隨感。
一、在正統與異端之間
雖然本書強調了埃克哈特神學與哲學的特質,但在我看來,他神學思想重要的表現之一即在聖典的解經。有趣的是,埃克哈特的解經與西方傳統經院哲學的方式有所出入。可以說,他是神學家,而於經解卻有別子爲宗的傾向,這使他經常在解經中出離於神學注經的主流傳統,而自立權衡。其中最緊要的一點,是在解經中注入個體性的宗教經驗。這一點,鈴木的看法是對的,他發現即使是通教理的學者,若無埃克哈特那種豐富的宗教經驗,對於他所講也會力有未逮(參見鈴木大拙,《耶教與佛教的神秘教》,徐進夫譯,臺灣志文出版社,1986,頁10)。就是說,與一般經院哲學家不同,埃克哈特一面具有良好經典知識的修養,一面又相當重視解經過程中宗教經驗的價值。對他來講,內在的經驗遠比知識和傳統權威更具優先性,這也正是該書作者所說的,埃克哈特神學所具有的“超神學”的氣質。在埃克哈特看來,知識建立在切身體驗的基礎上,神學的知識更應該是如此。如該書從解釋史的角度,詳細討論了埃克哈特對《聖經·路加福音》中馬大—馬利亞片斷的分析,這一案例也說明他如何對傳統經院哲學的經解有所入,亦有所出,并提出自己的獨得之見。埃克哈特對馬大與馬利亞的解讀,可以看出他解經思想中傳統與創新的一面,特別表現在他敢於背離傳統解經主流的意見,重新判釋“沉思的生活”與“實踐的生活”的異同高下。
顯然,埃克哈特的注經學有著鮮明的內在化傾向,與經院神學的解經學傳統保持著較大距離。他試圖在個人經驗、實踐生活與傳統神學權威之間尋求一種“精細的辯證”,這一點很像中國佛教史上禪師與經論師的區別。其實,禪者對於經教並非一味否定,只不過是注重於經教“唯意相傳”的一面,因而最終要“以心宗之衡准平之”。這種內在化的解經方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聖典本身的權威化,禪宗發展到後來的傾向就是這樣,語錄取代了經典成爲新的權威。而這也正是那些以聖典爲圭臬、以正統自居的人所最爲擔心和提防的。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多少表明,所謂正統與異端背後所呈現的,除了權力的分配與角逐,其對於聖典的不同解讀與處置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通常的情況是,或重於外在傳統的規範,或傾向於內心生活的經驗,決定了對於經教的不同態度和解讀,也逐漸形成了正統與異端的不同法流。
應該說,埃克哈特是兼備聖典知識與內心體驗的哲人,就他敢於在聖典經解中大量帶入自己的宗教經驗,而不一味因循傳統舊義而言,他的思想後來被教廷判爲異端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此並非單純和孤立的宗教個體性事件,而是典型化地表現了宗教解經立場和思想上的分野。禪宗初傳到中國,對於佛典的觀心之解亦曾遭受過類似的命運。我們發現,最初對禪宗極力排拒的,並非來自佛門外的外道,而正是來自佛教內部的經論師傳統。
於是,正統與異端的分別只是心法與傳統、內心體悟與外在立法之間對立的顯化而已。我們應該瞭解,內在化的解經學並不是一味地反對傳統,而是以爲傳統的根源就在個體性的心法當中。回到真正的宗教“傳統”,在他們的理解來看即是回歸於自心,從自心的宗教性體驗中去找尋真正失落的源頭。因此,解經重要的是如何以心解的方式,去填補和重建歷史所造成的時空距離。這種超歷史主義的回溯傳統,傾向於從內在經驗中去會解聖典的言外之意,即理解聖典需要在發乎本心與實踐經驗之間去作契合,因而強調解經要有獨得法眼與“出格之見”。這一解經學的原則與旨趣,恰恰與歷史時空中所形成的聖典及聖典注經傳統間產生了某種分離與緊張,難免易被看作革命和異端之舉。在宗教歷史上,當一種聖典的解經傳統被固定並合法化之後,大多有創造性和內向化的思想解讀就這樣經常被輕率地判爲異端。忠實於自己的本心所得,而不是追隨傳統形成的權威之見,這對於生活在宗教氣氛濃厚時代的埃克哈特來講,需要相當大的勇氣與擔當。
二、無執之道
無執是大乘佛家空宗思想常用的一個概念,它有所針對性地批判傳統修道者對於法的執持與固化,故而意在強調對於佛法果境也需要做到無所求和無所得。該書把“無執”看作埃克哈特神學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字,這一點確實和傳統神學修道論的主流意見大相徑庭。“無執”這種充滿了佛教色彩的修道觀念,讓埃克哈特的神學論述表現得尤其與眾不同。如他討論基督徒的祈禱觀念時,就特別指示出一種無目的性的無執的祈禱:“禱告是一種純粹的走出,是面對無。”“我請求上帝”,埃克哈特這麼禱告,“讓我擺脫‘上帝’”。埃克哈特的禱告不像一般禱告那樣導向有目的性的祈求某物,而只是一種否定和清空自我的過程。無執的禱告成爲一種否定神學的形態,類似東方佛教所說空性的智慧。對埃克哈特來說,不經過否定,便無法成就真實。只有告別了外在化與偶像化的上帝,告別了有利害因素——不管是物質的還是靈性的——的人神關係,才能回到真實的上帝和修道觀念。這與大乘佛教空宗的應無所住及空中生妙有的教義頗爲玄契。我們可以把埃克哈特的“無執之道”視爲通往東方宗教的一座橋樑嗎?
三、平常心是道
無執所帶出的靈性修煉,即是禪門所謂的平常心是道。佛教主張不能夠離世覓菩提。在禪門看來,浮華落盡後的平凡才是道,道在事中,必須在日常生活的應對與進退中去體會大道。對於修道者來講,返歸平常,於事中曆煉,才能夠透現出所謂的“宴定”(大定)。在禪的意境裏,平常不是平庸,平常之中有深密。這一點,我們在埃克哈特的神學思想中找到了特別類似的提示。埃克哈特建議他的聽眾不要逃離外面的世界,而應該獲得一種清晰的對內在生命的認知。他還特別強調必須在事物中把握上帝,讓上帝在我們內心深處強有力地、實質性地生成,如他對《聖經·路加福音》中馬大-馬利亞的解讀也正是基於這種觀念。
與傳統解經不同,他讚美馬大往事物與人群中去“把握上帝,讓主的形像在靈魂中成長”,并指出象馬利亞那樣放下一切、坐在主的腳前,在沐浴法喜中獲得的靜心並不是修煉的頂點,甚至不是學習上帝功課的最好方式。他說,如果我們要在此生中奮鬥,那麼不是上帝、宗教、靈性努力、哲學或神學,而是生活本身比任何主的在場都能教給我們更多關於上帝的知識。所以,清空了外在上帝之後,還必須走到神學之外,擁抱日常工作的挑戰。他指出,越是平常的、帶著日常的進進出出、在傳統意義上非宗教的人生,越是上帝的生命。越是上帝的生命,越沒有宗教性,越平常。因而把自己淹沒在世俗生活的平平常常中,比在虔誠的苦行禁欲中抓住上帝更妥當。無怪乎鈴木大拙要慨歎,埃克哈特的神學觀念與禪佛教的思想“實在太接近,接近得幾乎可以使人以十足的把握印證它們出於佛家的思維”(《耶教與佛教的神秘教》,前揭,頁6)。
當然,要從東方傳統來論究埃克哈特的思想,可以說的方面遠不止於此,這裏所論不過吉光片羽,旨在抛磚引玉。以佛教化或禪學化的方式來讀解埃克哈特,並非要簡單對西方傳統的神秘主義都作東方主義的格義,而只是提示我們一種可能性,即東西方的宗教可能面對某些共同的生命與心靈層面的課題,並提出過類似的解決方案。這種類似不一定要從哲學或歷史學的嚴密論述中去找尋,畢竟,埃克哈特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神學家和形而上學家,他同時是一位行者和生命大師(Lebemeister)。
對我來說,《無執之道:埃克哈特神學思想研究》是我閱讀到的相關著述中的上乘之作。埃克哈特是一位在漢語學界還沒有被充分認識的人物,相信該書的出版不僅對漢語神學的研究者助益良多,我更堅信,漢語學界研究東方宗教的學人也一定能夠從中找尋到更多的靈感和啟發。
鄭淑紅的譯文不僅文字流暢優美,絕無浮泛之氣,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譯文也確實可能傳達了埃克哈特的某些“非西方觀點”,因而更可以看作是一部解讀性的譯作。雖然這並不是一部有關佛耶對話的書,但是文中時常出現的“無執”、“無分別”、“無我”等觀念,確實會讓我們聯想到埃克哈特神學觀念中那種跨越宗教界限的力量。我們有理由期待,淑紅譯傳的埃克哈特將成爲東西方之間一席意味深長的文化與宗教對話。這部中譯本所具有的特殊價值與魅力正在於此,它也更加吸引我去作全面閱讀和細膩咀嚼。可以肯定,這部譯著會帶給漢語讀者更爲豐盛和富於挑戰性的閱讀經驗,無論是宗教或是非宗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