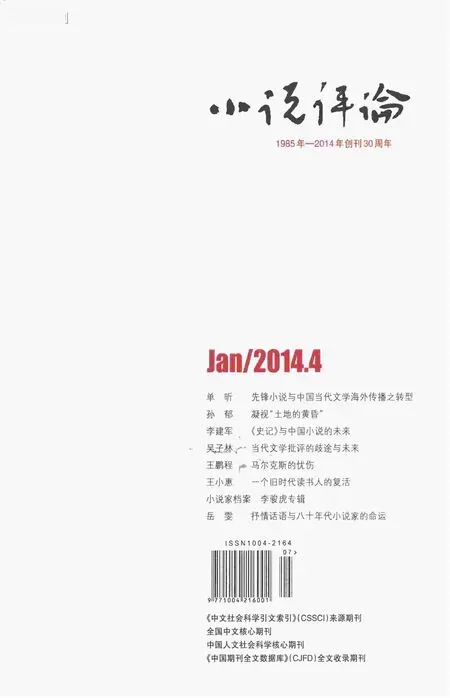“拧巴”与“绕”:生存伦理与语言逻辑的双重错位:刘震云小说主旨与风格探微
崔宗超
1987 至1990年的几年间,刘震云凭借他所发表的《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一地鸡毛》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开始受到文坛重视,同时,也正因为这一系列小说,刘震云被认定为当时勃兴的新文学创作潮流——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无疑,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理论概括,对于描述当年刘震云、方方、池莉、刘恒等一批文学新人的创作旨趣与艺术共性,有着相当的准确性与深刻性,而刘震云也得益于这种理论加冕,牢固确立了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然而,“新写实”这一术语,及其被评论家所赋予的“还原现实生活”、“塑造普通民众”、“冷静客观的叙述风格”等审美特征,作为一种宏观概括和理论维度,其语义的含混性与指称的模糊性,也显而易见,它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能力,一开始也便饱受质疑。因此,倘仅以此试图更清晰和深入地揭示刘震云小说的艺术个性与精神内涵,自然难乎其难。且不提1987年以前刘震云创作的《瓜地一夜》(1979年11月)、《被水卷走的酒帘》(1982年2月)、《栽花的小楼》(1984年11月)、《罪人》(1985年6月)、《乡村变奏》(1985年6月)等早期作品,明显不属于“新写实小说”;即便是1993年后,刘震云新创作的“故乡”系列小说、《手机》、《一句顶一万句》等小说,所体现的历史拟想、语言试验、生命叩问等艺术新变,也与“新写实”愈离愈远。
刘震云曾说:“我觉得用知识分子话语的‘新写实’不恰切,在创作中,我是带有感情的,打开了感情世界同艺术世界的通道,打开了这个通道才有创新能力。”“一个真正的作家写作,不是为了写而写,写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需要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尽管30 余年来,刘震云的小说创作无论在内容与风格上,都有多次明显转变。然而纵观其全部创作,我们仍能发现其中贯穿着作者最基本的生命体验和对世界的认识:“拧巴”。刘震云曾解释说,“拧巴”的同义词叫“别扭”,自己的创作是“想把生活中‘拧巴’了的理儿给‘拧巴’回来,把人骨头缝里‘拧巴’的理儿也给‘拧巴’回来。”结合其创作不难看出,拧巴在刘震云这里,实际上表述的是一种人生不通畅、不正常、背离了常理的社会生活与生命状态。也正是这种生存伦理与语言逻辑双重错位,以及刘震云不断尝试将这种“‘拧巴’的理儿也给‘拧巴’回来”的艺术努力,构成了刘震云艺术世界最基本的内核,成为可以将刘震云多变艺术世界一以贯之的基本线索与艺术主旨,同时也使他的艺术世界生发出了诸如反讽、复调、语言狂欢、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存在主义等诸多斑驳陆离的色调。
生存“拧巴”:生活混沌与秩序错乱
刘震云小说所构建的艺术世界不仅兼涉乡村与京都的三教九流、达官显贵以及凡夫俗子,而且其笔触不断在数千年的历史与当代生活之间、在梦幻呓语与现实之间,自由游走。然而,无论其所描绘的人生图景与生存状态是宏大高贵还是琐屑卑微、是时空久远还是近在眼前,作者似乎都在略带嘲讽、略带绝望与悲悯地重复讲述:世人无不处于拧巴的生存状态,伦理道德的坍塌衰微、乃至荒诞虚无似乎反而成了生活的恒常本质。
刘震云早期作品《瓜地一夜》中,生产队所种的西瓜可以随意被队长、村支书、乃至看瓜人享用和送人,而老实巴交的贫穷农民为让临死的娘吃口西瓜,被抓为偷瓜贼,遭受重罚;《被水卷去的酒帘》中,本无悬念的乡村婚约,在一个五十多岁老头子、某机关主任所能带来的县城新生活面前,瞬间如水流逝;《栽花的小楼》中,有着幸福婚姻的红玉,甘愿与曾经的恋人私奔,然而恋人已被生活磨灭了理想激情与斗志,红玉回到家中羞愤自杀;《大庙上的风铃》中,做生意让农村小伙子赵旺活的像个人样了,却无颜再面对曾经的姐弟亲情;《罪人》中,牛秋将娶亲的机会让给了哥哥,却按捺不住对嫂子的情欲,以至结婚后仍对死去的嫂子愧疚不已,他不需要自己的妻子,却仍要寻找离家的妻子,最后却发现妻子原来早有丈夫;《乡村变奏》中,秋荣不满恋人小水的无能,却又珍爱着他们的恋情;爱干歪门邪道、卖猫贩狗的成银,却悄悄将可买一个好价钱的老龟放了生……。总之,刘震云早期小说中的乡村生活,都是走了调的“变奏”,在这里,没有圣贤高人和仁人志士,也没有大奸大恶和宵小伪善,更没有伦理道德的庄严规范,只有一种混混沌沌、习以为常的不和谐和“别扭”,一切都脱离了常规然而又似乎没有什么常规。
1980年代后期及1990年代,刘震云创作的那些被称为新写实小说的《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和新历史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温故一九四二》、《故乡面和花朵》中,所表现的无所谓道德伦常和正义大道、同时又磕磕绊绊和零零碎碎的无聊无趣兼无奈的生活,从基本性质上来讲,和其前期乡村小说的主旨,并无不同。差别仅在于小说将拧巴的生活状态在城市的背景下表现得更为醒目、在历史的写实与虚构中表现得更为沉重而已。学者陈晓明在评价《故乡面和花朵》时说:“这部作品全面解构了很多的传统人伦关系,重新编织了很多新的关系:同性关系——错乱的关系;父子关系——反常的关系;异性关系——经常是被颠倒的;亲友关系——很虚假;偶像和权力关系——包含对秩序社会的强烈反讽。从古代到现代,人类社会的建构经历了从血缘关系、家庭关系到社会关系,这种建构要以伦理关系为基础。但在刘震云这里,可以看到这种种关系都受到质疑”。简言之,刘震云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成年人的令儿童和成年人都失望的世界。”
2002年,刘震云的小说《一腔废话》,“是《故乡面和花朵》的一个余韵”、“一个余波”、“胡思乱想之后”的“一个胡说八道”:五十街西里街区中的一些人的,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周围的人和生活都处于疯傻状态,他们为了寻找其中的原因和改变这种疯傻状态,最后却使五十街西里变成了更为恐怖的世界——人人变成了木头和木偶,任人摆布和宰割。这种荒诞混乱、不可理喻的生存状态,在刘震云近期作品《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中,仍是最突出内容:谈话节目《有一说一》著名主持人严守一,在生活中却靠谎话周旋在妻子与情人之间,结果狼狈不堪;民工刘跃进本来丢了东西要捉贼,却被别人像贼一样四处寻找;吴摩西、牛爱国,这两个相距七十多年的男人,都纠缠于无爱的婚姻之中,并被迫假意维护这种婚姻离乡漂泊;李雪莲告状本来想折腾别人,谁知道头来折腾了自己。
《一句顶一万句》中,看相的瞎老贾说:“所有的人都生错了年头;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这也是刘震云对拧巴的另一种解释,对他小说中人物命运与生存状态的总概括。
语言的绕:文化思考与意义追寻
刘震云在小说中对拧巴生存状态表现的同时,还展示了对这种错乱生活的思考,这思考在其前期的创作中并不明显,因此他的前期作品的内容情结和语言都显得相对单纯和通俗易懂。《故乡面和花朵》之后,刘震云小说的无论在叙事内容和叙事语言方面,都显得纷繁缠绕、甚至晦涩深奥。王朔就曾说:“刘震云在《故乡面和花朵》中,能用一句话说清的事,刘震云用了三页来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语言的绕,正是作者对自己所描绘的拧巴生存状态所不断进行艺术阐释和思考的表现。
刘震云承认:“读我的作品绕,我也发现了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为什么这么绕呢?确实它是有来由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一件事里有八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道理,这说起来的话就特别的费劲。不把六十四个管道给钻出来,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考习惯往往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这事就说不清楚。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我来把它说清楚。但是当我想把它说清楚的时候,所有人又说‘绕’。事不绕,但事背后的生活逻辑是绕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震云抱怨:“《故乡天下黄花》我觉得直到现在评论家看懂的不多。他们认为是另一种真实的历史,我写的时候强调的是文化。就是说在社会的整体框架中,到底是哪种文化更有生命力?更强大?是正统的力量大?还是一代代革命的思想力量大?(革命有个从不正统到正统的过程)还是民间文化的力量大?我看还是民间文化的力量大。”
显然,在刘震云看来,其作品语言的绕,是因为事情背后的生活逻辑与思维方式的绕,而这种语言与逻辑思维的绕,正是其作品所描述的人生拧巴状态的深层原因。换言之,语言的绕,是拧巴现实在逻辑思维层面、在(民间)文化的表现。
因此,在刘震云的小说叙事中,语言的“绕”,首先体现在人物语言与人物命运的纠缠中,主人公们常常因为一句不顺心的话以命相搏,一句特定的人物语言,时常充当了其小说叙述的核心与原动力,这就构成了其小说中常见的“一句话的悲剧”情节模式:《乡村变奏》中,小水因为恋人说“我看李发也比你强”,愤而搞运输出了车祸;《被水卷去的酒帘》中,郑四因为受到质问“你会干什么”,泼了命挣钱买缝纫机和自行车,但仍没有赢得青子的心。这种悲剧模式在刘震云的后期创作更明显:《手机》讲述了民国期间一个口信、1968年一个电话、手机时代一个短信,对严守一家族祖孙几代人生活与命运的关键影响;《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因为看厕所妇女的一句话:“该跟他闹呀”,与前夫、与法院、与县里、市里告状折腾了几十年;尤其是《一句顶一万句》中,剃头匠老裴、杀猪的杨百顺(后改名吴摩西)、贩葱的姜虎、运货司机牛爱国,都有为一个理、一句话要提刀杀人或离家出走的举动。这类的情节,刘震云小说叙事过程的高潮与转捩点上,左右着并且扭曲了人物的命运,使他们的人生呈现出拧巴状态。
刘震云后期小说的“绕”,还体现在叙事语言本身:220 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22 万字的《一腔废话》的语言狂欢,甚至淹没了故事情节和语言意义本身,让人有目不暇接、不知所云之感;《手机》之后的创作,虽然语言风格大为收敛和沉静,但其中情节框架的有意叠合与细节叙述的往复回环,仍凸显着缠绕的语言风格与转轴式的思维方式:《手机》中严朱氏、严守一不同时代的婚姻虽大不相同,但其阴差阳错的偶然状态却似乎又神似;《一句顶一万句》中吴摩西与牛爱国祖孙两代七十年间的出走与寻回延津,似乎是一种生命的轮转。《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告状初衷:“先打官司,证明这离婚是假的,再跟秦玉河这个龟孙结回婚,然后再离婚”,单从语言表述,就呈现出真与假、结婚与离婚的思维纠缠状态。
综上所述,刘震云小说中,“一句话的悲剧”的“绕”和叙事语言本身的“绕”,都在显示语言本身对于情节发展与人物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刘震云后期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在为一句绕的话或一个饶的理而赌气,并且常常是因为这种赌气而活着,在这里,语言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生命的主要支柱。因此,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来看,刘震云后期小说中语言及“绕”的凸显,还包含着他对啰啰嗦嗦、言不及义的日常语言现象的哲学性思考。刘震云曾说:“我想一般的人,一天……95%都是废话,那么为什么,上帝在安排舌头时间的时候,会安排它占95%的比例?我觉得废话肯定是支撑我们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个力量肯定要超过有用的话。”“人们整天都讲废话,这说明废话对人们的语言系统,生命历程都很有用。”他还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的不是假话,这种假不是对错那种假,而是对真相的无意识增减。《故乡面和花朵》就是从语言的虚拟中呈现我对世界的真实感觉”。
也就是说,在刘震云的小说所构建的艺术世界里,语言的绕,不仅是人们生存拧巴、生活错位的内在原因,而且这种绕的语言,还是人们在混混沌沌、悖乱失常的生活状态中,得以跌跌撞撞、步履蹒跚走下去的精神动力,不仅漂泊异乡吴摩西、牛爱国如此,不断打官司的李雪莲如此,就连过着“一地鸡毛”式琐屑生活的小林,在最后也意识到:“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拧巴”与“绕”的民间文化意义及限度
“拧巴”主旨与“绕”语言风格,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乡村民间文化心态与视角。这种创作心态与视角的形成,与刘震云早年经历关系密切。
豫北小县延津的乡村,是刘震云早年生活的地方,也是刘震云小说艺术表现的重心所在:“作家所以与故乡关联比较大,我同意因为故乡与作家的童年往往相联系。童年时代对于作家是一个宝藏……”即使其中“一些与故乡没有直接关联的作品,如《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两个系列,表面看是写城市的,其实在内在情感的潜流上,也与故乡或农村有很大关系。”故乡并没有给刘震云的童年带来更多的暖色,更多的是一种饥苦、荒寒、狭隘的情感烙印,在他看来,故乡是“一个毫无感情色彩的地域名字”,“没有任何让人心情兴奋的地方……在我脑子里的整体印象,是黑压压的,一片繁重和杂乱。从目前来讲,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我不理解那些歌颂故乡或把故乡当作温情和情感发源地的文章或歌曲。”
这种缺乏诗意的凝重乡村记忆,直接影响了刘震云的世界观、方法论,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使他对乡村底层人的生活“有认同感,充满了理解。在创作作品时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台阶上,用同样的心理进行创作。这同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是不同的,创作视角不一样。”刘震云说:“鲁迅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清醒的我是不清醒的,我比较混沌。”其实,刘震云小说的乡村文化视角,与现当代文学史上描写乡村的诸多写作传统,都有所不同:它不仅缺乏鲁迅的训诫式启蒙主义立场或叶紫等左翼作家们的阶级斗争立场,也无意于像沈从文小说那样建造人性神庙和重铸民族道德,更没有赵树理小说中的问题意识和王汶石、李准、柳青等建国初期农村小说中的对现实政治的趋附,同时也不同于莫言对乡村的人性张扬和余华《活着》中对农民坚韧生命力的宣扬。“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我特别推崇‘自然’二字。崇尚自然是我国的一个文学传统,自然有两层意义,一是指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作者的真情实感,二是指文字运行自然,要如行云流水,写得舒服自然,读者看得也舒服自然。中国的现代派作品就不自然,是文字游戏,没有什么价值。”在自然呈现乡村生活方面,刘震云不经意间游离了20 世纪中国新文学所确立的明显带有西化特征的现代性范式,而远承了本土传统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类似元曲《般涉调·高祖还乡》的相当纯粹的乡村视角,对处于传统与变革互动中农村社会生活的状态,进行了自然呈现式描摹与隐喻。
然而,在悬置了启蒙、诗意等外在因素之后,刘震云小说中所呈现的乡村世界,是那样的充满若无其事的苦涩琐屑、混乱不安,充满了错位、反讽与冷幽默,亦即“拧巴”。简言之,刘震云小说中“拧巴”主题的形成,一方面是作者早年经历的“黑压压”农村生活的文学表现,更重的是,他作品所采用的自然呈现乡村视角,放弃了对启蒙主义、诗意、问题意识、政治或干预生活的激情等这样一些社会职责或文化建设的主动担当,这就使得刘震云小说中的生活,缺乏一种高远的积极的精神纬度进行梳理、凝聚、评判和关照,因此显得混沌、杂乱、压抑和阴暗绝望。比较而言,鲁迅的小说固然冷峻,但总让人感到不满,想去呐喊与抗争,天上还高悬着象征美好未来的一轮金黄的圆月;而刘震云的小说,则让人感到消沉,并自得于委曲求全和“环球同此凉热”的生活之中,最常见的意象是天上血红的晚霞和剪纸般恍惚苍白的人影。在刘震云看来,“世界混沌纷繁,千古一泡血泪,谁又能说得清楚呢?”“鲁迅觉得铁屋子里有几个人清醒,是他觉得他首先清醒了。所以他才能找到知音。但这知音找得对不对,我觉得存在问题。至于他自己是不是清醒,也是问题。我觉得如果我在铁屋子里,我首先是不清醒的。所以我也没有找到知音。如果找到知音的话,这些知音也都是不清醒。”这显然是一种乡村常见的民间文化史观。
刘震云的“拧巴”乡村叙述视角与其中的民间文化史观,还使刘震云具有了与同样凭借“新写实小说”创作成名的方方、池莉、刘恒等作家迥异的艺术特质。当然,在对启蒙、诗意等理想主义和宏大话语的放逐态度,对日常琐屑生活的描摹上,刘震云与其他“新写实小说”确有相似之处,但由于早年生活的关系,方方、池莉和刘恒等人的创作视角,实际上是城市化的:他们所表现的生活充满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喧嚣与热度,人物语言简洁清晰,故事情节直线发展;而刘震云在创作中则处处以乡村的思维和精神来丈量和表现世界:生活混沌凝滞,人物语言絮叨缠绕,故事情节复沓回环。尤其是在对历史与大人物的理解和表现中,刘震云的乡村叙事视角,表现的最为充分: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为争夺一个小寡妇;朱元璋则像一个善于骗人、满口粗话的乡村无赖;慈禧太后到延津,是为了偷会情人,太平军领袖陈玉成则红眉绿眼、一身瘴气。《官场》与《官人》中,对于省部级官场的描写,也充满了乡村政治的小心计,缺乏复杂的政治力量角逐与宏大利益考量,这显然是乡间底层的政治观念。
传统的乡村文化观的“拧巴”特色,还体现乡村在对权力的敬畏与亵渎、对神圣的崇拜与戏谑,这一个看似矛盾的心态中,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一方面,乡村小农们虽然时常能够感知政治统治力量或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对他们生活的巨大影响(这影响大多是巨大的灾难),并不由自主的会敬畏或膜拜这种力量和人物,祈求受到垂青而获得温饱平安或荣华富贵;另一方面,狭隘的生活世界与眼光,是他们无法真正理解政治力量的运行与大人物的内心世界,更无法理解他们常常给底层乡村所带来的苦难,因此,常以一种世俗与庸常的心态去忖度和应对他们,这就造成了民间文化具有了某种反讽意味和存在主义意味。这些意味,在《头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温故一九四二》中,都非常突出,不过在刘震云看来,他并不是在反讽和表现什么存在主义,这只是生活固有的“冷幽默”,刘震云解释说:“这跟黑色幽默还不一样。这种幽默触手可及随处可见。它能消解许多种困顿、焦虑与不安。它能够使人苟且偷生,成为一种生存下去的极大的精神支柱。……把麻木变成有趣。我觉得这是中国这个民族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然而,乡村文化创作视角,在给刘震云的创作带来“拧巴”、“绕”、“冷幽默”等鲜明的艺术特质的同时,也给刘震云的创作带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乡村文化虽然贴近底层,充满土滋味泥气息和鲜活的生活质感,但毕竟芜杂散漫,一旦作者在创作中对此没有足够的警惕,沉溺其中,也很容易导致笔调放纵和语言狂欢,使文学创作变成无意义的语言游戏,使读者难以接受,而从接受美学上来讲,一个作品没有被读者接受,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刘震云耗时8年所做的长篇《故乡面和花朵》,虽然对刘震云的创作风格转变具有关键意义,但从艺术价值上来讲,实际上并不成功。其次,乡村文化还有一种狭隘性和犬儒主义倾向,它的本质就是鲁迅所批判的“阿Q 精神”,刘震云称之为“冷幽默”,并正面强调对乡村的苦难消解与精神抚慰作用,这虽然有其道理,但这毕竟是一种麻木、无聊的消极心态,由于作者对此没有恰当的超越,“他对农民文化本身的反思和批判也因之显得举步维艰”,其创作也很容易流于琐屑、空洞与平庸,《我不是潘金莲》就有这方面的不足。实际上,刘震云也说:“一个作者背后的蓄水池到底有多深是最重要的。这个蓄水池中有对生活的认识、对哲学的认识、对民族的认识、对宗教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等等。作品呈现了其背后的蓄水池。……一个作家真正的功力不在有形的小说,而是后面无形的东西,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具体到一个作品里面,作家真正的功力包括呈现出的力量,不管是荒诞还是什么,它不在你的文字表面。功夫在诗外。这就是结构的力量,这个结构力量特别考验作家的胸怀,这个胸怀就是你能看多长看多宽,你对生活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对文学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认识。”可以看出,刘震云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代表的近期创作,就是在追求一中大境界、大情怀,追求对乡村文化视角狭隘性的某种超越,这也是他近期创作风格新变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267页。
②24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③④⑩12 15 16 22 27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第3期。
⑤王佳欣:《把拧巴的捋顺了》,《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11月15 日。
⑥陈晓明:《故乡面与后现代的恶之花——重读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⑦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卷一)》,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⑧刘震云,姜广平:《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冷幽默》,《西湖》2012年第8期。
⑨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11范宁,刘震云:《我是中国说话最绕的作家吗》,《长江文艺》2013年第3期。
13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4李潘:《真不容易》,西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327页。
17刘震云:《刘震云精选集》,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页。
18 19 21刘震云:《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文艺争鸣》第1992年第1期。
20刘震云:《三问三答》,《大家》2001年第4期。
25刘震云:《刘震云自选集》,现代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29贺仲明:《独特的农民文化历史观——论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当代文坛》1996年第2期。
30刘颋:《一个作家身后的“蓄水池”——刘震云访谈》,《朔方》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