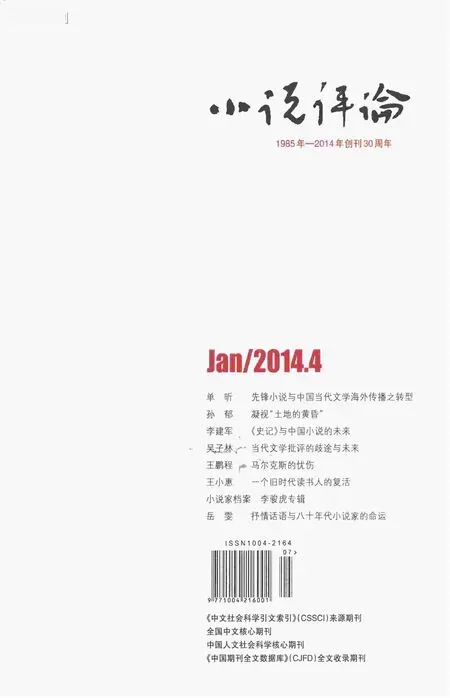《统万城》:浪漫主义骑士的英雄之歌
王金元
《统万城》是被称为浪漫主义骑士的高建群封笔之作,是一部真正的英雄史诗。高建群在这部小说中书写他对历史和人生的最深刻的体会,表现出他对于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最后敬意。可以说,这部小说是用他骨子里那股浪漫主义情怀与心底那份浓浓的英雄情结凝结而成的一首浪漫主义骑士的英雄之歌。
《统万城》虽然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是与其他历史小说相比具有独到之处。首先,作者在表现历史时不是机械地复制历史,而是寻求历史发生的必然律和可然律,将历史书写富含艺术性,从而提炼出一部带有诗意的历史。其次,作者将英雄情结渗透到在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落,着重展现出英雄以及与英雄相关的爱情、传说、战争、巫史等一系列具有浪漫主义色调的母题,并从中升华出作者对于历史和人生的哲学解读;最后,作者在叙事上既采用了双线并进的传统叙事手法,同时也运用了蒙太奇、拼贴等现代和后现代叙事手法,使得小说在历史叙述中拥有了具有了更大的张力,拓展了历史事件与人物形象的原有容量。高建群通过对《统万城》进行以上方面的熔铸,使得这部历史小说在思想与艺术上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成效。
一、诗意化的历史书写
《统万城》讲述的历史是被称为乱世的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用作者的话来说“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黑暗、最为动荡的岁月,同时又是一个张扬激情、张扬个性的岁月。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南北大融合时期。”他在表现这一历史时并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只做“具体事件”的考古者,而是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发掘历史所蕴含的“普遍性的事”。
亚里士多德区别了诗人与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的不同,“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记载具体事件。”高建群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种诗人,他将以游牧文明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及外来的西域文化、古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多元文化融汇到这一历史时期,并在这距今一千六百年的历史迷宫中,寻找到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两个重要的节点,一是匈奴民族的退出历史舞台,一是汉传佛教的创世纪。这两个历史事件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都是可资记忆的,对华夏文明板块的发展和延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高建群通过这两个历史事件进行诗意化的处理,既让世人看到了历史发生转折的多种可能性,又将历史终究按着自身规律前行的必然性揭示出来。
高建群在小说中集中表现了匈奴这一民族对于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所起到的影响以及改写历史的可能性。小说写了这一时期震动东方和西方的两位匈奴民族首领,一位是南匈奴末代王赫连勃勃,他建立五胡十六国之——大夏国,建造了一座辉煌的匈奴都城统万城;一位是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他是北匈奴的末代王。他在今天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建立了匈奴大汉国,给整个欧洲大陆带去了威慑。匈奴民族历史上的两位伟大首领,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游牧文明的独耳狼旗向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和以海洋文明为代表的欧罗巴地区发起了进攻并建立了统治政权,打破了固有的世界秩序和文明格局,从而为历史提供了转折和改变的可能性。然而,历史却因许多偶然的因素制造了必然的结果。两位匈奴末代王赫连勃勃和阿提拉纷纷死于爱人所赐的毒酒下,完成了自己的绝唱。匈奴这一民族也在华丽转身后推出了历史的舞台。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作者在书写匈奴这一民族历史时,看到了这种历史发生的普遍性,不仅为读者展现出了普遍的历史事件,而且客观揭示出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一普遍规律就是马克思说所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高建群将这一历史规律隐含在小说之内,利用英雄史诗、英雄悲剧等诗意化的处理将匈奴这一民族在历史上所存有的辉煌和悲壮揭示出来,从而使得小说中所叙述的历史更富有哲学性和艺术性。另外,小说还将匈奴末代王赫连勃勃与大乘佛教的创世者鸠摩罗什放在一个时空内,将两个无关联系的人用时代命运牵连起来,使他们共同筑起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主题。不管是民族融合还是文明融合,它们都给中华文明注入的新鲜血液,使得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来一直屹立不倒,生机勃勃。
高建群从这两件看似毫无联系的历史事件中窥探出共同的走向,从而将它们收集起来重新组合到历史的发展序列中,升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主题和规律。虽然这段历史有着命定的行程和框位,然而作者却可以将历史中的千回百转表现得多姿多彩,因所叙述的历史,是诗意的历史。
二、英雄母题中的史诗品格
母题(motif)最早起源于民俗学的神话研究中。民俗学家汤普森对于母题曾有这样的界说:“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存于传统中的成份。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绝大多数母题分为三类。其一是一个故事中的角色——众神,或非凡的动物,或巫婆、妖魔、神仙之类的生灵,要么甚至是传统的人物角色,如像受人怜爱的最年幼的孩子,或残忍的后母。第二类母题涉及情节的某种背景——魔术器物,不寻常的习俗,奇特的信仰,如此等等。第三类母题是那些单一的事件——它们囊括了绝大多数母题。正是这一类母题可以独立存在,因此也可以用于真正的故事类型。显然,为数最多的传统故事类型是由这些单一的母题构成的。”从汤普森对于母题的界定和特征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母题主要是为我们展示世界上相似的、类型化的故事情节,以便我们来把握和辨认。“这种情节元素具有鲜明的特征,能够从一个叙事作品中游离出来,又组合到另外一个作品中去。它在民间叙事中反复出现,在历史传承中具有独立存在能力和顽强的继承性。”母题发展到现在,已经从民间叙事研究的学科术语上升到能更大范围内使用的文学理论范畴。“现代批评开始用母题来描述和分析那些反复出现于不同文本中的构成成分。它或者是一种在众多叙事文本中都会出现的基本要素,如某种角色、人物、道具,或者是特定的情境、背景;也可以是一种单一的程式化的事件;还可以是一种与具体的叙事对象无关的言说形式或话语单位。”尽管母题拥有多种具体内涵,但是这些内涵都共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母题必定以类型化的情节、结构或者叙述方式反复出现于不同的文本之中。
高建群在《统万城》中应用了大量的母题来完成文本的创造,其中有英雄、战争、复仇、英雄美人、传说、巫术等母题。这些母题的使用,不仅可以丰富小说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而且可以让读者更加深刻地领会到小说中的史诗品格。《统万城》中最具有史诗特征的地方莫过于对于英雄母题的使用,其他的母题如战争、复仇、英雄美人、传说、巫术等都是紧紧围绕英雄这一母题相伴相生,并为之服务的。
东、西方文学对于英雄母题的表现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西方文学将塑造英雄作为一种伟大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英雄史诗中反复出现的母题通常包含“英雄身世类母题、英雄对手类母题、神奇动植物类母题等几大类。”英雄身世类母题一般包括英雄出生特异、英雄的父母比较传奇、英雄的爱情比较唯美、英雄被害等母题;英雄对手类母题主要指英雄的对手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神奇动植物类母题是指英雄史诗中经常出现一些神力的动植物。
高建群在《统万城》中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继承了英雄史诗中所共有的英雄母题,尤其是英雄身世类母题。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匈奴末代王赫连勃勃和大乘佛教创世人鸠摩罗什,虽然身世各异,但是作为作者塑造的英雄形象,他们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到生命结束囊括了英雄史诗中出现的所有英雄身世类母题。首先,两位英雄都有非凡的出生经历并且都会有神人一样的人对英雄的身世进行预言。赫连勃勃出生在行走的高车上,而且是逆生的。具有神力的女萨满说:“逆生,不正常生的人,按照民间的说法,这会是一个不安生的人,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鸠摩罗什在母亲的胎腹中时,她的母亲罗什公主的身体就出现了种种异象,例如身体突然充满了檀香的味道,口中居然会说出从未接触过的天竺国语言并能背诵大段大段的经文。一位过路的拖钵僧,告诉罗什公主“你怀的是一个非常之人,他的光辉将照亮东方,如果这个孩子在三十五岁之前不曾破戒的话,那将是位圣人,一位佛陀,将会大兴佛法,度无数众生,人们对他怀着怎样的期待都不算过分。”其次,两位英雄都有伟大的父母并且父母将巨大的使命寄托在英雄身上。赫连勃勃的父亲是被称作“朔方王”的匈奴西单于。赫连勃勃一出生就被父亲赋予了成为草原上王者的使命。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因为不满于他的软弱,使用两次非常的方式来磨练他的意志,一件事是把他扔在河里让他自我解救,另外一件事是用在炉火上烧红的弯刀在他的脸上划上三道痕,教会他勇敢和凶恶。这两次极端的方式都是赫连勃勃被父亲寄予英雄使命的体现,为后来他成为大夏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炎是一位得道高僧,本是天竺国宰相的继承人,因为志向是去东方弘扬佛法,在去东方的途中遇到了龟兹国的罗什公主,在命运的安排下成为了龟兹国的宰相。鸠摩罗什的母亲是龟兹国的罗什公主,才貌双绝,见识卓著,在鸠摩罗什孩提时期,放弃了公主的地位带着鸠摩罗什出家,并远赴西域三十六国游走,最终为佛门事业献身。鸠摩罗什在出生时同样被父母赋予了重大的使命。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对母亲说“这个孩子不是为世俗的社会而生,而是为我未尽的理想而生的。我的双脚已经被牢牢地捆绑在大地上了,动弹不得,希望他不要这样。那根打狗棍、那只讨饭钵,我一直还留着,让他拿着,有一天,送他上那通往遥远东方的道路吧!”母亲在他少年的时候,担心宫中温柔富贵的环境会消磨鸠摩罗什的意志,遂决定带着鸠摩罗什出家并远走西域三十六国,来让鸠摩罗什完成父辈交给的理想和使命。最后,两位英雄都创造了伟大的事业并留下了为人们所称道的奋斗精神。赫连勃勃遭遇了家族被灭、亲戚背弃的人生变故,在忍辱负重之下不断成长,最后在草原上建立了威名赫赫的大夏国,并筑起气势恢宏的统万城,给历史留下了永久的记忆。鸠摩罗什则经历了长途跋涉、凉州蹉跎的人生历练,终于凭借他的执着来到了理想中的东方,在长安城建立了当时最大的佛教中心。两位英雄为理想和使命而奋斗的人生态度和奋斗历程,成就了他们的英雄之名。
传统的没落在学界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如白晋湘认为:现象上是传统体育的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不同于西方体育的竞技性、惊险性、健美性;而实质是因为两种体育文化的背景源于世界文化的两个不同的体系,西方文化体系更为强势[8]。值得注意的是,外来文化包含非常强势的西方文化,也包括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异质文化。笔者认为: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是单向度的,而会是双方间全面的对抗。
小说对于其他英雄类母题也进行了展现。一是展现了神奇力量母题。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具有神奇力量的人物和场景,有半人半神半巫的匈奴女萨满和西域耆婆,有恒河上劈开胸膛淘洗肠肚的高僧,还有舌吐莲花的鸠摩罗什,这些神奇力量的表现都为小说的英雄母题增色不少。二是展现了神奇的动植物主题。小说写了马、鹰、狼等动物,这些动物是我国英雄史诗中经常出现的母题。小说尤其是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写马,将马作为英雄最亲密的朋友、最忠实的助手,并且马具有神力,一旦有险情发生,它会提醒自己的主人,而当英雄遇难,它会奋力去救自己的主人。小说还写了带有神力的狼,匈奴王赫连勃勃和“上帝之鞭”阿提拉举着独耳狼旗征战,将苍狼作为保护神,在苍狼神的佑护下,他们无往而不胜成为一代英雄。高建群对于神马和神狼母题的运用展现出具有草原游牧文化特色的英雄母题。三是小说写到了英雄美人母题,如鸠摩炎与罗什公主、赫连勃勃与鲜卑莫愁的爱情一个是热情奔放式的,一个是含蓄婉转型的,但都饱含着英雄母体的奇幻色彩和浪漫情调。
高建群通过运用以上所有的英雄母题使得小说具有了一种英雄史诗的品格,让历史上的英雄主人公既表现出世俗性特征又表现出超人的独异性,成为人们永远诵读的丰碑。
三、多元化的叙事
高建群在小说《统万城》中运用了多种的叙述手法,既有双线并进的传统叙事手法,又有蒙太奇、拼接等现代和后现代叙事手法。通过这些叙事手法的应用,小说在描写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将历史与现实、真实与想象完美地结合起来,不仅扩展了历史事件的社会生活容量,而且挖掘出历史事件和人物形象更为丰富的意蕴。
首先,高建群在《统万城》中采用了典型的双线并进的叙事手法,将小说描述的历史集中分割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展现匈奴末代大单于赫连勃勃的传奇一生,从赫连勃勃的出生写起,一直到他建立大夏国,筑起匈奴唯一的都城统万城。这一部分可视为一部赫连勃勃大传。另一部分,展现了西域第一高僧鸠摩罗什的传奇一生,从鸠摩罗什的父亲写起,写了鸠摩罗什的出生,在鸠摩罗什凉州城的羁留,以及抵达长安城草堂寺的故事。这一部分可视为一部鸠摩罗什大传。这两个部分既独立成局,又相互映衬,展示了两个英雄人物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他们异于常人的精神品格,多维度地挖掘出英雄的内涵。赫连勃勃为了复兴匈奴民族,虽然也用了一些残忍的手段,如为他岳父莫奕于将军设下陷阱并夺取了固远城等,但小说并没有停留在对这位大恶之华在复兴匈奴民族所作所为的批判上,而是重点刻画赫连勃勃身上特有的匈奴英雄气概。赫连勃勃在年幼时期遭遇了家族被灭的灾难,从小就在心中种下了振兴家族和重建家园的梦想。赫连勃勃好几次身处险境,死里逃生,心中却一直坚守筑城的梦想。在叱干城墙下,他向玩“掷羊拐”的小孩们借走羊拐,然后用一个个的羊拐堆起城墙和城楼。他说“我要造一座城,一座匈奴人的城,一座童话般的城。我要这城像咸阳城一样宏伟,像洛阳城一样壮观”。赫连勃勃历经人生坎坷,终于建立了大夏国,建成了统万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鸠摩罗什同样是一个拥有梦想的英雄,他立志要去东方弘扬大乘佛教,途中经历了凉州滞留17年的艰辛,经历了频繁的战乱,但他矢志不渝,终于来到了长安,在草堂寺广传佛法,完成了光辉的事业。
赫连勃勃和鸠摩罗什两位英雄,一个是大恶之华,一生沾满了战争留下的血迹,最后死于爱人的毒下,一个是大智之华,一生融化在佛法的光辉之中,最后含笑圆寂。虽然两人人生历程不同,命运结局不同,但都有着伟大的梦想,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崇高的事业。
其次,高建群采用了蒙太奇式的镜头转换方式,将小说的两条主线和附属部分有机结合起来,使得小说叙事在叙事时有条不紊,结构更加和谐完整,故事情节更加丰富生动。高建群在小说中并不是把历史上的两个事件简单地放在小说中任其自由发展,而是将两条主线和附属部分通过镜头的切换相互交织在一起,使赫连勃勃与鸠摩罗什、赫连勃勃与阿提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命运的时空对望中获得更加深刻的自我存在。高建群在书中写到“赫连勃勃与鸠摩罗什,这两个乱世中的特殊人物,此生注定将会有一次相遇。相遇之后,各自西东,又继续踏上他们命定的道路。”但是,此后他们虽然不再打过照面,却在不同的地方遥系着对方。当姚兴皇帝有一天问起鸠摩罗什如何评价赫连勃勃是,鸠摩罗什叹息说“那是一位天人,一位为某项特殊使命而来到世间的可怜的人。不要评价他的对与错,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站在末代匈奴王的角度来看,都是必须的。在这样的任务面前无所谓对与错、善与恶,人类现存的法则和善恶根本不适用于他!”赫连勃勃在夺取长安城后即将离去之时,突然想起要去终南山下的草堂寺拜谒鸠摩罗什高僧,想告诉他当年长安城楼上所托付的三万龟兹百姓的事,已经安置妥当,并且还想再问一下他当年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真的可以实现吗?这两次没有相遇的相遇,不仅牵起了赫连勃勃和鸠摩罗什两人的命运,同时使我们能够将一方的叙述将自由转换到另一方身上,从而将分离的镜头组合到一块,使故事情节有序而完整。另外,小说中还写到了同时期另外一位伟大的匈奴首领阿提拉的故事,通过末代匈奴王赫连勃勃和“上帝之鞭”阿提拉的遥望和关照,既让我们看到了两位匈奴英雄在世界历史进程所铸就的辉煌事业,也让我们看到了匈奴英雄所经历的共同悲剧命运,从而使匈奴这一民族在历史舞台中的退场写的更加完整、深刻。
最后,小说还采用了拼贴的后现代主义手法,将现代嫁接到历史当中,对历史中的事件和人物做了现代的佐证,不仅使历史小说具有了现代品格,而且也让现代生活有了历史传承。高建群在小说序歌中写到了赫连勃勃的对话,对他说现在有一首流行歌在写他还有匈奴民族,歌词是“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人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腐锈的铁衣——”。赫连勃勃觉得这几句歌词的确是在写他。另外,作者还将昌耀以及他的《高车》放在小说的第二歌中,在昌耀的高车上伟大的赫连勃勃降临而生;将郭地红的《昆仑英雄传》这首游牧古歌借用女萨满的口中唱出,让我们在草原上看到赫连勃勃这位天赐的英雄。小说通过拼贴的叙事手法将历史与现代搭起一座桥,让我们能够穿行在历史和现实当中,将匈奴民族的辉煌接续起来,将英雄的气血流淌开来。
总之,高建群在《统万城》中用歌的形式吟诵了一首英雄之歌,完成了浪漫主义骑士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诗意行走,为我们留下了横越所有历史时空的英雄精神和理想丰碑。
①⑧⑨⑩11 12 13 14高建群:《统万城》,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8,78,33,43,107,3页。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
③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页。
④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⑤陈建宪:《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版,第11页。
⑥孙文宪:《作为结构形式的母题分析——语言批评方法论之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⑦郎樱:《史诗的母题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9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