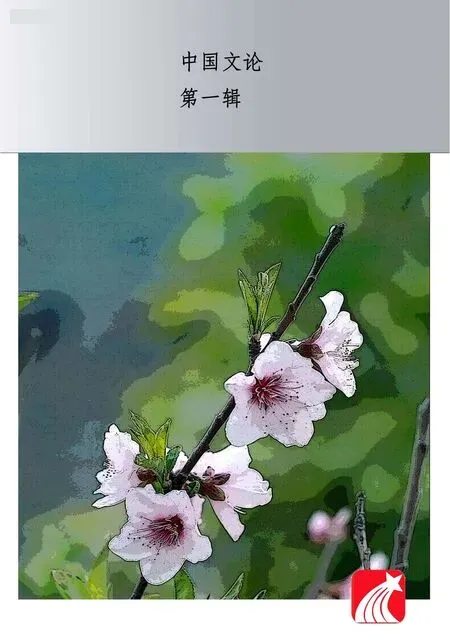政事乎?文学乎?
——《文心雕龙·议对》篇细读
游志诚
政事乎?文学乎?——《文心雕龙·议对》篇细读
游志诚
《文心雕龙》是一本“论为文之用心”的著述,然而须知这个“文”意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之文,更须推源溯本,只有具备“子家”胸怀,镕铸经典,翔集子史之人,始能作此大块之文,文心文论就是在此背景之下产生的文论。本篇研究,从文献学角度考查子集分合,辨析“杂家”新旧内涵,细读《议对》篇用政事之文对抗“舞笔弄文”之意义,重新解释《文心雕龙》此书的著述性质。
文心雕龙;子集合一;议对;政事;文章
按照章学诚《校雠通义》一书提示《汉志》有互著法,谓同一书互见两处。考察历代著录《文心雕龙》一书,也同样有“互见”的情形,除了“经籍”一类未见著录,其他凡是史部、子部、集部等三类无不有人著录过。甚至日本藤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文心》此书,先入子部杂家,后又入总集类,将《文心》此书互见,分入两门,盖即属章学诚“诸子即后世之文集”定义之下的集部学术,明显与后世例如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首立《文心》为诗文评类的“文”集概念,大为不同,而有文集古义与后出义之别。
据此《日本国现在书目》分子部杂家与总集著录《文心雕龙》的作法,即是章学诚“互著”法的具体呈现,亦最能展现刘勰其人一生学术的总体风貌。同时,也反映了两汉以下,私人著述畅行,个人文集纷纷刊行,由子到集,亦分亦合的“子集合一”之文献状况。
考历代著录《文心雕龙》此书,当有十五类之多。除了经部阙录之外,凡史、子、集三部皆有,反映出《文心雕龙》此书归类非常不一致,往往有“互见”的类别,不只两见三见,举凡别集、总集、子部、史部等无不有之。如果再加上《道藏》的著录,以及像《山堂考索》与《太平御览》类书的摘录,则《文心雕龙》的学术归类又可以再加丛书与类书两项,此书的“互见”情况益形繁复矣!它远远超出《汉志》的“互见”著录最多也不过“三见”的范围。例如《汉志》著录《管子》入法家、道家;而《弟子职》一篇又别属《礼记·儒行》篇与儒家同类;又《司马法》互见礼部与兵家:但也都只是二见而已。由以上比较可知《文心雕龙》此书互见“多元”学术类别的事实,有力地表明《文心》此书的“杂家”性质,用“杂糅诸家为一家”之概念最足以说明《文心雕龙》有不折不扣的“子书”性质。因为,唯有子家始知会通学术之道,翔集“子史”,镕铸“经典”,将经史子集之学融会贯通,“折中”为一家之学。因此,由历代著录《文心雕龙》此书互见多元学术类别,判定此书为“子学”之作,则刘勰其人理当视为“子家”性格。刘勰是子家,《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终于可以根据此书“文献目录”历代著录事实,得到有效的推论与印证。《文心》此书内涵的子书性质,可以从每一篇原文分析,其中的“义理”大都根据“子学”思想,做为刘勰“论文叙笔”背后的“理论”本源,具体证明《文心雕龙》内涵深厚的“子学”思想,更有助说明《文心雕龙》之历代著录,明清两代用“诗文评”观点看待此书的理由。至清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总目》收录此书,始正式定位《文心》为诗文评专书之后,《文心》全书的子家性质亦至此而埋没不彰,刘勰一生学术自成“专门之学”的特质也因此受到严重误解。究其根本原因,就在汉魏文集古义与明清诗文后出义不明,混言“诸子文集”与后世“集部文集”的概念为一类所导致之误读。
案《四库全书总目》于集部下新增“诗文评”一类,堪称四库馆臣学术分类之创见。盖馆臣编辑历代图书之目的,务主学术细目之“分”,不尚学问大道之“合”。为求分类而要求细目分明,馆臣不得不自原作文史类之《文心雕龙》析离为一类,改判为诗文评,置之首编。或许此举可视作纪昀平生爱读此书的心得创见,然而纪昀所“破”处,亦正如自己所“盲”处。今按四库总集类前有“序”云如下:
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始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然文章相扶,理无偏废,各明一义,未害同归。
细读纪昀此节对“集部”之学的分类,完全采用“分而又分”这种细目分类原则,从“大道”脱离,往“专精”的方向发展。因此,《诗经》要从总集三百篇本来的“集”之性质,排除出去,升格为“经”。先将“经”与“集”判别分立,依此类推,子与史二部也必然不属于“集”。纪昀的学术归类法完全是“分”的思考,不是“统合”与“圆通”的方法。准乎纪昀的分类,《文心雕龙》的归类必然不会有“互见”之作法,亦必然要归为集部之下再细分出的诗文评矣!经此细分之误,《文心雕龙》全书丰富而多元的理论思想内涵即不再被探讨与发掘矣!
由以上历代《文心雕龙》著录之十五种类别而言,此书几乎包尽经史子集四部,可见历代学者视此书之多元观点,向不以“单一”学术归类理解此书。此文献著录之多元事实,不只反映《文心》一书之复杂性,由书知人,亦同时反映《文心》作者“刘勰”其人学术之“通儒”路数,非自甘于一乡曲学之士可比。至于论文一家,尤其不足以划限《文心雕龙》全书内容。故而北宋《太平御览》以“类书”性质,亦收此书。甚至,道藏亦视此书为道教之作,并收录之。总上而论,《文心雕龙》全书“唯务折中”的论述方法,兼参各家的特色,实在最符合“杂家”之定义。《箓竹堂书目》编入“子杂”类,必有其理。另外,据杨明照在《文心雕龙》历代著录与品评一文之末所作的附注云:“日本藤佐世《见在书目》将舍人书两属,既入杂家,又入总集。”对此,似不以为然,故而杨明照云:“故未列入。”详味杨氏之意,不认同《文心雕龙》既是总集,又是杂家的双重著述性质。
其实,日人藤佐世两属《文心》此书的作法,反过来看,正代表《文心》此书之多元复杂,并再次印证刘勰写作此书学术背景,本为“镕铸经典,翔集子史”的通儒之作,才导致《文心》此书的归类难定。刘勰一生“折中”方法之学,不唯在文论之见是如此,子学理论亦然。刘勰于“论文”之外,又身兼“子部杂家”学术身份,以总结自己一生的子家“折中”之学,乃才人志士必有之常情。由《文心雕龙》一书的历代著录文献资料,澄清《文心》此书实“子家”之作,理解刘勰一生之学乃子部之学,亦可谓一解矣!
考明清学者尝著录《文心雕龙》入子部,以子家之作评价此书,则刘勰其人不仅为论文家,也是自成一家之言的诸子之流。今据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一书附录著录“入子类”之五家,与“入子杂类”之二家可略得其说。除了杨氏列目之外,又见日本九州岛大学藏明代刊本《文心雕龙》一书,总题《刘子全书》,以子书类别刊行,同书别刊《刘子新编》,固已属子部,而自两唐书著录以下,《文心雕龙》皆入子家。
另一本是亨保十六年(1731)大阪心斋桥筋文海堂刊行冈白驹校正句读本《文心雕龙》,书前有冈白驹序,作于亨保辛亥春三月。此序文不但以“子学”观点评论《文心》此书,更有谓《文心》一书乃“旁论文体”,意思是《文心》全书以圣贤之志为本,而文体之论述,乃此书之旁出。冈白驹《刻文心雕龙序》云:
昔者圣王之为政也,其迹乃有诗书礼乐,诗书礼乐之教,虽高矣美矣哉,而其书所载,则不过专之无言而已。言之不喻也,文以足之,焕乎炳蔚,高矣美矣者,存于文辞之间。……东莞刘勰氏盖有见乎兹焉,是籍之所由作也,乃旁论文体,而要其枢纽,以为古之为辞者为情而造文,今之为辞者为文而造情。……使文不减其质,言不隐于荣华,然后可谓彬彬之君子矣。
此篇序首先定位文辞之作,不外言与事二项。又谓文辞之功用,首冠“圣王之为政”。冈白驹此种文章观点,悉自刘勰定义“圣贤书辞总称文章”之本旨而来。因此,冈氏主要凭据《文心》理论“政事”与“文艺”并行的观点,认同文质彬彬,与文武合一,左右为宜之道才是《文心雕龙》基本理论。由此而导引冈氏批评六朝文体务华弃实的弊病,主张述道言治才是文心“正论”。无疑地,冈氏此处用《诸子篇》“入道见志”的定义诠释《文心雕龙》此书。也因此之故,冈氏会将《文心雕龙》归入子部,当作子部著录。
考查刘勰其人及其学,必从学术源流加以探讨,必须参考文献目录学在学术归类如何由经子之学,转变为子集之分的学术史渐变过程,以及“经”即是“史”,而“史”亦“经”此说之“经史合观”论,早已经化为刘勰平生学术思想的主轴,并且做为刘勰文心的理论体系大纲。刘勰应用以上所言四部学术合观之史识,进行“镕铸经典”,以及“翔集子史”之论述,完成《文心雕龙》,原来就都是根据以上所述刘勰思想理论总纲导引出来的一贯论述。
一言以蔽之,《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而刘勰的身份根本就是一位彻头彻尾皆未变本质的“子学家”,《文心》所以曾经一度而降为“论文”之专书,弊端全出在后人之不详查,尤不能详读《文心》文本早已内涵子学之故也。因此,《文心》学界若要认真反省当前研究新一步进展,首先要辨明《文心》此书的子学内涵,重探刘勰一生学术思想的真实“本色”。
首先,不妨先参考纪昀的学术分类“集”部概念。纪昀《诗文评类》小序云: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憍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
纪昀此段话,正式定位《文心雕龙》一书为“诗文评”类,不但不视此书为六朝“文集”之古义,更无视于此书内含“子家自居”之自喻与暗示。纪昀的目的惟在为分而分“图书部目”要求,欲使学术流别判明,各家门户厘清。其有助于“寻目索书”之便固无可疑,但顾此而失彼,不能反映一家一门学问之“总体”及其“大道”,则乃文献目录湘川曲学之通病。难怪纪昀评点《文心雕龙》《史传》篇与《诸子》篇二文,颇有微词,认为二篇皆非刘勰专门本行,乃虚论凑数而已。
案《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虽《序志》篇已自白“言为文之用心”,但并非篇篇皆只谈文学。且刘勰自定文章定义为“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仅限后世诗文辞赋。故而《文心》一书有《宗经》篇、《征圣》篇、《史传》篇、《诸子》篇等,盖谓经史子莫不皆“文”也。本乎此,刘勰《文心》之作,实乃“文集”古义之书,非可但据后世经、史、子集四部归类此书为“集部”,更遑论纪昀必欲强设“诗文评”一类,而冠《文心》为首之作法殆为“为分而分”之目的。盖纪昀援后世“集”部之偏见,遂于《文心》一书之评点有过激之语,聊举如下:
1.评《征圣》篇云:此篇却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
2.评《宗经》篇云:本经术以为文,亦非六代文士所知。
3.评《史传》篇云: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
4.评《诸子》篇云:此亦泛述成篇,不见发明。盖子书之文,又各自一家,在此书原为谰入,故不能有所发挥。
细审以上四则纪批,凡是在集部之学以外,文心一书属于经史子三部之学的内容,纪昀一盖加以轻诋,没有好评。只因为纪昀一口咬定文心之作为“诗文评”,归类刘勰一生之学为“论文专家”,遂否定刘勰以“子家自居”之实,无心于六朝人私家著述之“文集”古义,更别说刘勰希圣希贤之心思,以及宗法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名山之志,纪昀大都视而不见,略而不谈。
案纪昀严分集部之学,又别设“诗文评”类以定位《文心雕龙》一书,其致误之由主要是:将刘勰其“人”与其“书”分开,孤立而论,不明刘勰其人一生志趣抱负,不外文章、政治二途,刘勰力主文武兼治,励德修业,唯待时而动,刘勰本不甘一生只落为文士而已。故而《文心雕龙》有《才略》篇、《程器》篇之作,畅述文武之道。又有《宗经》篇、《史传》篇、《诸子》篇之作,涉及经、史、子论之学。而全书理论大旨用《周易》之道为总纲,贯通全书。凡此皆展现刘勰“通经致用”之志,文论一以贯之的通儒之学。岂可拘于后世区区小论,只当集部书看?故若不明刘勰其“人”之学为何?即不能知其“书”大道本意为何?顺此而推,亦不能真知《文心雕龙》一书为何?
近儒刘永济精通刘勰《文心雕龙》此书著述性质,晚年已定论文心之作,非仅供文论分析而已,乃断言文心是一部“救世”之经典著作,归类文心此书是一部“诸子著述”。刘永济真可算是文心真知音,已能博通刘勰思想之奥妙。
其实刘勰之子论,在文心此书《诸子》篇已尽表之。此篇有三大子学见解,代表刘勰的思想史观。首先,文心《诸子》篇分子学为三时期:
其一,先秦时期。此期之子家作者皆能“自开户牖”,各立门派,故有儒、墨、名、法、道、阴阳、纵横家、杂家之门派,即所谓“诸子”之学。
其二,两汉时期。此时期虽有子家,但已由“家”转向“论”之倾向,然大抵仍归之子学,可惜已不再能像先秦自立门户,开创一家之学。《诸子》篇曰:“类多依采。”意谓两汉子书大多依循先秦之情采而已。
其三,魏晋时期。此时期乃刘勰最不肯定的子学衰落期,《诸子》篇不谈论此时期任何一家子书,只用了一句“充箱照轸”概述魏晋子学“滥竽充数”的卑劣无价值。
由以上所述可知刘勰的子学史只承认先秦时期“自开户牖”的创派学说,而先秦以下子家大多只是依采与沿袭而已。此一见解,非谓先秦以下无子学,刘勰本意在点明先秦以下之子学已逐渐分散为“论”体,对各家采用博观约取的方法,进行“折中”子学之路,已不可能再看到像先秦子家那样的门派学说论述,必然带着“杂糅兼综”的子家折中方法,现代学者钱穆《道家政治思想》一文畅述先秦思想流派当区分先秦与后世的不同,即颇近似刘勰的《诸子篇》看法。钱穆云:
又所谓儒墨道法诸家之分派,严格言之,此亦惟在先秦,略可有之耳。至于秦汉以下,此诸家思想,亦复相互融通,又成为浑沦之一新体,不再有严格之家派可分。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史,分期论述,较之分家分派,当更为适合也。
详此节谓先秦思想可以分流派,先秦以下就很难严格区分,与刘勰《诸子》篇谓先秦子学能自开户牖,而两汉子家“类多依采”之语暗合。盖刘勰之意谓两汉子家依先秦子书之情采而发论,然而已经不能明指是依采哪一家?故亦不能严格分出门派矣!当然钱穆的意思,与刘勰一样,不是否定先秦以下的思想义理,而是说先秦以下的子学早已走向融合先秦各家思想之潮流,不再限定于一门派。类似钱穆此种说法,吕思勉与章太炎也有相近之论,而章太炎更直接表明后世子学必然是“杂家”一途之倾向,直截了当点出刘勰《文心·诸子》篇“类多依采”与“充箱照轸”的必然现象与结果,由此可见刘勰的子学三期论启导后来学者之说很深。
既然刘勰表现如此精通的子学创见,由此推论,《文心雕龙》此书之性质不只是文论。韦政通在一场中国哲学史的讨论会上,说过《文心雕龙》是兼具文学与哲学的精彩著作,又说此书的思想方法也受佛教影响。韦政通云:
先秦诸子与经的关系,我们的研究也很少,以前方东美曾说过,中国只有断头的哲学史,好像先秦诸子是突然蹦出来的。先秦诸子的思想当然不是凭空而定,它与经的关系应有彻底的研究。中国哲学史与西洋哲学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西洋的哲学史与文学史的关系比较疏远,而中国的哲学史与文学史的关系则比较密切。中国很多大思想家本身就是文学家,文学史与哲学史有很大的重迭性,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譬如《文心雕龙》,主要是讲文学理论,其实它也是一部很精彩的哲学著作。刘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很深,他的理论主要得自佛学。中国文学与哲学的共同特质是什么?各家与文学的关系又如何?仔细研究,可使中国哲学史增加新的视野。
此一段韦氏谈话可分为两部分,前半段说经书与子书的必然关系,后半段则直接点明《文心雕龙》一书有文学也有哲学,用崭新的观点评价文心此书。其实韦氏这种见解,文学与思想不分,在文心此书的《诸子》篇早已谈过。《诸子》篇定义子家之学有两大内涵:其一是“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也”,这句清楚界定诸子之学是以“道”与“志”二项为主要课题。《诸子》篇又说诸子之学术渊源即“述道言治,枝条五经”,表示诸子的学问盖从“五经”而来,是五经义理的“分枝”。又《诸子》篇比较说明经与子其实没有出现的先后问题,只有思想内涵不同的差异。所以《诸子》篇谓:“圣贤并世,经子异流。”此句话表示圣贤经典与诸子著作并世而出,到后来才分成经与子两类,乃受到外在客观环境推波助澜的影响变成诸子与经学两大学术脉络。《诸子》篇此种看法,解释经与子的源流与性质异同,可以回答现代学者韦政通前揭的提问,所以说刘勰《文心·诸子》篇早于韦政通一千五百年即已注意到经子之学类比文学与思想的学术问题。
试看《文心》全书首立《原道》篇畅述天地人三才之道,乃根据《易经》太极之道,以及乾坤天地之心,发展《原道》的理论,建立“道”之文的说法,即韦氏讲《文心雕龙》此书有文学与哲学的双重内涵。
再如《征圣》、《宗经》、《正纬》三篇直接论述圣贤与经书、纬书之关系,皆为先秦两汉思想史必然要谈的主题,此三篇兼述哲学与文学,自不待辩。而《文心·诸子》更是直接谈论诸子百家之学,简直就是一部先秦两汉到魏晋的哲学史精论。仅次于《诸子》的《论说》也在辨正子家与“论家”的异同,说到“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曰论”,据此做为子与论之分,又用通达与一偏的标准界定两者之别,论点明白透显,皆属哲学范围的讨论。由此可知,《文心》此书确实如韦氏所说兼具文学与哲学,研究古代思想史不可略过《文心雕龙》此书,再次印证《文心》此书同时兼具文学与思想内涵。
其实韦氏用“文学”与“哲学”二词描述文心此书的双重性质,若不易理解,可改用古代学术“子”与“集”的概念加以推敲,立可知晓,盖刘勰文心之作,乃刘勰以“子家自居”之志,畅论“为文之用心”。易言之,即用子家研究集部之学。刘勰可谓兼子、集二家之学的通儒,而所谓古代之集就是现代学术的文学与哲学之谓也。
再看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此书于《程器》篇释义,率先发蒙此意,可谓刘勰知音之一例。刘永济云:
全篇文意,特为激昂,知舍人寄慨遥深,所谓发愤而作者也。乃后世视其书与文评诗话等类,使九原可作,其愤慨又当何如邪?
此节首明《程器》篇暗藏刘勰平生身世寄慨之语,用“激昂”形容之,又由此寄慨之语,推知《文心》此书乃刘勰“发愤而作”之书,此与司马迁自述《史记》乃发愤述作之旨同意。若然,《文心雕龙》与《史记》二书皆有“成一家之言”之志,近似刘勰《文心·诸子》篇定义子书“入道见志”之志向。本乎此解,刘永济提醒世人《文心》此书不可仅当作文评诗话一类的著作看,必须当作子书读。刘氏此言诚可谓发千古之秘,乃《文心》此书与刘勰学术思想的现代“知音”。兹述《文心雕龙·议对》篇内涵的“子学义理”,摘取片段,提示纲要,藉此“内证”方法,论证《文心》此书的真正本色。
《文心》文体论自《明诗》以下至《书记》等二十篇,所述文体皆内含子学。但刘勰论述各篇仍用子学“政事”与文人“文章”双重兼顾角度,阐释各项文体技巧与理论,故有“华实”并配之语,又有“文理”一词之主张,谓主于文,主于理。如此将政事与文章并行之观点,并无孰轻孰重之意。唯独有一篇曰《议对》则反是。其实质涵义刘勰明确表示此体写作统归“政事”为主,旨在论议“治术”与“政体”,偏重于文章之“事理”,绝不可“文浮于理”,甚至举杜钦的议对文为例,说杜钦议对文章佳处全在“治事”之简要具体与明白,刘勰斩钉截铁说他“不为文作”。此篇《议对》乃刘勰罕见的唯一单用子家“政治”观点界定文体,并且评述此体名家皆侧重在主“理”之论。《议对》篇全文采用子学“述道言治”之说,反对“舞笔弄文”之作,批判“穿凿附会”之理,完全用“子学”角度论述文章,代表刘勰以子领文最强烈态度的一篇文体论。《议对》篇云:
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熏桂之椟,郑人买椟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存于兹矣。
此节刘勰用“买椟还珠”之典故,比喻议对此种文体的可贵处在文章“事理”,将之类比做“真珠”之宝美。反而讲究文章修饰的文采修辞是“椟”,比喻做无用可弃之物。刘勰主张议对文体主“理”而略“文”之见解,由此显露无遗。故而刘勰又有下述一段强烈之口吻,批判“舞笔弄文”之作,不适用于议对此体。刘勰《议对》篇:
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
此节明示议对之文,当庭应对,陈述政体治术,悉以“事实”为据,严禁“穿凿附会”之游辞。可知刘勰规定议对文体主“理”为宗旨,批判在议对文章大作“舞文弄墨”之巧饰。刘勰文论一致口气偏主“理”而反“文”之论述,以上两节可谓文心全书最强烈语气之代表。此乃原原本本第一次反映刘勰用“子家”攻击“文家”之批判。
然而,更值得意会玩索之一节话,则在《议对篇》之结尾,刘勰大叹特叹当今之世,深懂“练治”与“工文”双重才学之士已“难矣哉”,因而“通才”之辈少之又少,乃感慨唯有子家“博明万事”之通才,始能做到政事与文章双重兼备之功。刘勰《议对篇》云:
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
此节真可谓是刘勰以“子家”自居的又一段自誓自表之宣言,可惜向来诠解文心此篇之学者大多忽略其深旨而不察刘勰此节所示子家自白意涵。今考此节先定位议对文章作用即在“王庭”之驳议,以政治事理为对谈之内容,此全属“政事文章”之一类,可无疑矣!而这种当庭驳难讨论事理之方法,绝非无学无才之“高谈”可辨,乃是深知“经权通变”博学才士始克胜任。盖唯有博学通才之士,才学俱优,翩翩风采,既能驳议论难“练治”之事理,出言成辞,也能引经据典,博古通今,做到“工文”之美对!必如此“政事”与“文章”双美兼擅“通才”之士,始能成功撰作“议对”文章。由此可见刘勰述《议对》篇文体之高超远志,雅有以此为标杆,舍我其谁属之大气魄,刘勰一句“难矣哉”之叹,深可揣摩,隐约之间已传达刘勰极有自负之远大抱负。《议对》篇“赞曰”总结此体是“治体”文,注重政治“名实”之义理,摒弃文章“摛辞”之工文,又再次表明刘勰重“理”轻“文”之观点。刘勰《议对》篇赞云:
议惟畴政,名实相课。断理必刚,摛辞无懦。对策王庭,同时酌和。治体高秉,雅谟远播。
兹据此赞,议对文章所要陈述的“治体”,到底涵盖哪些政治事务?以及此体涉及“治体”的哪些事理?勾划原文要义如下:
一、首先界定议对文章的“述道言治”之本质云:
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
二、至于议对文要在王庭陈述的“治事”内容项目,则有治水、外交、变法、军事、外寇、宗庙祭祀、诛罚、兵事校练、货殖以及宫闱妇女之事。《议对》篇云:
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宅揆之举,舜畴五人;三代所兴,询及刍荛。《春秋》释宋,鲁桓预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辩: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至如吾丘之驳挟弓,安国之辨匈奴,贾捐之之陈于珠崖,刘歆之辨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程晓之驳校事,司马芝之议货钱;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贾充之谥: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
三、再述议对之文,须备“博通古今”之学,须明“万事万物”之理,始能写出具有“文骨”与风格之议对文章。一言以蔽之,非有“子家”之才不足以应王庭之议对。《议对篇》云:
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
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
四、其次再补述议对之文所陈“治体”又有礼乐、兵术、贵农、法术等各项。而写作之纲领则提出“弃奇采正”之论,完全以“事理”之论辨为主体。《议对》篇云:
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佃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
五、《议对》篇分出“射策”与“对策”二项支流别体,而这两项次分类,仍不出“政治”之陈述。《议对》篇云:
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者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观晁氏之对,验古明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
六、次由上述两种支流文体,再举董仲舒与鲁丕、杜钦等名家为例,凡此诸家皆有“经学”内涵,以及“子家”身份。《议对》篇云:
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
七、《议对》篇有两段评论,首次看到刘勰用“政治”观点批判“舞笔弄文”之作,抬高“政事治术”的价值,贬低文辞浮华之弊,十足表现刘勰“述道言治”的子家本色,这是重新诠释《文心雕龙》此书的一个起点。《议对》篇云:
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
《议对》篇又云:
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
八、《议对》篇讨论驳议与对策(含射策)两种文体,讨论对象是“事”,讨论的内容标准是“理”,讨论的最高原则是“不离事而言理”。因此,《议对》篇最重要的理论概念就是拈出“事理”此词,而通篇自首至尾,用一个“理”字贯串之。文心全书只有此篇《议对》篇全篇用“理”字谈论文章,并将“理”字衍生出的“事理”、“情理”做为驳议与对策(包括射策)两种文体的写作准则,同时,也用有没有事理或情理品评议对文章的优劣高下。刘勰文论的主要纲领“情理”二字贯通在《议对》篇全文,而“情”与“理”的结合,恰恰正是子集合一这种学术内涵的代表特征。例如《议对》篇单用“理”字有两例,《议对》篇云: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
又云:
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熏桂之椟,郑人买椟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存于兹矣。
《议对》篇合言“事理”有三例,《议对》篇云:
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
又云:
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
三云:
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
以上“理”字单言与“事理”一词合言,皆以“理”为主轴,《议对》篇的文章理论至此可证已经援用“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曰论”的子学定义,悉本子家义理之学。但是,《议对》篇终究不能离“文辞”而言理,文辞亦必不能没有“情采”可言,《情采》篇所谓:“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此句“情采”合一论,十足说明了刘勰子中含文的学术内涵。故而《议对》篇最后仍然将情理与事理合参并观,展现刘勰最高境界的文章理论。《议对》篇云:
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
游志诚,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所专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