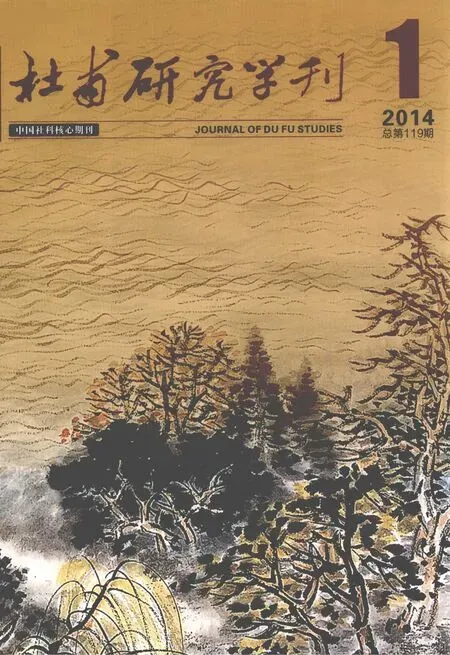唐宋巴蜀地区杜集整理略论
彭 燕
杜集的祖本,也是定本,为宋人王洙和王琪编订的《杜工部集》(二十卷)。王洙,字原叔。《杜工部集》最先由王洙于宝元二年(1039)十月编成,王洙编成后并未付诸刊刻,其本乃为家藏本。故周采泉先生《杜集书录》卷一“全集校刊笺注类”中,著录王洙编次的《杜工部集》“版本栏”付为阙如。周先生在《杜集书录》全集校刊笺注类中著录的第二个杜集本子为:《杜工部集》(二十卷本),宋王洙编次并记,宋王琪校刊并后记,宋裴煜校。宋嘉祐四年(1059)蜀人王琪以王洙编次的《杜工部集》为蓝本,聚古今诸集,会其友人,参而考之,三月乃成,遂镂其板,广为传布。我们今天所看到杜集的各种本子,皆从王洙、王琪本(亦称二王本)而来,后人在此基础上或增添、或辑佚、或注释、或编年、或分类、或分体、或正谬等等不一而足。
杜诗辑集,从晚唐,到五代,再到宋代,至蜀人王琪手中,杜集定本终得以最后形成。对杜诗的收集和整理,王洙的贡献是巨大的,而蜀人王琪对王洙《杜集》的校勘、整理、编订和刻印,对杜诗的流传、保存和研究的作用和功劳亦功不可没。张忠纲、赵睿才等编著的《杜集叙录》不再著录王洙编次《杜工部集》本子,而只著录二王本。后人认为王琪并不只是简单校勘和刻印王洙《杜工部集》,而是对其重新进行了编次、整理和修订。杜集定本在蜀人手中终得以完成并刻印流传,成为千年不移之祖本。据调查,唐宋时期,除王琪整理刊刻《杜工部集》(二十卷)外,较早参与杜集整理和研究的蜀人主要有六家,涉六种本子。
一、王洙《杜工部集》所参考的蜀中杜集
据《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和《玉海》,第一本《杜集》为杜甫亲自编订,为六十卷。后樊晃采其遗文二百九十篇,分六卷。这就是杜诗学史上通常所说的最早杜诗选本:《杜工部小集》(六卷),樊晃辑。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说:“杜集的编纂,最早不知何人,可考者起于唐樊晃。”胡可先所论似更为恰当。王洙《杜工部集记》云:“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可知,王洙《杜工部集》所参杜诗文献凡九种。查九种文献辑集时间,王洙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罗列。九种本子中,前五种为宋以前的杜集本,后四种为宋代杜集本。在这九种本子中,蜀中本子有三种。其中,宋以前有二种;宋以后有一种。可见,王洙在编订《杜工部集》时对蜀本的重视,从中亦可管窥当时蜀中整理研究杜诗之风气和成就。置古本于首,当为唐本,二卷古本,应不是全集。蜀人辑《蜀本杜诗》位置仅次于古本,其年代应该是早于樊晃《杜工部小集》,晚于二卷古本。古本二卷杜诗和樊晃《杜工部小集》一样,极有可能是杜诗选本,而非全集本。除《杜甫集》(六十卷)外,现在基本可以肯定宋以前的杜诗全集本有两种:《蜀本杜诗》二十卷、蜀人孙光宪编《杜甫集》二十卷。宋以前的杜诗文献,据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焦裕银等《杜集书目提要》和张忠纲、赵睿才等《杜集叙录》等书目,知有14种,除已佚的《杜甫集》(六十卷)和樊晃《杜工部小集》外,有:二十卷本二种,皆为蜀人所编;写本二种,为《唐写本杜诗》、《吴越写本杜诗》,佚;日本《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著录《杜员外集》,二卷;后晋官本《杜集》卷数不详,已佚。为冯道主刻《九经》后,最早官刻本;疑为抄本的有三种,为《南唐抄本杜甫诗》、《杜员外诗集》和《旧抄本杜少陵诗》,佚;还有《杜氏诗律诗格》(一卷),及《杜甫集略》(十五卷),二书皆佚。据上可知,目前可考宋以前杜诗文献中,蜀中全集本有二种。
(一)蜀中杜集三种
1.《蜀本杜诗》,二十卷,蜀人辑,姓氏不详,五代本
《蜀本杜诗》(二十卷),周采泉《杜集书录》著录为《杜甫集》二十卷。题下按语为:“拟名。亦称旧蜀本。”并认为:“严羽之称旧蜀本者,以别后来郭知达所刻之蜀本《九家注》而言。”王洙《杜工部集记》云:“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云:“旧蜀本杜诗,并无注释,虽编年而不分古近二体,其间略有公自注而已。今豫章库本,以为翻镇江蜀本,虽无杂注,又分古律,其编年亦且不同。近宝庆间,南海漕台雕《杜集》(指曾噩刊刻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亦以为蜀本,虽删去假坡之注,亦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赵注(指赵次公注)比他本最详,皆非旧蜀本也。”郭绍虞笺注云:“案镇江蜀本既与旧蜀本不同,疑即是王洙所编、而王琪所刻、裴煜所补之本。其与旧蜀本不同之点有二: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谓:‘王洙原叔定其千四百五篇,古诗三百九十九,近体千有六。’则是此本虽无注而分体,与沧浪之说正同。又云:‘蜀本大略同,而以遗文入正集中,则非其旧也。’则知旧蜀本遗文不入正集,是又与新蜀本不同之一点。”蜀本杜集二十卷有新旧蜀本之分,王洙所用之本,当为旧蜀本。后蜀韦彀《才调集叙》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各有编次。”是当时杜集已在蜀地流传。则此本或为五代后蜀时刊印,已佚。周采泉先生疑其版本为五代或宋初四川刻本。
2.孙光宪《杜甫集》二十卷五代本
孙光宪,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资阳)人。后唐天成元年(926),为荆南高季兴掌书记。历三世,累官荆南节度副使。入宋,授黄州刺史。为政颇有治声。光宪博通经史,尤勤学,聚书数千卷,抄写雠校,老而不废。著述甚丰,今传有《北梦琐言》。能诗工词,为“花间派”词人。《宋史》卷四八三有传。王洙《杜工部集记》:“孙光宪序二十卷”,惜书与序皆不传。王洙后记径称“孙光宪序二十卷”,则光宪所整理、编订的杜诗并没有固定之名,周采泉《杜集书录》著录为《少陵集》二十卷,其在题名下按语云:“此为拟名,或径称《杜甫集》亦为可知也。”张忠纲、赵睿才《杜集叙录》著录该书时,则径称其为《杜甫集》。今从张、赵二先生《杜集叙录》,称光宪编订杜集为《杜甫集》。光宪《杜甫集》是其在荆南时所整理编订,作为蜀人,光宪必定知道蜀中流传的杜集,从后蜀韦榖《才调集叙》所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各有编次”可知,当时蜀中李白和杜甫的诗集已经流传。此本极有可能就是前面我们谈到的五代时蜀人整理、编次的蜀本二十卷杜诗。周采泉先生认为严羽称其为旧蜀本,是为有别于二王本杜集和杜注蜀本《九家集注杜诗》而言。蜀人光宪博通经史,勤学,工诗,富藏书,不可能不知晓蜀中有此本杜集流传,此本杜集有可能还是他“聚书千卷”之一,亦未尝可知。有一点我们基本上可以明确:光宪整理、编次二十卷杜诗时,必定参考和借鉴了旧蜀本二十卷杜诗的某些经验和成果。以二十卷编次,就是其中之一。
3.郑文宝编、张逸序刊《少陵集》二十卷宋本
据王洙后记,其编订《杜工部集》(二十卷)所参考之文献,宋以后与蜀地有关的是郑文宝编、张逸序刊的《少陵集》二十卷本。郑文宝(953—1013),字仲贤,又字伯玉。宋汀州宁化(今属福建)人,文宝父仕南唐,初文宝亦仕南唐,以荫授奉礼郎,迁校书郎。入宋,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除修武主薄。曾知梓州(今四川三台)录事参军事,转光禄寺丞。官终兵部员外郎。善篆书,能诗,著有《江表志》、《南唐近事》、《谈苑》等。《宋史》卷二七七有传。《竹庄诗话》卷十六郑文宝《爽约》诗注引《诗事》载:“欧公云:‘文宝诗如王维、杜甫’”。文宝编《少陵集》二十卷,已佚。王洙后记有:“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
王得臣《增注杜工部诗序》:“按郑文宝序《少陵集》,张逸为之序。又有蜀本十卷……”“又有蜀本十卷”,陈尚君以为此“蜀本”谓五代蜀人辑《蜀本杜诗》(二十卷),认为“十卷”非是,应为“二十卷”。胡可先认为此“蜀本十卷”,“或原刻与张逸所刻卷数不同”。而周采泉先生则以为此“蜀本”就是指张逸序刊的郑文宝所编的《少陵集》,周先生在《杜集书录》按语道:“岂张逸序刻之蜀本仅为十卷耶?郑、张两序均不传,仅知其为白文本。”张逸,真宗、仁宗时人,生卒年不详,字大隐,郑州荥阳(今河南荥阳)人。进士及第。天圣二年(1024)、三年、四年为益州路提点刑狱。景祐四年(1037)、五年,宝元二年(1039)、三年知益州,卒于官。《宋史·艺文八》著录有张逸、杨锷《潼川唱和集》一卷。《宋史》卷三〇一有传。万曼《杜集叙录》认为此本为南唐本,陈尚君先生疑其有误,认为此本当为宋初本。其后的周采泉、张忠纲、赵睿才等均采用宋本说。王得臣“又有蜀本十卷”不知其究竟所指为何,十卷蜀本,难道是蜀中流传的另外一种不见诸于诸家著录的又一蜀本?或者谓五代蜀人《蜀本杜诗》二十卷本?或者谓郑文宝编、张逸序刊《少陵集》二十卷蜀本?文宝和张逸的书、序皆佚,一切皆不可考。
(二)蜀中杜集的几个问题
1.二十卷本的杜诗篇目。
宋人王洙《杜工部集后记》云:“蜀本二十卷”,宋人王得臣《增注杜工部诗集序》中评郑文宝编、张逸序《少陵集》后,又云“有蜀本十卷”,陈尚君疑此论有误,认为《蜀本杜诗》非仅十卷。而王钦若《王氏谈录》“修书”条:“杜甫诗”下注云:“古六十卷,今亡。世传二十卷只数百篇。参合别本,以岁时为类,得编二十卷。”王氏的“世传二十卷只数百篇”一语,值得我们思考。古人编书分卷有一定的标准,一般来说是依每卷内容多少而定。故现在我们据古人的分卷法,即使古书已佚,但如果知道其卷数,我们还是大致可以推算出该书当初内容的规模。陈尚君依据六种基本保持原貌的唐人诗集分卷的内容承载量,取每卷编次诗歌在四十首到七十首之间。聂巧平博士据二王本每卷诗歌的数目,取其每卷诗歌数目为七十首。二人所得标准皆有一定依据,都讲得通。如果我们取陈尚君的唐人分卷标准的最低值四十首,“二十卷本”载杜诗当为八百首;如果取其中间数五十五首,那么“二十卷本”载杜诗当在一千一百首,这个数目基本上接近现在流传下来的一千四百余首的杜诗数目了。如果我们取聂巧平博士依二王本每卷七十首的分卷标准(亦即陈尚君的唐人分卷标准的最高值),则“二十卷本”所载杜诗篇目则为一千四百首,若此推论成立,基本可以肯定此本就是二王本当初整理、编订依据的主要蓝本。故“世传二十卷只数百篇”,可能当事人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完本。王氏“世传二十卷只数百篇”语中一个“只”字,实已经透露了个中些许消息,王氏自己也认为“数百篇”远远少于了“二十卷本”本来应该有的诗歌数目。究其原因,则语焉未详。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是“世传二十卷本”当不会在八百篇以下,或有一千篇,或有一千四百余篇,或者更多。无论如何,当初所传的二十卷本所载杜诗篇目,已大致接近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定本《杜工部集》的模样了。
2.蜀中杜集“二十卷本”现象
关于二十卷蜀本杜集,前人分别多有讨论。蜀中杜集,皆为二十卷本,包括后来成为定本的《杜工部集》,也是二十卷。在二王编订《杜工部集》之前,除了宋以前的两种二十卷本外,还有一个二十卷本,即宋初郑文宝编、张逸序《少陵集》二十卷。此本为多次至蜀,知益州的枢密直学士张逸在蜀中刊刻的,亦称蜀本。当然,“二十卷本”特指蜀人所编订的杜集本子的卷数。二王之前,可考二十卷本杜诗只此三本,其中二种为蜀刻本,一种为蜀人所辑本。皆与蜀地有关。蜀中整理、编次杜集通为二十卷本,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笔者以为,蜀中二十卷本在不同的时期反复出现,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的问题,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蜀中杜集每一次的整理、编辑、辑集都会参考、因袭和继承了乡人们整理、编订杜诗的成果。如此,就形成了在不同的时期,蜀中杜集皆以二十卷本形式反复出现的现象。
3.新旧《蜀本杜诗》
据严羽《沧浪诗话·考证》和郭绍虞笺注,可知,蜀本杜集在宋时已经有新旧蜀本之分,而王洙所用之本为旧蜀本。《九家集注杜诗》为注杜蜀本,不在我们讨论之中。白文本的蜀本杜集除二王本外有二个本子,一五代蜀人编订《蜀本杜诗》(二十卷)本;二为郑文宝编、张逸序刊的《少陵集》(二十卷)本。严氏、郭氏皆以为二王本和注杜蜀本《九家集注杜诗》皆非旧蜀本,原因有:旧蜀本不分体;亦无注;编年与二王本不同;遗文不入正集,诗文分刊。所谓旧蜀本,目前学界皆疑其为五代蜀人所编《蜀本杜诗》(二十卷本)。当然,也有可能是郑文宝编、张逸序刊的《少陵集》(二十卷本)。目前为止,学界似乎还未有定论。
从上述关于蜀中二十卷杜集的几个小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蜀中治杜之风气可谓由来已久,源远流长。蜀人对杜诗的整理研究,是后世杜诗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如果没有蜀人如此用功、用力地收集、整理和编订杜诗,后世的研究工作可能就无从谈起。
以上,为王洙后记中所提到的三种蜀中二十卷杜集的大致情况。
二、宋代蜀中其它杜集
入宋后,蜀中收集、整理和编撰杜集的风气更盛。除了上面我们已论及到的郑文宝编、张逸序刊《少陵集》(二十卷)和杜集定本二王本两个本子外,搜集、整理和编次杜诗的还有蜀人王著、苏舜钦、何南仲等。
(一)王著《手写杜诗》(一卷)
王著,字知微,蜀中成都人。唐王方庆孙。世家京兆渭南(今属陕西),祖从唐僖宗入蜀,遂为成都人。现存王著《手写杜诗》一卷,系残卷。书杜诗五律三十六首,共二百行,每行八九字不等。旧藏丹徒包山甫家,后归霍邱裴景福,现不知尚存否。近人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三有著录,有跋。周采泉先生以为蜀人王著《手写杜诗》(一卷)与蜀本杜诗有关,极有可能是王著手书当时所流传蜀本杜诗中的部分内容而成。《杜集书录》因其不全,但考虑其在杜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将其列为选辑之冠冕。此卷可做杜诗校勘用。
(二)苏舜钦编《老杜别集》
苏舜钦,天圣进士,因慕杜甫故字子美。宋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生于开封(今属河南)。易简孙。《老杜别集》未见公私书目著录。其收诗三百八十余首,书不传,而题后存。此本辑于景祐年间,早于王洙所编《杜工部集》二十卷。舜钦对杜诗极力推崇,长期收集和整理杜诗,对杜甫的人格气节也是十分敬仰。在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盛行的宋初文坛上,独蜀人舜钦不尚世风,不随潮流,四处搜集、整理和编次杜诗,并大力学杜、尊杜,在宋代杜诗学史上,无疑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舜钦尊杜可谓“宋初一人”而已。
(三)何南仲《分类杜诗》
何南仲,蜀人,进士。与张耒、邓忠诚、晁补之等有唱和。南仲《分类杜诗》,公私书目未见著录。李石《方舟集》存序,书不传。此书编次体例为分类,分体标准,依杜诗之变。周采泉先生亦认为:“杜诗如此分类,向所未有。”的确,以诗变分体,从古到今,为南仲此一书而已。
宋代蜀人对杜诗的搜集、整理、辑集在杜诗学史上影响较大的几家大致如上。
三、宋代蜀人杜诗辑佚
王琪聚集古今诸集重新校定、整理、编次王洙《杜工部集》后,在刻印时,把裴煜所辑得的佚文佚诗作为“补遗”附于集后。“补遗”包括杜甫佚诗五首,佚文四篇,凡九篇。宋代杜诗杜文的辑佚由裴煜始,然蜀人王琪载籍“补遗”也功不可没。裴煜,字如晦。宋临川(今属江西)人,郡望河东。庆历六年(1046)进士。嘉祐二年(1057)知吴江县。五年,仁宗命为《新唐书》校勘官。官终翰林学士。裴煜任吴江知县时,协助王琪编刊《杜工部集》,搜集杜甫佚诗、佚文凡九篇,作为“补遗”刊附集后。《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杜工部集》二十卷”条云:“王琪君玉嘉祐中刻之姑苏,且为后记,……又有遗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宋代共辑得杜甫佚诗五十一首,其中有五首已入正集,今已不辨。余四十六首于诸本所录,还可辨认。关于杜甫佚诗,宋时已有人表示不足为训,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诗话》云:
世所传《千注杜诗》,其间有曰“新添”者四十余篇,吾舅周君德卿尝辨之云:唯《瞿塘怀古》、《呀鹘行》、《送刘仆射》、《惜别行》为杜无疑,其余皆非真本,盖后人依仿而作,欲窃盗以欺世者。……其中一二虽稍平易,亦不免磋跌。至于《逃难》、《解忧》、《送崔都水》,《闻惠子过东溪》、《巴西观涨及呈窦使君》等,尤为无状。……吾舅自幼为诗,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尝与予语及“新添”之诗,则颦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无几矣,然谛视之,未有不差殊者。诗至少陵,他人岂得而乱之哉?”公之持论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顾我辈未之见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王若虚借其舅周君德卿语,认为当时辑得的杜甫佚诗四十余篇,只有四篇为杜无疑,至于其他,皆非真本。周紫芝《竹坡诗话》说当时士大夫家藏《杜少陵逸诗》刻本不同,而好事者以此流传,而以假乱真。一概否定或轻易抹灭宋人所辑得佚诗的态度亦过于极端。《杜甫集》六十卷,其散失、亡佚是很严重的,二王定本搜罗远非完备,二十卷《杜工部集》仅为杜诗的三分之一而已。周紫芝《竹坡诗话》云其收杜甫佚诗有二十八首,王直方更云自得杜甫佚诗有二十九首。杜甫佚诗的收集,自裴煜后,蜀人员安宇辑得佚诗有二十七首,这是从宋代到目前为止,杜甫佚诗辑得最多的一次。后诸家虽各自声称其所搜集佚诗数目,实际相互重复较多。周紫芝、王直方所收佚诗,均大致不出员安宇所搜范围。至清代,仇兆鳌云又得佚诗六首,然今天学人认为其以贪多为目的而未尽可信,洪业《杜诗引得》称:“仇兆鳌虽续有所辑,然或一联半首,或鬼语梦句,或明知其不为甫诗而尚载之,无足取也。”清以后,唯复旦大学陈尚君辑得杜甫佚诗一首。
员安宇,据南宋蜀人员兴宗《九华集》卷二十一《员公墓志铭》可知,安宇,神宗朝人,今四川仁寿人,皇祐进士,累官朝奉大夫知眉州。安宇为员兴宗本家长辈,官至屯田员外郎,与乡人苏洵、文同交甚厚。员兴宗,字显道,号九华子,早年读书九华山,高宗绍兴二十七年进士,孝宗时累官至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有《九华集》五十卷,佚,今辑存有二十五卷。员兴宗诗歌创作不多,大都饱含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员安宇、员兴宗二人对杜甫的崇敬和对杜诗的喜爱表现形式不同。现辑得员兴宗《九华集》有论杜三条,其景仰之情无不溢于其间。员安宇对杜甫的推崇则表现在用功辑杜甫佚诗方面。员安宇所辑得佚诗二十七首,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有收录。另外,蜀人赵次公、郭知达也各自辑得杜甫佚诗一首。宋代蜀人所辑得杜甫佚诗共二十九首。裴煜辑、蜀人王琪收录杜甫佚诗又五首。《过洞庭湖》佚诗,据《潘子真诗话》,蜀本有收入。整个宋代三十五首杜甫佚诗,因蜀人之功得以保存而流传至今。蜀人在杜集的整理和完备过程中,可谓居功至大,贡献卓越。宋人辑杜甫佚诗具体情况如下:
裴煜五首:《瞿塘怀古》、《送司马入京》、《呀鹘行》、《惜别行送刘仆射》、《狂歌行赠四史》
王原叔本三首:《送王侍御往东川》、《惠义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军中醉歌寄沈八》
陈浩然本二首:《楼上》、《杜鹃行》
吴若本七首:《闻惠二过东溪》、《过洞庭湖》、《李监宅二首之一》、《长吟》、《绝句三首》(其一《闻道巴山里》;其二《水槛温江口》;其三《谩道春来好》)
赵次公一首:《避地》
郭知达本一首:《汉州王大录事宅作》
员安宇二十七首:《客旧馆》、《遣闷戏呈路曹长》、《逃难》、《寄高适》、《送灵州李判官》、《与严二归奉礼别》、《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二首之二》、《又呈窦使君》、《遣忧》、《早发》、《巴山》、《收京》、《巴西闻收京送班马入京》、《花底》、《柳边》、《送窦九归成都》、《赠裴南部》、《送崔都水下峡》、《随章留后新亭会送诸君》、《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愁坐》、《阆州送二十四舅赴青城》、《陪严郑公秋晚北池临眺》、《去蜀》、《放船》、《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虢国夫人》
以上可以看出,定本杜集形成后,蜀人在完善杜集方面依然用功很多。从宋人搜集杜甫佚诗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从致力于搜集杜甫佚诗的士人数量,还是从搜集杜甫佚诗的成就来看,蜀地均遥遥领先。蜀中较全国其它地区,尤重对杜集的搜集、整理、编纂以及对杜集的完善等工作。这种情形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自古蜀人就有好文的传统,蜀人历来就具有开放、包容和热情的特点,杜甫一生最安宁、最幸福的生活在蜀中度过,杜甫诗歌创作艺术亦成熟于蜀中,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蜀人对杜甫有强烈的认同感,并以杜甫曾寓居过蜀中为幸。全国杜甫草堂有九处,目前保存得最完好的杜甫草堂、全国最早成立的杜甫研究学会、全国唯一的杜甫研究专刊《杜甫研究学刊》均在蜀中。蜀中传统,无论是本地之蜀人,还是入蜀之外乡人,但凡身在蜀中,皆会加入到学杜、研杜的队伍中来。正如张秀熟在《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一九八一年一月的创刊辞中讲到:“杜甫一生,在蜀中流寓最久;杜甫诗篇,亦以在蜀为盛。寓成都有草堂,寓夔府亦有草堂,蜀已成为工部第二故乡,离夔东下,犹时想念。工部垂老不忘蜀,蜀之人亦永不忘工部,海内外有客来蜀,亦未尝不欲一游草堂;甚至谈蜀必侈谈工部,谈工部必想望蜀,蜀之名已与工部之名相联系,相互照耀于史册。”
注释:
①本文中的杜集,主要是指白文本杜集。
②张忠纲、赵睿才等编《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第2页。
③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④九十九卷数与后括号内九个本子卷数之和有出入,不知是王洙过录各家本子卷数有误,抑或是计算卷数有误,或者是后来刻印错误,皆不知晓。
⑤⑦⑮《宋本杜工部集》(《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
⑥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90页。
⑧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第703页。
⑨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91页。
⑩文中所指的蜀人有两种,一为巴蜀籍贯蜀人;二为入蜀为官且对杜集的整理和研究影响较大者。
⑪何汶《竹庄诗话》卷十六,《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诗文评类),商务印务馆1987年铅印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⑫⑯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2244页。
⑬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杜诗学通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⑭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92页。
⑰王钦若《王氏谈录》,《四库全书》(集部·杂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62册第586页。
⑱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96页。
⑲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1937年)。
⑳据聂巧平《宋代杜诗辑佚》可知,黎庶昌《续古逸丛书》本《杜工部集》有诗1423首,其中古体诗409首,近体诗1001首,除所收他人诗13首(李邕1首,卷一;高适2首,卷8、卷11;岑参2首,卷10;王维1首,卷10;贾至1首,卷10;严武3首,卷12、卷13;韦迢2首,卷18;郭受1首,卷18)和裴煜5首外,有诗1405首;而二王本《杜工部集》有诗1405首,其中古体诗399首,近体诗1006首。二本对勘结果为:《续古逸丛书》本《杜工部集》较二王本多收古体诗10首,少收近体诗5首,即全集多收诗有5首。疑为后人翻刻时补入正集,现已不可辨认。
㉑丁福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506页。
㉒洪业《杜诗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页。
㉓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有“拾遗”一卷,收录有裴煜、陈浩然、员安宇、卞圆、吴若等所搜逸诗四十五首。另有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辑得逸诗一首,不见诸于他本。
㉔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引《潘子真诗话》。
㉕据复旦大学1998年聂巧平博士学位论文《宋代杜诗学》。
㉖据宋人曾季貍《艇斋诗话》和潘淳《诗话补遗》,《军中醉歌寄沈八》为畅当作品;《全唐诗》卷二三四著录《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为杜甫作,题下注:“一作畅当诗”,同书卷二八七畅当诗亦收入,题下注:“一作杜甫诗”。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引宋人彭叔夏《文苑英华辨析》辨析此诗后云:“非甫作也”。今人胡可先以为此诗当为畅当作,而非杜甫也。
㉗《全唐诗》卷二三四著录《杜鹃行》为杜甫作,题下注:“一作司空曙诗。”同书卷二九三司空曙诗卷亦收入,题下注:“一作杜甫诗。”宋人彭叔夏《文苑英华辨析》卷六(名氏)、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九皆两存未决。杨伦《杜诗镜铨》卷二十引李子德云:“当是司空曙作。”今人胡可先认为杜甫已有《杜鹃行》一首,《全唐诗》卷二一九收入,疑卷二三四《杜鹃行》为司空曙诗,而《文苑英华》连类收入,故难定作者。
㉘《过洞庭湖》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三引《王直方诗话》云:“……,此老杜《过洞庭》诗也。李希云:‘得之江心一小石刻’。”;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引《潘子真诗话》云:“元丰中,有人得此诗刻于洞庭湖中,不载名氏,以示山谷。山谷曰:‘此子美作也’今蜀本收入。大历四年夏,公在潭州。此当是五年夏自衡州回棹,重过洞庭而作。”今人吴企明《唐音质疑录》(《杜甫诗辨伪札记》认为此诗非杜甫作。可参。)
㉙《避地》诗,赵次公注乙帜卷三(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乙帜卷八)有《避地》一诗,严羽《沧浪诗话·考证》:“少陵有逸诗《避地》一首云……,此则真少陵语也,今书市集本并不见有。”今人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云:“诸注叙时间准确到月日,王洙、王琪是不可能臆加的,显然出于杜甫之手。”莫砺锋《论宋人校勘杜诗的成就及影响》文赞同陈尚君说,并认为宋人的判断(断为杜甫作)可谓卓识。今人吴企明《唐音质疑录》(《杜甫诗辨伪札记》认为此诗非杜甫作。可参。)
㉚《全唐诗》卷二三四著录《虢国夫人》为杜甫作,题下注:“一作张祜《集灵台》二首之一。”同书卷五一一张祜诗卷收其在《集灵台》二首之二,题下注:“此篇一作杜甫诗。”此诗据朱鹤龄注见《草堂逸诗》。南宋蜀刻本《张承吉文集》卷五收《集灵台》二首之二,题下注:“又云杜甫,非也。”宋楼鈅、清施鸿保皆认为此诗非杜甫作。今人胡可先、吴企明也以为此诗非杜甫作,而为张祜作品。
㉛张忠纲等编《杜甫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第460页—461页。
㉜张秀熟《发刊辞》,《草堂》(创刊号),1981年1月。
——评王新芳、孙微《杜诗文献学史研究》
——以宋代蜀人三家杜诗注辑录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