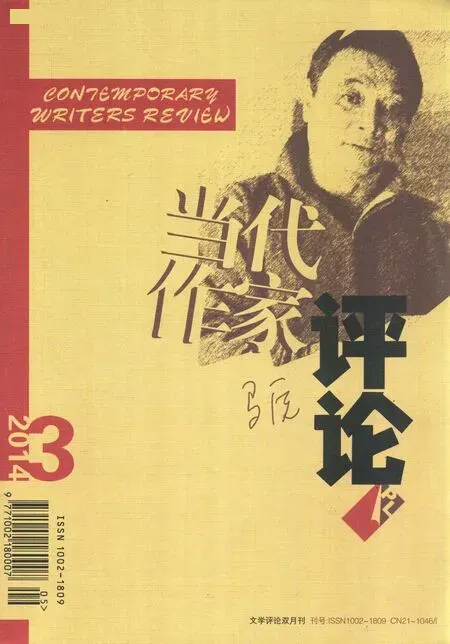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几点看法
葛浩文 (潘佳宁译)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将来临,文学翻译依旧前途未卜。马丁·阿诺德(Martin Arnold)在《纽约时报》(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八日)上写道:“总的来说,外国译著在美国的销售,就像一瓶所剩无几的剃须膏,只有一点儿空气和泡沫。”
到一九九〇年为止,在各国外文译著总数中,法国接近10%,意大利超过25%,美国不到3%,中国尚无数据。美国每年出版图书近二十万种,其中译著仅占3%左右。要是把视线转向小说和诗歌,那比例就会缩减到0.7%左右。这些数据说明,英语作品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但同时也让我们想到,美国的文化排外心理依旧存在,而且相当盛行。
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国作家要获得他们应有的关注,哪怕是些许的关注,那么选择作品的标准就至为重要了,比如,介绍谁,翻译什么,何时介绍,何时翻译。不然的话,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要进入西方文学主流,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米兰·昆德拉及奥克塔维奥·帕斯等人比肩,就是不可能的。
如果没有一批题材宽泛、技巧出众的中国小说和诗歌的英译本,中国作品很难在艺术上感染西方作家。在这方面译者大有作为。不过,在我们开始考察翻译作品的种种特色及其成因之前,我们有必要花点时间,先泛泛地讨论讨论文学翻译之外的几个话题。评论家雷金庆(Kam Louie)撰文研究新近出版的英译中国小说,他在文中引用了中国著名小说家刘索拉的话,刘索拉同意“那个流行的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欣赏中国文学——无论外国译者技巧如何娴熟,他们仍然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作品,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抗战或改革开放”。她发牢骚说,“这个世界严重西化,凡事都要以‘欧洲标准’或‘美国标准’来评断。”她的话表达了“一些中国作家的无所适从,他们的作品在国外为何总是迟迟不被承认”。对刘索拉来说,这番话也许不大合身。对于她的无所适从,我表示同情——谁又能不同情呢?——但是对于她所谓“中西文化不可传递”的说法,雷金庆和我都不敢苟同。刘索拉显然否定了想象力的作用。抛开这点不论,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民族特殊性/本土特质与人类普遍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尽管“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充满了经济的,乃至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色彩,但是过分片面地强调各自的文化,又何尝没有一种东方主义或偶尔与之相对的西方主义味道呢?还有,刘索拉的论点很容易让人尴尬地联想到年龄、性别、阶层等方面的限制。如果文学想继续承担“文化交流”的责任,那些限制就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毋庸置疑,翻译作品的性质和质量,对跨语言传播/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至关重要。只有最好的译文和最坏的译文才能高低立判,其他要靠主观定夺,所以不讨论译文质量。毋庸赘言,忠实性(准确)、理解性和文学性等要素能确定译文的高下。另一方面,译者的目的和方法也容易确定。一些翻译评论家和实践者强调,译者的责任是将读者送到原著作者面前,而不是相反。在他们那里,异化的文本(姑且称之为直译)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上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一部可以轻易打乱目的语语码的作品,这就与归化(意译)的译本有所不同,归化的译本是在借用外国文化,但读者的语言又与原文不同,所以无法表现原文的风格特点。
“意译”派在出版方面更胜一筹,因为无论是商业出版社还是大学出版社都推崇意译派的译著。对此无论我们是庆幸也好,悲伤也罢,事实依旧是,在那些“可译的”小说里,“可读性好”的译作才能出版。
那么,当代中国小说的英语读者都在读什么呢?为回答这个问题,请允许我说说我自己作为一名译者的经验。我要重点讨论我最近翻译的三部小说,这三部作品各不相同。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陆续翻译了近五十部中国现当代小说。尽管这些译著不能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学的所有变化,但足以体现我个人的文学品位,我在翻译上的取舍,乃至中国长短篇小说的精髓,英译读者对此已经有所接触。
当代文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文革”后的那些早期作品,以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为题材,但与建国后统治文坛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没有多大不同。作品尚无质的飞跃,虽然作品中对性、对作家独立写作、对党和政府评头品足所采取的更自由的态度,已经开始谨慎地显现出来。
等到那些童年或少年时代经历“文革”的一代作家成长起来,写作的性质才发生了大的改变。这批作家从中国(城市)初显的国际主义氛围中汲取智慧和灵感,创作出不仅让国内的读者,也让我们外国人怦然心动的作品,我们这些外国人出于职业上的原因,也曾不知不觉地将自己视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支持者。
后邓小平时代进入后现代,文学创作的方向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至少在拥有写作才能、进行实验创作、又自我专注的青年男女作家那里是如此。在他们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中,个人视角取代了国家政策,写作形式越来越趋于唯我至上(有时也称作“为艺术而艺术”)。不必感到意外,这种写法是悲观的、虚无的,乃至变态的,但与西方读者正相呼应。
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在我看来,要者有三:一、改变长期以来对中国虚幻的、异域的看法(同时也降低了对我们曾经熟知的实证主义写作手法的宽容度);二、全球性世纪末焦虑(体现在中国近期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和社会行为上);三、对于世界终将充满暴力的恐惧。
英语中出现的最让人不安的中国作品充满了对恐怖暴力的刻画,文字与挽歌不相上下。一位评论家对短篇小说家余华的评论,用在众多其他中国作家身上也很合适:“行走在他的小说中,要经历一个又一个对死亡、肢解、乱行以及无端暴虐的恐怖描写。”
杂芜的故事情节讲述的是超乎想象的暴虐,其中不乏象征手法,往往又没有时间、地点、人物等传统写作标记——这些吸纳了普世感的故事使其中麻木的暴力平添了不折不扣的转喻色彩。充满杀戮的小说表面上“与批判文革的不人道行径相契合”,然而,“在老一代作家和批评家那里,却成了旁门左道,因为在他们那里,暴力是历史的政治行为和症状,尽管是非理性的。对那场历史创伤的幸存者来说,将暴力作为美学形式表现出来,之后毫无顾忌地消费,是不可想象的,自然也是彻头彻尾的亵渎”。不过,这一个个充斥着堕落和兽行的幽闭恐怖症的世界(与波兰作家舒尔茨〔Bruno Schulz〕的世界相同,这位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遇难),能概括王德威(David Wang)所谓的“走近惊奇。让世界变成充满奇幻与惊诧元素的王国,或者让乖戾与疯狂变得司空见惯,作家借此要把读者从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惰性中唤醒,引领他们进入一种全新的现实。”
苏童的小说《米》,名字波澜不惊,但其中的暴力和邪恶借用凡是可能的转喻手法,对恐怖娓娓道来,这方面其他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比。
小说写一个坏透腔的家伙,在其堕落自毁的一生中,腐蚀(或杀害)接触到的每个人,描写了(战前)中国自我毁灭的社会,在很多评论家看来,那也是个反人性氛围弥漫的当代社会。《米》是一部阴暗的、令人麻木的乃至大逆不道的作品,虽然其中夸张的荒诞描写比比皆是,但依然使人信服。一位评论家曾经这样发问:“为什么还有人读这本书呢?”她自己的回答颇有见地:“因为苏童对人物刻画得太生动,对我们来说,他们有着别人没有的个性。即使这些人物恨透了女人,也能告诉我们,他们每个人是多么冥顽不化,内心恐惧,时时戒备。因为当我们读到坏人倒了霉的时候,我们也感同身受,这使我们有了人性。”苏童的这部长篇和多部短篇,把中国的历史——又借助暗指,旁及当下——写得一片漆黑。
说到作品内容“不健康”的作家,要数莫言了。莫言曾是解放军的一名文化干事。在《红高粱》中,莫言将土匪、通奸犯、杀人犯、反党分子塑造成令人同情的英雄人物。在其政治色彩鲜明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里,莫言呈现了中国农民和政府之间不稳定的乃至对抗性的关系。而在《丰乳肥臀》中,莫言的视线锁定在性爱、政治和中国那令人胆战心惊的现代史上,后者与《红高粱》如出一辙。上述作品各自与众不同,但哪一部也不能与《酒国》相比,《酒国》可能是本世纪中国最令人震惊的文学作品。《酒国》这部多层面的作品,运用了实验性的叙述手法,被一位评论家称为“二十世纪末的杰作”。小说刻画了中国人的贪食、对“性”的不安,一系列人际关系,很多关系又相当奇特。《酒国》让人联想到斯威夫特(Swift)的《一个温和的建议》,即使二者不是百分之百地相同。
如果也有人问我:“为什么有人读这本书?”我认为那是因为小说里有着拉伯雷式幽默与情趣的纯然快乐,结构上的艺术性以及辛辣的讽刺。这些特点即使在英译本里也有所再现。
当然,莫言又凭借另一部情节曲折、想象丰富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获得在俄克拉荷马大学颁发的首届纽曼现代中国文学奖。所以我们希望莫言写作的全部意义将在西方得到更全面的认可。
苏童和莫言,都是沉重的话题。那么,“对使命感表示怀疑”的那位青年作家如何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不喜欢他的人和喜欢他的人旗鼓相当,尤其是年轻人,对他格外崇拜。王朔的小说以自我专注、享乐主义、蔑视社会的傲慢来挖苦体制和改革,他被冠以北京“恶少”和更坏的称谓(或更好的称谓,那要看你的态度)。纽约时报指出:“如同杰克·凯鲁亚克,王朔为一群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叛逆青年涂上了浪漫的色彩。又如约瑟夫·海勒和库尔特·冯尼古特,他在探索社会的矛盾和荒诞。”
王朔并没有批评集权,但他所做的更要命:他笑话他们没风度。
在《玩的就是心跳》中,王朔故作神秘,讲了一桩可能发生的谋杀案和一个可能是罪犯的享乐派小青年。王朔所谓的“心跳”就是讲述北京的“下层社会”,编织的故事既扑朔迷离又引人入胜,为读者送上的答案至少不比他提出的问题少。
对有些读者来说,如同在封面上为自己的小说做宣传的神秘大师史蒂芬·金,王朔的小说也是写给所有人的:
《玩的就是心跳》也许称得上九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妙趣“横生”的小说。这部作品自成一格,可以称之为中国的黑色幽默,带给读者负罪的快感,要超过金赛(Kinsey Milhones)或者鲁坎(Lucan Davenports)二人相加的效果。这部小说到底算什么?解放了的杰克·凯鲁亚克?我认为不是,你只有经历之后才能知道。好玩儿得不得了。
较之从前,如今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越来越多。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学的读者层也同时扩大了?是不是有更多各行业的人开始关注“容量增加的剃须膏罐子”了呢?这还很难说。因为波动原理也会影响中国文学读者的多少。新闻中出现中国消息,中国文学作品的销量就会增加;反之要是新闻中好久没有中国的消息,中国文学也就从书店下架了。再有就是燕尾效应:到中国工作或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书籍的阅读数量和种类也会随之增加,其中自然涵盖文学作品。
还有一点让人感到鼓舞,美国商业出版社有一种倾向,为丰富自己的书单,要添上中国作家——不仅仅是几部作品——至少是以部分的热情来宣传这些中国作家。
但不幸的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中国人中那些胆子更大的人就有希望享受空前的物质生活,与此同时,不少作家发现,他们用心创作的作品,在这个消费资本主义大环境下,并不被人那么看好,回报越来越小。查建英的话不无道理:
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一个普遍事实: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政府了。现在他们还要考虑商业的力量。他们不能再开自己的玩笑:读者大有人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什么作家是人民喜爱的需要的代言人,是社会的良知,这种感觉也一同消失了。
好多颇有前途的年轻小说家开始放弃对艺术的不懈追求,转向有利可图的商业领域,如写电视剧剧本等。在我看来,这对中国纯文学反倒有利,其实这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只有那些最执著、最有才能的作家才能留下来,促使他们继续提高写作水平,以此来面对国内外越来越小但又更为严格的读者。目前,固定在西方出版的小说家不超过十几人,他们大多是人到中年。他们在国外已形成鲜明的特点。人们读他们的作品,一是为了他们的写作才能,一是为了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诚然,这是一场逆流而上的战斗。尽管翻译过程存在着种种风险,尽管中国文学仍处于“第三世界”的地位,但即使荆棘丛生,当代中国文学仍可以以其独特的魅力,满足国外的读者,启发国外的读者。一位评论家的话正好用在译成外文的中国作品上面:“一部译作让我们走入世界文学,让我们走入不同时空的心灵。翻译是他者的庆典,一次真正‘多元文化’的盛宴,只不过没有彩球和喧吵。翻译不但可以丰富我们的个人知识和艺术感觉,同时也可以提升我们文化里的文学、语言和思想。”这段话,对于译成外语的中国文学来说,同样适用。“通过译入其他文化的作家作品,可以防止文学过度地民族化和地域化。”这句话若是对的,那么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一定要双向畅通才是。
〔此译文系二〇一四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L13CYY02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