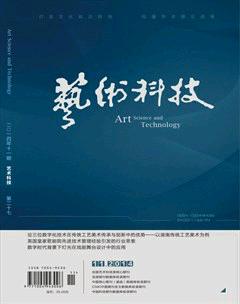《蕙风词话》与《人间词话》的创作论比较
李甜
摘 要:《蕙风词话》与《人间词话》有“双璧”之称,而这两部词话虽所处时代相近,其创作风格却十分迥异,一部作为古代词学评论的集大成者,一部开西方文学批评的先河,本文试比较二者在创作论方面的不同,从二者创作主体对创作的作用的不同、创作要求的标准的不同角度,看词学观对其创作论的影响,总结这两本书词学创作论共同认识及各自的疏漏之处。
关键词:《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创作论
创作论的概念十分含糊,他大致可以与词人本人的词学观相辅相成,但在实际的创作中,词人却可能违背于自己的词学创作观,与自己崇尚的词学标准相悖。词学创作论是从词作产生之时开始发源,并且指导词人的创作内容与表达风格,对文学创作提出了细致具体的要求。
1 从创作的主体看
创作的主体,实质也是抓住创作的起源。词人对创作灵感的寻求是不遗余力的,所谓“情发于中而行于言”,而灵感、性灵之说又是十分玄妙的,对灵感的解释只好依托于外物,与学力、与景物生发、与人生阅历等相联系,这样也为求学之人指了一条明路,似乎通过多读书、多感发于外物就可成就优秀的文章,实际上这样的解读方式是对“灵感”本身的消解。灵感既不可抹去他本身具有的神性,也不可与现世割裂的产物,是历史与环境作用的结果。
而究竟创作起源于何处,《蕙风词话》和《人间词话》给出了不同的阐释:
《蕙风词话》:“词中求词,不如词外求词。词外求词之道,一曰多读书,二曰谨避俗。俗者,词之贼也。”又有:“填词要天资,要学力。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亦与有关系。无词境,即无词心。矫揉而强为之,非合作也。境之穷达,天也,无可如何者;雅俗,人也,可择而处者也。”
这里提到的词外求词,注重作词之外的世界,其方法为多读书和谨避俗。多读书终有天可达到学力与境界的融合,谨避俗即是人有力区别雅俗,择而处之。同时况周颐又十分强调“吾心”,“吾心”即“词心”,从心中流淌而出的真意是受到“风雨”、“江山”的感发,感到所谓“万不得已者”,即人与景物的关系常有一种相磨砺,自然之景所呈现的必然的样子,这种自然的天性或顺己志,或逆己志,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说,“物各有性,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应物。一艺之成,三者俱焉。”而况周颐也指出了“吾心”来自书卷,正如《沧浪诗话》“别才非学而必多读书以极其至。”
而在《人间词话》中:“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以及为词人所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此处,王国维的观点认为,写词要有“赤子之心”。而李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环境中,孕育了忧郁、细腻、纯真的情感,即所谓“赤子之心”。而又将宋道君皇帝和李后主对比之后,力推李后主是有推己及人的担当之心的人。而李后主的成就之高,不仅仅在于他的情感是承担着天下的愁苦,更在于他自身的悲剧性,他自身经历与词学创作所给人的动人力量,即所谓“以血书之”。而王国维对词人的要求也是具体的,认为如果是客观描摹的诗人,要多阅世。主观的诗人要保持真性情,不可多阅世。阅世包括读书与阅历,而词作为主观抒情的表达,阅世浅反而见真性情。
此二人的共同点是都发现了“词心”的存在,也都注意到外在境界与自身的关系。王国维比况周颐深入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发明本心”,将“吾心”降落于情真意切之上,而况周颐还是将“词心”玄妙化了,在达到的途径上,继续提出要多读书、多感于外物才能练达文章。况周颐认为“多读书、谨避俗”是词境界高的必要途径,而王国维则认为性情真,文章方有内涵,我们需锻炼的并非一概而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是注重内在性情的培养,保持真挚的情感,抒写真意,便可成就好文章。
2 从创作的要求看
创作论观点的核心便是如何创作才能写出好的文章,而词学观的实质也是对至高艺术的追求。
《蕙风词话》的主要词学观点是“拙、重、大”。首先与“拙”相对的是“巧”,文章工巧便是强调对文辞形式的雕琢,而况周颐推崇“拙”,实质便是推崇自然不雕饰的文字,认为“词忌做,尤忌做得太过,巧不如拙,尖不如秃。”。其次是对于“重”的阐释,认为“填词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所谓神韵,即事外远致也。即神韵未佳而过存之,其足为疵病者亦仅,盖气格较胜矣。若从轻倩入手,至於有神韵,亦自成就,特降於出自凝重者一格。若并无神韵而过存之,则不为疵病者亦仅矣。或中年以後,读书多,学力日进,所作渐近凝重,犹不免时露轻倩本色,则凡轻倩处,即是伤格处,即为疵病矣。天分聪明人最宜学凝重一路,却最易趋轻倩一路。苦於不自知,又无师友指导之耳。”;对所谓“大”,《花间集》欧阳炯《浣溪沙》云:“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自有艳词以来,殆莫艳于此矣。半塘僧骛曰:“奚翅艳而已,直是大且重。”苟无《花间》词笔,孰敢为斯语者。”这里可以看出,况周颐对“大”的阐释为“大且重”、“大气真力”,以《花间集》论大,一反欧阳炯对《花间集》“轻倩”的定位,其质直情真,不同于矫揉造作的呻吟之词,感情深厚是其背后“大且重”的支撑力量。
我们可以看出《蕙风词话》所推崇“拙、重、大”的文學气质,是经历一番深沉沉郁的历练后,脱颖而出,表现为淳朴自然又不失厚重感的。
《人间词话》对词的高下之判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理论,但他在论词的高下时常用的词有境界、气质、品格、神韵等词,如有条目云“词之雅正,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
又有“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这些词看似是相近又不可区分的,似乎觉得王国维对于这些判别词本身也是含糊不确切的,境界与气质和神韵的区别在哪里?在我看来,王国维的境界之说在于物与我的融合,这不同于气质与神韵的完全发乎于中,如同灵感一样是玄虚的,好的境界便是自然之景与人真挚情感的结合,而非内在情感的宣泄,也不仅仅是文字上的清丽晓畅。总结来说,王国维对词作创作的要求便是情真。《蕙风词话》言:“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所表达的与王国维此处对境界的看法是一致的。
放在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晚清四大家推崇吴文英,将隐晦幽深的词放在词学的高位上,这在文学史是一个短暂而又偏激的时期,而王国维力求推翻这种评价标准,不谈吴文英词的优劣,转而谈词的“隔与不隔”实际上是间接地纠正了词坛的风气,重新建立一种文学批评的视角。从这个角度看,王国维作为当时的新派,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他的《人间词话》中有许多不严密之处,但我们能从他突破框架的洒脱中寻求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真意,这也是我们对于古人之理解与同情之处了。
参考文献:
[1] 况周颐.蕙风词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 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3] 钱钟书.谈艺录[M].三联书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