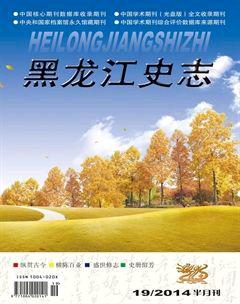周启澄与《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的成书
闫鹏鹏 杨小明
[摘 要]周启澄,我国著名纺织教育家,纺织史专家。其著作《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是我国纺织史研究奠基之作,在纺织史学界流传甚广,在国际上也颇受好评。这本书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因为该书几乎将我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有关纺织史料收录并加以系统地整理、总结。可以说是纺织史的百科全书。而这本书的主要统稿人,周启澄先生,并非历史学家,而是纺织学者。本文以口述史方法重现纺织专家周启澄先生编撰这样一本纺织史的百科全书何以可能,对了解和认识新中国第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提供侧面了解。
[关键词]周启澄;纺织史;《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成书风波:科学还是技术
1976年“文革”结束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对各行业的发展历史进行整理,决定出版一套百科全书,囊括各门学科的发展历史,其中也有纺织卷。然而当时有学者认为:“纺织是一门技术,而不是科学。”这种说法在学界引起较大争议。周启澄回忆道:
“编写《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定稿之前,大部分领导收到反映,说纺织是一门技术,不是科学。这个信息从北京吹到上海,大家都认为,这根本不对,这是科学。我们就要跟他们争论,但不能讲空话,而是要有相当的说服力。我听到(北京的)这种说法,感到也很气愤,肯定要翻过来,所以《中国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第一篇文章,主编(陈维稷)来写。其实这篇稿子是我起草的。我就把它(这种说法)扳过来,你说不是科学,我的题目叫做《纺织生产与纺织科学》,开宗明义表达我们的观点。这个稿子代表这本书,比较慎重,所以大家集体讨论。稿子打印后交给委员提意见。大家讨论中间认为这篇文章主题思想是对的,一定要这样改进。就具体提法吸取了意见,交给部长(陈维稷)看,修改后就送上去交付出版社编委会统稿。我去北京跟他们(专家)辩论“纺织是否是科学”。后来大家没什么一致同意我们的看法(1)。”
成书之难:“多方搜集”与“反复统稿”
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启澄编纂此书,遇到许多难题,回忆此事周启澄仍记忆犹新:
“我参加《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这本书,是集体工作。这本《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有20个人。我们学校有6个人。各个专业的人都有,大家在自己负责的部分找相关材料,不同的人写不同的章节,最后成书汇总在一起。所以好多原始资料不是我找到的,而是我们编写组分头找。还有个有利条件,编写这本书前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已经编写了一本《纺织史话》流传很广。他们在编写纺织史话过程,到处发掘有关纺织科学的史料、有关纺织的有趣故事,等等。因为《纺织史话》一定要写得有吸引力、看得有兴趣,不是一本正经讲技术,否则一般老百姓外行不愿意看。所以他们在编写这本书搜集了好多与纺织有关的资料,有技术的(资料)搜集,没有技术的(资料)也搜集。搜集面比较广。而我们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要把不是科学的删掉。因为我们是科技书,与科技无关的删掉好多(2)。
翻阅这本书,之所以完善,源自取材丰富,除正史所记载的纺织史料进行详细整理外,有些古籍甚至是孤本,对于这些未曾受专业历史学训练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个挑战,以周启澄为首的编写组为此花了很多力气去查找每一则能够找到的史料:
“依赖我们这20人各方面人都有,兴趣不同。有些同志比较喜欢这些古代传说,有兴趣,他就去搜集。特别是上海纺织研究院的6位学者,为了编写《纺织史话》,搜集了不少有趣的故事,这方面做得很多。至于正史里面的资料是有目的地去找,比如唐六典,不仅是唐六典,历朝历代的史料都去查的。正史有政治有经济,有生产技术的,专业性的没有,笼统的介绍都有,我们把正史里有关生产,有关纺织的甚至有关农业的都去查,而且是普遍查,有用的就拿来,选取最精华的,对分析纺织科学技术有关的都选出来。20人每个人都有熟悉的领域,我们学校6个人,有一个(人)是纺织机械的教授从美国回来的,有一个(人)是研究织造,还有搞棉纺的、研究企业管理、研究化学的人,如染色,染整。还有纺织材料的,如纤维这些。我本来是学毛纺的,对于历史一窍不通,因为被动的。领导给我这个任务,我开始用功(3)。”
这本纺织学术著作不同于其他同类著作,既要有扎实的纺织学术基础,又要有丰富的人文底蕴,特别是在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风气下,编纂者就要“文理兼备”,周启澄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
“这分两个方面。一方面,编书的人,那个时候都是三十多岁。这些人年轻时候都接受过一定的文言文基础,加之接受任务后拼命看书。假如说我现在再找二三十个年轻人去做这事儿,难度比我们那个时候二三十人要费劲多了,因为现在对古文底子比较低。我们这代人是在解放前到解放后的过渡阶段,所以文言文比较好。学的很多,基础有一些(4)。”
从这本书的质量来看,不仅文笔通畅,亦俗亦雅,最为难得的是通篇没有一个错别字,周启澄在谈及此事,也感慨成书之不易:
“第一个阶段是20个人分头写,每个人承担一部分,写到一定阶段,写完后收上来,第二个阶段挑出6个人一起看材料。20个人交上来的稿子无法成书,风格不一样,文字底力也不一样。写的各不一样。6个人分纺织、染、各个大方向,整理。这6人整理20个人的材料。整理的过程中间就把差异缩小了。按统一的思路和规格。但毕竟6个人,虽然大家总方向认识一致,具体到个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以6个人的稿子完成后,最后留下来三个人,从头梳理,将有前后矛盾的,有差别的改掉。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交出版社,编辑看了后交回来再改。
现在的书没有以前慎重,以前的书要经过三校。稿子给了编辑,编辑改了后清样,退回来,再让我们提出意见,编辑按我们修改的意见再修改。这样三次就可以。我们这本书经历四校。到第三次我们仔细研究,又修改一次,最后清样都是我一个人。当时科学出版社在北京,我就住在北京。我们以北京纺织研究所作为我们的住处。开始我们20个人第一阶段交上来,6个人统稿就住在北京纺织研究所,那个时候很困难,不像我们学校,有招待所,有住处。他们研究所规模小,没有招待所,就腾出办公室,搭六个铺位。研究所比较小,没食堂,旁边有家化纤机械厂,有食堂,就在工厂食堂吃饭。是这样子。搞了半年,6人把20个人的稿子统了一遍,最后留下三个人,第二轮统稿,还在这里,到三个人统稿交出版社,认为还要改,那一次就我一个人住在北京纺织研究所住了半年,稿子来了仔细改,编辑看了后再改。到第四次。所以我们这个书出来以后,没有错字。现在的书没法比。我们这本书下了非常大的功夫。这样编写质量可以说是过硬的(5)。
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间,北京纺织研究所的领导也参加编辑工作。他们决定出版一套资料选编(《纺织科技史研究资料汇编》)。这套资料选编就是在编写过程中有的稿子有的材料不能进书,第一次的素材,就是原始素材,书里不能用,但是对于历史还是有价值的,就把这些材料编辑,一个月一辑,跟杂志一样,这就是《纺织科技史研究资料汇编》。出了十几本。这个是最原始的材料,抽取出来最精华的部分便在这个书里。”
结语
周启澄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纺织史学者,纺织教育家,他所经历的社会变革造就了他们那一辈的学者对国家和社会的无私奉献精神。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周启澄那一辈的理工科学者会转向文史哲研究,一句“国家的需要”,就能鼓舞他们在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开疆拓土“。周启澄这一代的学者,是将国家的需要与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代,是奋斗的一代。通过对周启澄的著作及其本人访谈,我们可以真实体会到老一辈学者治学的严谨和认真。这是值得当今学术界省思的。
周启澄那个时代,计算机还并未广泛使用,编书绝大多数过程依赖手抄,对于资料的检索,也并未有如现在的数字检索高效便捷。然而当今学术的不端风气,似乎更胜于从前,无论是国际上的小保方晴子论文造假、韩国的黄禹锡论文造假,以及我国一些高校学生的抄袭成风,似乎更应该从周启澄这一辈的学者体会到一个学者应有的爱国情怀和严谨学术精神,学术需要信仰,少些功利心。
《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的主编者是陈维稷,而周启澄是受陈维稷部长委托,负责实际编纂工作,如果不是探究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我们也不会知道,周启澄才是这本书的最大功臣;同样,周启澄也可以不必因为这个使命而转变自己的学术方向,在纺织机械、纺织科普领域周启澄已经有自己的研究成就,然而为了国家的需要,周启澄开始钻研自己并不熟悉、也无人问津的纺织史领域,并取得一定成果。这一代学者对国家、学术的荣誉感,是当今学术界应当借鉴和反思的。
参考文献:
[1]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1-438.
[2]周启澄.中国近代纺织史(上下卷)[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3-7.
注释:
(1)引自《周启澄口述访谈记录》,采访时间2013年12月11日
(2)引自《周启澄口述访谈记录》,采访时间2013年12月11日
(3)引自《周启澄口述访谈记录》,采访时间2013年12月11日
(4)引自《周启澄口述访谈记录》,采访时间2013年12月11日
(5)引自《周启澄口述访谈记录》,采访时间2013年12月11日
作者简介:闫鹏鹏,男,1989年生,山西太原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纺织史、中国科技史;杨小明,男,1964年生,甘肃武威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纺织史、中国科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