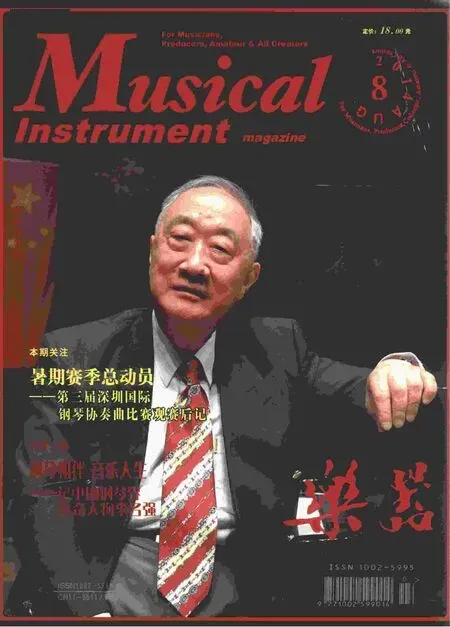“弓勺”与琴徽的器物学赘论
文/睹史陀

琴徽的产生年代是古琴形制演变史上的大事。围绕西汉是否已经有了琴徽,以饶宗颐先生为代表的正方与以郑祖襄先生为代表的反方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争论基本上以文献学和训诂学的方法展开。本文旨在利用器物学的方法为饶先生的结论提供新的支持,而饶先生部分论点似可以改进,以更清晰地说明琴徽的演变,故不避续貂之嫌作此赘论。
一、关于“琴徽”的学术争鸣
关于古琴徽位产生的历史年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发生了长达十几年的学术争鸣。此一学术争鸣是琴学研究的一件大事,也是一段学术佳话。耘耘有《“徽”字一辨十二载》①一文,描述、总结了此一争鸣过程和各方观点。只是,此文重在归纳各方论据与分歧,并未明确表述这一争鸣的最终结论,仅于最后委婉提出:“在漫长的争鸣历程中,也暴露出古代音乐史学界传统文献学功力的某些缺憾和非专业化倾向”,暗示饶宗颐先生所论略胜一筹。
此一争论始自1986年郑祖襄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该年第4期发表《“徽”字与“徽位”》②。该文认为《淮南子》中“参弹复徽”和杨雄《解难》中“高张急徽”等文献中“徽”字均不能解释为“琴徽”。“两汉论琴形制的记载中始终未出现琴徽,应是琴徽没有产生,而不是偶然为著者所不论”。“琴徽产生的年代是在应劭的晚年和嵇康的幼年之间”。
饶先生随后发表数篇文章③,讨论了《淮南子》等文献中的“徽”当作“琴徽”解释,并提出了枚乘《七发》作为证据:
“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于是背秋涉冬,使琴挚斫斩以为琴,野茧之丝以为弦,孤子之钩以为隐,九寡之珥以为弓勺,使师堂操畅,伯牙为之歌。”
饶文认为:“弓勺是射矢之准的,借射质之‘的’来比喻琴在音阶表现高下之准的。李善引用字书,没有说明是何书,但分明指出‘的……琴徽也’一义,可见西汉人亦称徽为弓勺。”
很明显的,饶先生所提这一证据较其他文献如《淮南子》要更有说服力。其后的辩论多数围绕这一证据展开。就逻辑而言,正方只要一个“有”的例子,即可以反驳“无”的观点。郑祖襄先生从文献、训诂多方面提出反驳,核心是张铣注弓勺为琴饰为是,而李善注为琴徽为非。许健先生作为反方,从琴的演奏等琴史故事推论而赞同郑的观点。
枚乘《七发》中的“弓勺”字,是辩论中的核心“战场”。琴徽产生于何时,此一文献是一大关键。“弓勺”字释为“约”、为“的”,饶、郑二先生并无分歧,只是对“注”的理解不同。郑文提到“朱长文《琴史•尽美》则说得更明白:‘…按律吕以定徽;合钟石以立度。法象完密,髹采华焕。于是,饰以金玉瓌奇之物;张以弦轸弓勺弭之用。而琴成矣。’徽是徽,弓勺是弓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张铣注得对,隐和弓勺都是琴上的装饰。”郑先生论点的最大难处是在文献、实物中都找不出具体的琴“饰”来。郑先生曾推测琴额上的玉饰为“弓勺”,其实琴额上的玉饰,从考古发掘的战汉琴到传世唐、宋琴均不见当时的玉饰。琴额之玉饰多是明清所为,所用玉饰也多是同一时期的。按郑先生的逻辑,“隐”也是“琴饰”,则更是找不到对应物了,实难自圆其说。饶先生认为张铣注为“琴饰”与李注为“琴徽”都正确,并无矛盾,侧重不同而已。饶先生之见解更合乎情理。
二、“弓勺”与“珥”器物学考察
“弓勺”释为“的”,当是确论。然而饶先生由“的”到“准的”到弹奏徽音(泛音)需要瞄准之义,故将“的”“弓勺”依古注释为“琴徽”一说,结论虽然正确,然而内中逻辑值得商榷。汉末刘熙《释名•释首饰》“以丹注面曰的”。从器物学上考虑,如果在琴面上做“琴徽”这样的标识,工艺上最简单的就是以红漆点一下,即所谓“以丹注面”。“弓勺”“的”就是汉代人对最初琴徽的命名,也是最确切、合理的命名方式。以金、玉、贝等明亮的材料做琴徽,不再“以丹注面”,“的”失去所指,过渡为“徽帜”之“徽”是个合理的逻辑。
“珥”作为耳饰,从考古发掘两方面看,是一种束腰形圆柱形玉饰,而且考古发掘此类器物确是女性所用之耳饰。将其切片,从制作工艺、尺寸大小、形状特点都符合做“琴徽”的要求,以“珥”为“弓勺”是很自然、合理的。“弓勺”确实当释为“琴徽”。以下详论之。
(一)从“弓勺”到琴徽——器物学解释
战汉漆器的出土数量巨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以红黑两种颜色为主,即所谓丹青二色,这一特点在汉代漆器中尤为显著。同时,战国至西汉早期的琴在同一时期的漆器中显得较其他器物更朴素。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七弦琴、马王堆三号墓七弦琴皆是通体髹黑漆。这一风格与同时期髹饰华丽、繁缛的瑟、均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此,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髹黑漆的琴上标识出琴徽,最简单、自然的处理方式就是点以朱漆。这是由器物的制作传统、工艺特征和时代审美等原因所决定。
汉末刘熙《释名•释首饰》中说“以丹注面曰的”。“的”,“明见也,射质也”。射质的“的”,就是红色的靶心,这是“的”(弓勺)字本义。朱漆点出的琴徽,如果让汉代人来命名,称之为“的”(弓勺)是最恰当的了。
饶宗颐先生释“弓勺”(的)为的准,因为徽是用来弹奏泛音的,需要“瞄准”来弹奏。这个逻辑忽视了器物工艺特征,因而没能采用汉代文献中“以丹注面曰的”这样直接、有力的证据。同时,以“的准”释“弓勺”,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后来“弓勺”又改称“徽”了。
由简单、低级到复杂、高级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最初的点以朱漆的琴徽,到玉徽、金徽、蚌徽,是琴徽制作、发展的自然过程。后者更美观、实用,代替漆徽是必然的。随着“弓勺”演变到不再是“以丹注面”了,而是玉、金一类材料,“弓勺”逐渐失去其所指。金玉质地的“弓勺”更准确地说演变成了一个标识、徽帜,称之为“徽”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珥与瑱
玉石耳饰是学术上跟琴徽一样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珥、瑱虽然在汉及先秦文献中多见,是何形制,如何使用,时至今日亦无定论。本文且不论这些分歧,只从一些确切的结论与考古成果出发,讨论《七发》中“珥”与琴徽的关系。
《说文》:“珥,瑱也,从玉耳,耳亦声。仍吏切。”段玉裁注说:“按瑱不皆以玉。许专去‘以玉’者,为其字从玉也。……《考工记》注引《左传》‘缚一如玉’,《释文》曰‘瑱本或作真耳,耳形真声。不入耳部者,为其同字异处,且难定其正体或体。’”瑱,亦作“真耳”。江琦先生以“瑱”字为例,论及“古字(词)不公义多随时代变迁,音亦往往随义的变迁而演化”,“瑱”有四种读音,义不同读音亦变④。“瑱”最初“真声”,用以充耳、塞耳以戒妄听,音填(tián);后来,悬于耳旁,为自镇重义而兼耳饰之用,读音镇(zhèn)。
实际上,瑱用以充耳、塞耳有2种情况,一为生者充耳以戒妄听用;一为葬玉,充耳作为窍塞。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⑤,出土耳部玉石器墓葬(群)、遗址计66处,约200件,其中13处出口玉耳塞24件(含琉璃耳塞1对,料珠定为耳塞1件);4处出口玉九(七)窍塞中的耳塞4对8件(含琉璃耳塞1对);17处出土玉瑱32件;18处出土琉璃瑱85件(包括1处出土玛瑙瑱7件);14处出土琉璃耳珰30件(包括2处出土玛瑙耳珰4件,1处出土炭精耳珰1件);另有4处出土玉耳环若干,均位于云南。
以上是按照文献原本命名所做统计,通过查阅原始文献的描述及图片,可以发现器物命名标准非常混乱,存在一定数量的同物异名、异物同名的问题。然而,具体考察这些器物,其中的规律却是明显的:
——玉质耳塞、瑱,均为实心无孔,多数是为梯形八棱体、梯形圆柱体,部分为椭圆形棒状。此类形制以琉璃或其他材质的,仅见2例。而其体量基本相当,长度约2厘米,直径细处0.4厘米上下,粗处1厘米上下。
——琉璃、玛瑙质瑱、耳珰,绝大多数为束腰形(或喇叭形)有孔。此类形制,上述统计中未见玉质。西汉陈请士墓⑥中出土过青玉质1件(M170:32),罕见。
另有一种不多见而特殊的形制,为在束腰形器两端多出一个稍小于截面的半球,统计资料中如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琉璃质⑦(见下图1),统计未包括的西安市北郊范南村西北医疗设备厂工地西汉墓⑧出土白玉质耳饰(见下图2)。

图1
以今天的琴徽形制看,共13个,最小徽(一、十三徽)直径约0.5厘米,最大徽(七徽)直径约1厘米。虽然最初出现的琴徽数量不确定,但是徽的出现是为了泛音的演奏,考虑到演奏需要、泛音位置的对称性和常用有效音乐等因素,13个徽是很自然的选择。琴徽的直径大小,从传世唐代古琴至当代古琴,差别不大,直径出入通常在0.2厘米以内。主要原因是美观与实用:太小不易区别大小徽,太大既不美观也不利于按弹准确。最初的琴徽也要遵循这一要求,琴徽直径不会有太大出入。
制作玉质琴徽,从工艺上来讲,当先以管钻取圆柱形玉胚,再磨制成梯形圆柱体(管钻所取玉芯,加工效率低的话,自然就成为梯形圆柱体。但出土汉代玉器显示很高的工艺水平,当是圆柱体),将圆柱体切片成大小不一的玉片(琴徽)。
综上,汉代玉质的耳饰从形状、尺寸上讲,是制作琴徽的绝佳选择!释“弓勺”为“的”,为琴徽,以“珥”(瑱)做徽,工艺上的合理性难道仅仅是种巧合?!而放眼形形色色的汉代玉器,找不出另外一种可以如此便捷改制成古琴部件的!
琴徽学术争鸣中未有人讨论“孤子之钩以为隐,九寡之珥以为弓勺”中的前半部分是何义。“钩”为带钩。“隐”,《说文》释为“蔽也”,引申有“短墙”义。《左传•襄公 二十三年》:“踰隐而待之”。杜预注:“隐 ,短墙也。”汉代称岳山为“隐”当是由此义而来。有效弦长称为“隐间”是又一佐证。有论者说“隐间”之名源自瑟等有相对的2个或2个以上岳山的乐器,而此类专业术语在乐器间借用亦是很正常的。带钩在汉代是极普通的用具,多以金属为之,高等级的也有玉质的。虽然形制多样,但是长条圆柱体的造型是常见的。把这种形制的带钩截掉钩首与钩钮,便可以用来做岳山或者方便地镶嵌到木条上作岳山!“孤子之钩以为隐,九寡之珥以为弓勺”中,“钩”之金与“珥”之玉对仗,两者之巧妙改制为岳山、琴徽2种琴之部件相对应,这难道又是种巧合?!这显见是一种必然。
三、试论“徽位”与“徽”的出现年代
枚乘《七发》所讲虽然是虚构的寓言,但是,必须有现实生活的基础。特别是寓言中的此类描述,是为说理服务的,完全脱离现实与合理性,就最终难以达成寓言说理的目的。寓言中的描述,其隐含的道理就当是易于理解的、明显的。以钩为岳山,以珥为琴徽,在枚乘生活的时代应该是有现实基础,并为读者(听者)所理解的。从以朱漆为徽到以玉、金等为徽,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枚乘创作《七发》时,琴徽尚称为“弓勺”(的,“以丹注面”,以朱漆为之),而以“珥”为“弓勺”已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琴徽——“弓勺”的出现应当有一段时期了,处于向称为“徽”过渡之时。枚乘生卒与创作《七发》的年代均不详。《汉书•枚乘传》讲“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学界以此公认卒于武帝即位之年,即公元前140年。有学者考证枚乘《七发》作于其在吴王濞处为门客时(宋代以来学者多持此论),约在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前后⑨。以此论,“弓勺”(琴徽)的最初出现年代可能不晚于文帝初期。
饶宗颐先生《三论琴徽》⑩一文中说:“现在试举出二条含有徽字的汉赋中的句子加以说明:
杨雄《解难》:
‘今夫弦者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是故钟期死,伯牙绝弦破琴而不肯与众鼓。’(汉书•杨雄传)
颜师古注:
‘徽,琴徽也。所以表发抚抑之处也。’
孙机据此谓‘大约至西汉晚期,琴上才普遍装徽。……(《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页386)其说平实可信。”杨雄作《解难》时琴徽命名已经由“弓勺”演变成“徽”,距“弓勺”之出现约百年,就语言、器物,特别是古琴形制的演变来说,都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注释 :
①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3年第1期。原文标题中“辨”似应为“辩”。
②主要辩论文章收入《华夏旧乐新证:郑祖襄音乐文集》P.202~215。
③主要辩论文章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经术、神乐》之《古乐散论》。
④《说“瑱”——兼论古代汉语音随义变问题》,《武汉教育学院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⑤据《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赵朝洪主编,科学出版社,2004年)所收文献粗略统计,原文献未说明玉器数量的统计为1件。此书收录文献发表时间下限截至2000年。上述统计涉及的文献,有若干资料过于简略,如“玉窍塞”12件,不确定是否耳塞,因而无法计入“耳塞”或“九(七)窍塞”中。石质塞、瑱未计入。
⑥《西汉陈请士墓发掘简报》(程林泉等,《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6期)
⑦《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 考古学专刊 丁种第六号洛阳烧沟汉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出版社,1959年)P.212。
⑧《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刘云辉,文物出版社,2009年)P.238。
⑨《<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赵逵夫,《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第36卷第1期。
⑩《音乐艺术》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