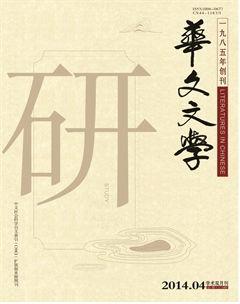子轩访谈录
欧阳昱 子轩
欧阳:先拉拉家常。听说你是北大毕业,而且学的是泰语,怎么会学这个语言呢?
子轩:为了不离开北大。我是在北大校园里长大的,父亲是北大东语系教授。我从小学习就重文轻理,很偏科。那年我的高考总分只过了北大的送档分数线一点点,上不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父亲于是说:报个小语种就能留在北大。
欧阳:那对这种小语种的兴趣你能维持四年吗?
子轩:准确说是三年,第一年我们没上专业课,我们是双语制,泰语和英语同时学,第一年只修英语。而且,北大的公共课非常多,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选自己感兴趣的别的系的课了,类似“西方艺术史”,“美学”,“西方哲学”什么的。这也是我一定要留在北大读的原因,当年的北大是个知识的和社会的独立王国,你能很方便地涉猎到所有你有兴趣的东西。
欧阳:所以至少你成了一个诗人,是这样吗?记得当年你还写过不少诗,我都译过一首。
子轩:是的。年轻时好像大多数人都是诗人。自由浪漫嘛!
欧阳:跟年龄有关吗?还是跟国家有关?不然,怎么到了澳洲却停写了?
子轩:应该是和国家有关吧。澳洲本身已经给了我我想要的自由与浪漫。但,也没有停写,而是写出来的不再感动我自己,所以觉得没意义了。我是艺术家,知道:一件艺术作品首先要能打动艺术家自己,才能打动观者读者。
欧阳:谈起澳洲,想问一下,你是何时去澳,又是为何去的呢?艺术的事稍后再聊。
子轩:1989年4月拿到签证,6月17号到达墨尔本。为了自由。我从小到大都是个西方文学艺术的酷爱者,又会英文,想出国看看、想明白自由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是很自然的。在中国,我们只知道“不自由”是什么样,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样。今天的中国人,即便他们有点钱了,可依然不知道什么是“自由”。所以,今天无论多么富有的中国人,依然想出国,西方社会依然是他们的向往。
欧阳:这么说来,你到澳洲已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澳洲自由吗?自由跟钱有没有关系?跟艺术呢?
子轩: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所以,在澳洲我很自由。自由跟钱没有关系,跟艺术有关系,或者说是艺术跟自由有关系。自由的某一种解释是选择,有选择才有自由,有钱会带给你多一些选择,这不可否认,但只在西方社会;在中国,你的选择不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而是在不可能和不可能之间,于是有钱也没有选择。艺术跟自由的关系很直接,是共存亡。我称现在的中国艺术界是:有形式没艺术。
欧阳:一谈起艺术和自由这个话题,似乎就有说不完的话。对了,记得1994年我代表墨尔本华人作家节邀请韩少功、张贤亮参加时,你还来过,那时似乎仍对文学情有独钟,但不久好像就开始画画了。为什么?
子轩:对文学我一生都会情有独钟的。写作对我来讲,是生命的陪伴。画画是因机缘。认识了我现在的partner,才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进入了绘画的领域。
欧阳:谁是你partner呀,能问一下吗?
子轩:他叫傅红,是知名的澳洲华裔画家。在澳洲获得的绘画奖项能有五十多次了。但对我来讲,获奖不重要,最主要的是,自从他踏上澳洲这片土地,二十四年了,一直是靠画为生,而且生活得很好,没有做过一天别的工作。这么种艺术上的良性循环,即便是澳洲本地人,怕也是绝无仅有。这就是我认识他后决定拜师学画的原因之一,希望也能建立我自己的艺术王国,做个“国王”!
欧阳:能否讲述一下,你从白手起“画”到现在,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子轩:挺顺利的。有大师在身边,少走了很多弯路。我是从油画的花卉起步,直接用色彩解决结构、光影、构图和造型。基本上是印象派的底子,因为傅红的风格属于印象派风格,他的色彩在澳洲非常有名气,所以,我的色彩也很为顾客称道。我是在学画六个月之后就进入市场的,也就是说卖掉了第一幅画。三年之后,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离开他的轨道,自我探索新的风格。到现在,我画了十年了,也入选过不少奖项,获过两次奖,有了四家很稳定的画廊代理。我想,画画要求我做到两点:耐心,和安于孤独。
欧阳:你的文学功底,对绘画有帮助吗?请具体讲。
子轩:不知道。这是个含糊的问题,具体不了。很多人都说有,可我自己感觉不出来,也许潜意识中有。写作与绘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绘画,只有技术不用脑子完全可以,如此这般画得不错的也很多,并不需要很深的知识结构或文学功底(说得难听点,文盲也可以画)。他们说有关系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动脑子,喜欢看大量的画册吧。我只是习惯上觉得单单掌握一种技巧挺没意思的,也配不上“画家”这个多少带有内涵的称号。
欧阳:换个方式问吧,也就是说,你是否看书?除了看画册之外,看不看文学书,什么书?比如,一个从不看书的人,跟一个业余时间大量看书的人比,其画一定是有着某种本质的不同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子轩:这么说肯定是有所不同。阅读是我的一大爱好,尤其西方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艺术类的作品。已经有很多年了,我基本上不看中文原创作品,只看翻译的作品。我曾经有三四年创作的画作是属于带有Nave风格的变形画,那其中就多少含有我的文学意识。那批画的市场非常好。其实谈画却看不到画是很难谈的。有些,只有看到画面你才能体会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视觉艺术是需要看的。
欧阳:为何不看中文原创,是指大陆的,还是港台的,还是海外华人作家的,还是所有?有什么很好的理由吗?
子轩:这是个很得罪人的问题。实话说,我几乎不看所有的中文原创作品。我个人理由的抽象表达是:西方作品给我的启示和感悟更多一些,他们所表述的人文观念更能让我接受,离我的精神故乡更近些。生命短暂,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读我没兴趣的书上。
欧阳:谈谈绘画吧。能谈一下你个人觉得最好的古今中外画家吗,主要是油画家。
子轩:我的绘画上的精神教父是凡高。当我2012年来到大英博物馆,站在凡高的向日葵原作前时,真正流下了眼泪。那色彩是他永恒的灵魂,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我喜欢点彩派以修拉为代表的一批画家。他们的色彩只有在原作面前你才会被折服,那么灿烂的色彩的流动,和那么多闪烁的层次,是任何精良画册都印刷不出来的。我对色彩极度敏感,所以,我喜欢的都是能够很好表达色彩的画家。
欧阳:你绘画中的人物画多于风景画,而人物对象也是中国人或曰华人多于其他人种,为什么?绘画人难道不能超越自己的种族和文化界线吗?
子轩: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中国女人的肖像,市场好,可能是西方人觉得有装饰效果吧,我画得也顺手,抓人物神态很容易抓得准,所以画得多。其实我最爱画的是城市街景,大场面的街道和人群,十几个几十个在画面上,那才见工夫,色彩才灿烂。你的最后那个问题对我是不存在的,你来过我最近的个人画展,是以肖像为主的,你看到在我的作品中,何止是中国人,什么日本人印度人毛利人荷兰人,加上穆斯林,全都有了。
欧阳:对,这就是我注意到的,也有意提到的,发现是你与其他许多身在海外的华人画家不太相同的一个地方。这种关注的立意何在?
子轩:因为我的画展主题是“墨尔本人”。这个城市现在聚居了近二百个不同种族的人群,而海外出生的墨尔本人已经占了百分之三十多。这个城市不大,却很丰富多彩,文化气息很浓,有影响的国际性文化艺术节一年能有十多个。所以,表现墨尔本就成了表现它的“国际化”和“多元”的特性。中国人是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在墨尔本,它也不过就是其中一个族群而已,和别人是平等的,不需要特别关注。
欧阳:有没有想过回国办画展?
子轩:没有。如果你接下去要问为什么,我现在就回答你,因为中国的艺术市场太脏了。
欧阳:这话怎讲?能否更具体点?因为我不问,别人也要问的。
子轩:其实读这篇文章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简单说,在西方,画家只管创作,把画送到自己的代理画廊。画廊负责展示、出售和定期为画家举办画展。卖掉了就按照合同上的比例分成,画家部分由画廊按时转到画家的帐户上,或寄支票。画家与画廊的关系很简单,见面一杯咖啡而已,甚至我在另外一个州的画廊都代理我的画三年了,卖得很好,我至今还没有见过他们。每次,我把新画的照片email过去,他们选择,我寄画,卖了他们把钱直接打到我账上。如办画展,规矩则各不相同,但大部分是画廊画家对半承担开幕式的费用和此次画展的广告费用,卖掉的画依然按照合同的比例分成。多少年了,规规矩矩大家都遵循着这样的道路走过来,自由,也平等。画家自己可以有几家画廊代理,像傅红,最多的时候全澳有十五家画廊代理他的画。至此,我倒是想问:在中国他们是怎么操作的?有这么清楚干净的可能吗?
欧阳: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因为就我所知,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华裔画家,如关伟、阿仙、呼鸣、池展穗、周小平、张鸿俊、沈嘉蔚、宋陵、沈少民、郭健、王志远、林春岩等,现在都脚踏两只船,中国船和澳洲船,往来其间,有些甚至干脆就长期居华了(如沈少民、郭健、王志远、林春岩),连傅红也不甘寂寞,曾到中国做过一次大展。连美国的徐冰、蔡国强等艺术大腕,也对中国趋之若鹜。你的不回甚至不去(毕竟中国对你来说,已经成了外国),想必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你能细谈一下吗?
子轩:个人的选择问题,没有什么“隐”。也许因为我出来的时候年纪很轻,于是比他们更西化也更安于澳洲的生活方式吧。反正,他们跑回中国所寻求的各种满足都不是我的需要(其实你列的名单中有一半都算不上是专业画家)。中国,在专业上,画大画的能得到便宜的人工,烧陶的能得到国内的工艺,有人有业内朋友的帮助在中国容易炒作,有人想拥有更多形式上的关注和掌声;心理上,中国有热热闹闹的气氛,吃喝嫖赌成本都低,画家再不用“独立作战”,等等。要知道,在西方社会,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成功失败都是自己的事,没有谁为你鼓掌喝彩。这么种寂寞,是一般中国出来的人所不能忍受的,他们已经习惯了集体主义,习惯了帮派体系,习惯了形式上的宏大,和私生活公共化。总之,一切都不过是两个字在作怪:“欲望”。但,这不是我的理念。我不觉得画家画画一定需要巨大的空间;我也不觉得画画需要成帮结队安营扎寨。我曾经有三年的时间,是在自己家里四平米大的洗衣房里画出了几百幅作品,卖到全澳各地。真正的艺术家只对艺术创作有欲望,“拿起画笔,我就是国王”!我很尊重我自己和自己的选择:既然我选择了自由,就只会追随自由,我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顺便提一句:傅红的那次天津博物馆的个人画展是天津文化局的邀请展,性质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因为我参与了前期和天津方面的共同筹划,所以比较清楚。
欧阳:很好。哎,我想起来了,你好像还有个满人的背景,如果是这样,澳洲华人画家中,就有三个了:你,呼鸣和关伟。是这样吗?似乎少数民族的血统,更使人具有某种精神的气质,不是吗?
子轩:没觉得。能不能不去把人归类划圈儿呢?这个做法很中国。
欧阳:哈哈,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其实也很澳洲的。还有个问题忘了问。你说你不读中国书,那么,两个获得诺贝尔奖的高行健和莫言你看不看?怎么看?
子轩:十年前都看过。更喜欢高行健。我好像以前对你说过,这些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文化精英主义者,莫言和他的作品,我都不喜欢。
欧阳:去年你患了一场大病,今年痊愈得很不错,而且很快就办了一个画展,应该是你所有画展中最大的一次吧。能否讲一下生病和绘画的关系?
子轩:生病和绘画能有什么关系?生病了就不能画画了。不过,我患的是血癌,的确和死亡的距离太近。出院几周后,朋友依我的请求带我去墨尔本市中心看一个世界有名的T恤衫收藏家的四千件收藏展。那天还是盛夏,市区人流涌动,我突然就有了一种新的感情:以前那么反感的拥挤的城市与人群,今天呈现给我的竟然是如此健康而灿烂的生命色彩。就是从那天起,我决定画一系列城市街道人群的题材,表现生命的盛大,而用的也正是前面提到的点彩派的新画法,更加强调色彩。不过,癌症出院八个月能推出如此大型的个人画展,又全是新作品,我都为我自己骄傲!
欧阳:你看看,关系这不就出来了吗?下次计划再画哪方面的题材呢?现在一些年龄逐渐大起来的画家,都似乎有点焦躁、浮躁、急躁,好像觉得再不搞点大动作,弄点超大的作品出来,很快就时不我与了。你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搞个什么大动作来?
子轩:还没想下次。城市街景刚开始几幅,还需要一段时间扎扎实实地画下去。我没什么大想法。画画是很enjoy的一件事,搞得那么功利,哪里还能画得下去!我正好相反,生病之后再回画室开始画画,心境越发宁静平和,好像倒是比以前来得更有耐心了。我从大笔改小笔画,为了达到色彩层次更丰富的效果,结果速度变慢了一倍,但,我非常沉浸其中。画好眼前的每一幅画,要像信仰宗教一样认真才行。
欧阳:好,谢谢你的访谈答问。你看还有什么地方没有问到而需要补充的吗?
子轩:没了。谢谢。
(该访谈2013年9月16日开始,从上海松江提问,从墨尔本回答,至2013年9月27日结束于北京。)
(责任编辑: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