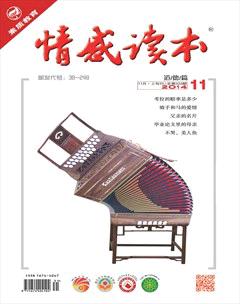轻放
安宁
走廊里的声控灯,很早以前就坏了。每次走到门口,同租的几个人都会习惯性地叹口气,在黑暗中摸索着将门打开,又重重地关上,想以此发泄对那一脸晦暗的廊灯的忿恨。楼下的小卖部里摆设了各种各样的灯泡,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有想起在买泡面的时候顺手捎带一个灯泡上来。那盏灯,就这样沉默着,一日日听我们的跺脚声,砰砰砰地响了又响。
爸爸过来看我,走到门口,看见我费力地用手机里微弱的光线照明,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说声“稍等”,便下了楼。不过几分钟工夫,他便拿了一个灯泡上来,一声不响地安好。然后,他轻轻一击掌,黯淡无光的走廊便瞬间有了温暖通透的光亮。我站在门口,看爸爸脸上淡然的微笑,便说,你可真是光明使者呢。爸爸却扭过身来,正对着我,说,其实路过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不过是1元5角钱的灯泡,顺手就捎过来了。
我笑,说,可不是人人都像您这样乐于助人,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况且,这是租来的房子,这走廊也属于公共的区域,不只我们这一层,楼上的人也要从这经过呢。
爸爸没吱声,只拿起身边的扫帚,一层层地扫着楼梯上的烟头、纸屑、菜叶。有人从他身边经过,他便停下打扫,将身子朝楼梯一贴,朝来人笑着点一点头,表示让对方先行。而路人总是诧异地看爸爸一眼,慌乱地点一下头,匆匆离去。
我在晚饭的时候,便抱怨他,何必对陌生人这样殷勤,他们指不定在心里觉得你有毛病呢。爸爸呷下一口酒道:我管不着别人心里怎么想,但我心里开心就可以啊!况且,我就不相信你给别人微笑,他还能泼你一盆冷水不成?所谓寻开心,就是这样,你不自己主动找,它怎会自登家门?
几日后,翻起账本,突然想起一个借钱的熟人,当时他信誓旦旦,说3个月后肯定一分不少地全都打到我的账户里来,可是已经过去5个月了,他不仅没有打钱,连一个解释的电话都没有。气愤之下,我操起电话便要质问熟人。爸爸得知后却将我拦住,说,钱既然已经借出去了,就不必再催了。我不解说:难道这笔钱就这样白白地给他了不成?这样不守信用的人,何必跟他客气?
爸爸一声不响地拿过我的账本,将我记下的还款日期一栏“啪”一笔勾掉。这才说:何时你将心里那个还款的日期也一并改成无期限的时候,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气愤了;假如人家忙得忘记了,你过去一通责问,不是彼此坏了感情?一笔钱丢掉不要紧,连带着把一个朋友也给弄丢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依然心里憋闷,我觉得这个人根本就是故意忘记的,我听说他还借过别人的钱,每次别人一催,他就推说下个月还。
爸爸依然不紧不慢地喝一口茶道:如果他真是一个常占便宜的人,那你这钱,丢了也没有关系,能够用钱测出一个人的深浅,并在以后的路上,尽可能地远离这样的人,不是更好么?况且,如果他不打算还你,你再怎样催促,也是得不到这笔錢的,不如心中先放下,这样轻松的是你。而他,则会在你的安静里,心里有小小的失落与不安。
十几年的光阴过去,回过头看看,我发觉捏着硕士毕业证的我,在没有读过几本书的爸爸面前,原来是如此地苍白且无力。人生中一切矛盾的化解,并不是拿尖锐的刀子划过,而是那最素朴、最温暖的轻轻一放。
郭冬生《深圳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