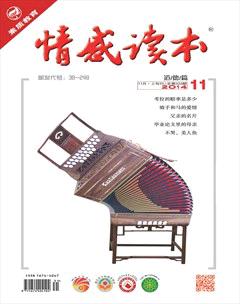父亲最后的日子
羊白
老实说,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一直是鄙视父亲的。
父亲是个老实人,平时话很少,对领导唯唯诺诺,在家里脾气暴躁。父亲是个锅炉工,烧了30年锅炉,眼看就要退休了,工厂却倒闭了。人家都去闹,他却在家听收音机,说又不是他一个人,政府总归会解决的。
后来他总算熬到头正式退休了,我们兄妹几个也相继大学毕业,找工作成了难题,知道靠不上他,只好在外飘泊打工。
之后10多年,聚少离多,我们相继成家,父亲也老了,变得慈祥和轻声细语了,和孙子辈在一起时像个小孩。我懂得,这叫隔辈亲,只是一大家人聚在一起已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
我万万没想到,大家长时间地和父亲聚在一起,竟然是在他最后的日子。
这,来得太突然。电话那头的母亲没有哭泣,却极度虚弱,仿佛在自言自语。母亲说:“胃癌,就是胃癌,果然是胃癌呀!”
是的,果然是胃癌。细想起来,这个结果不算突然,其实老早就埋下了种子。父亲常年三班倒,饮食不规律,记得小时就听他说胃不舒服,尤其是他发脾气时,想打人又呲牙咧嘴地搂着肚子,被打的我在心里还骂过他活该。他认为胃炎很正常,疼时吃点药就是了,这么多年就这么习惯下来。没想到,身体里的战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现在终于爆发了。
医生告诉我们,癌细胞已大面积扩散,只能保守治疗。关键不能让病人的精神垮掉,保持良好的情绪,密切配合治疗,说不准会有奇迹出现。
我们只好瞒着父亲,告诉他还是胃炎,住院打点滴慢慢就会好的。
父亲说:胃炎不可怕,这么多年不都这样过来了。他让我们兄妹几个不要太牵挂,留一个人照料就行了,该干啥干啥。
有天我在病房的卫生间里洗东西,无意中听到父亲和临床的一个病人低声谈话,听着听着,我的眼泪哗啦一下涌了出来。原来,父亲早就知道了他的病情,我们瞒着他,他心知肚明。他和那个病人说:“唉,人这一辈子呀,早晚都要走,没什么想不通,只是,折腾了孩子们,各人都有工作,不能让孩子们整天耗在医院里……”
我装作什么也没听见,继续请假侍候父亲。我知道,能够和父亲呆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父亲坚持要出院。我们只好答应,希望家庭的温暖能给他以慰藉。
回到家后,父亲开始做离世前的一些准备。
他把家里的电话薄又工工整整地重抄了一遍,尤其把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的号码,比如我们子女亲戚的电话,水电煤气电话,都写在了显眼的位置。我知道父亲是怕母亲在他离去后,不能很快地找到这些号码,母亲的眼睛不好,他把那些重要的号码又用红笔描了一遍。
然后,父亲又把缴费的银行卡,煤气卡、电卡、医疗卡等,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专用的盒子里,又把各自的密码写在了一张清单上。母亲看着这一切,什么也没有说。其实母亲很过细的,这些东西是不会忘记的,可她由着他,她知道这是父亲愿意做的事情。做愿意做的事情,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有天晚上,父亲把别人欠他的借条也翻了出来。其中一张额度最大的为5000元,父亲说这人他信得过,不必着急要,等对方宽裕了,一定会还的。还有一张1000元的,父亲说,这个能要回就要,要不回来就算了,他老婆常年有病,日子也不好过……
父亲给母亲交待的细节,我在隔壁的房间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的心里一阵翻滚,感觉从来没有这么懂得父亲——这个曾经被我鄙视,碌碌无为、老老实实的我称为父亲的男人,此时此刻,我心里奔涌的只有敬佩和酸楚!
出院后半个月,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止痛的药片从一天吃一次,开始变为一天三次。止痛药吃过后,由于药物的刺激,导致父亲喝点水就呕吐,呼吸困难,咳嗽不止。我们眼睁睁地目睹着病痛对父亲的折磨,却束手无策。癌细胞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正在他的身上无情地切割。
看着父亲极度地瘦下来,坐卧不宁,呼吸不畅,我除了握住他的手,没有更好的办法。甚至谈话也极少。在死亡面前,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稍好点时,父亲会斜躺着望着窗户发呆,我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他在遥望故乡吗?是不是也在想他的父親母亲?这最后的时刻,父亲依然不善言说,他把话都埋在了心里和一个个细小的动作里。
在父亲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实在瞌睡得不行,就趴在父亲的床边睡着了。后来,迷迷糊糊之中,我感觉头有点痒。突然之间,灵光一闪,我意识到父亲正在用手轻轻地抚摸我的头。我的身体打了个机灵,泪水溢满了眼眶。我没有动,继续装睡,我不忍心惊动这神灵般的爱抚。我理解父亲的心情,他和我之间有太多的隔膜,更有太多的不舍和对亲人及这个世界的牵挂和留恋。
兰明芳摘自《北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