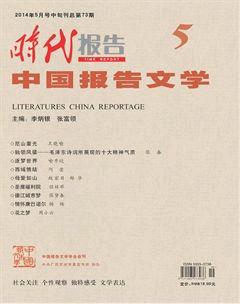圣鹰福利院
任林举
站在南鹰山上俯瞰松花江,松花江是一个半圆的弧,向内环扣着;也如一副张开的臂膀,从对面抱过来。江水从南鹰山左翼而出,又从南鹰山的右翼而没,将这段有关南鹰山的记忆、经历和印象时刻不停地转述给广阔的科尔沁草原,也转述给草原深处那烟波浩渺的岁月。
一生没有离开过水的纪老先生,在77岁的晚年,终于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在这依山傍水的岸边。这一次,他真的不需要继续奔波了。就在南鹰山与松花江之间那块半月形的土地上,他心中酝酿了大半生的梦想,一一变成了现实,一件件、一宗宗清晰而具体地排列在那里。树木、农田、药圃、渡船、诊所、可供200人居住的房舍……还有那些在困境或绝境中刚刚解脱出来的人们。他把这一切纷繁复杂的事物缩写成五个大字,刻写在一块木牌上:圣鹰福利院。
纪先生落脚于鹰山的第二年春天,突然来了一个风水先生,从江的转弯处弃舟登岸,一直走到南鹰山顶上,一通端详、考量之后,下了这样的断语:“山环水抱,屈曲生动,聚祥纳瑞。”并认定能够找到这样一处风水宝地的纪老先生是一个世外高人。对此,纪老先生不置可否,只是淡然一笑,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如漂萍的一生是怎样的祸福无定,一路走到了今天,其间的过程与结局又都是怎样的难以掌控。天地之间,如果真有什么神秘玄妙的布局或力量,也并不是人人可以窥破和预见的,人的能力和智慧也只能读懂自己身后留下的那行足迹。也许一切都是天意,至少是人意与天意的合力。“福瑞祥和”也好,“凶险乖绝”也好,最终的结果都不一定是人意所愿和人力所定。就像那千回百转的大江,在哪里顺畅,在哪里受阻,在哪里迂回,在哪里盘桓,在哪里被迫改变方向或折返回头,又在哪里峰回路转奔流激荡,并不一定由江本身所决定。除了一个向前行进的意志,一切都只能交付于那执掌着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机缘。
历史上,凡有一点传奇色彩的人,性情行为多怪异。看似不合理中常有大理、真理存焉,看似无情无义,却往往有大义在心。三国时,吴国有一位叫董奉的人,据说医道高深,相传有“仙术”在身。他“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杏十万余株,蔚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后来,杏子大熟,董奉就地做起了易货生意,用杏子换谷物,存储在仓中,然后再用得来的粮食接济那些衣食无着的贫苦人或旅途中断了盘缠的受困者。这倒好,悬壶济世,兼恤苍生,连动物们都照顾到了,只是自己一年到头,见不到任何利益,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个白忙活。图什么呢?什么也不图,可能就是图个自己内心的安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不是很好理解,因为人心与人心总是差异太大。现实中,一个人不论如何也不能够百分之百地了解和理解另外一个人。关于这个“杏林春暖”的故事,估计纪先生也不一定能够知道。他年轻时,家境贫困,念的书并不是很多,很早就开始下地务农,哪有闲心去关注那些难懂的古文和典故?但他却在那个故事发生了1700多年以后,把相似的情节重新演绎了一遍。
想当初,纪先生抱着那几本祖上传下来的古旧药书死啃不放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能看得懂,但他却一看就懂;当他按书上的方子试着给人治病的时候,也没有人相信他能治病,但他始终充满自信。中国的农民实在,却也实际,他们一般不会相信在身边长大的邻家小子突然有一天能够行医抓药、治病救人,正所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吧。于是,他只能到更远一些的地方,找那些疑难杂症和无药可医的病人“试水”,做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尝试,并且事先许诺病治不好绝不要钱。按常情常理和一般的医疗规律,去触碰这几类大医院都避犹不及的病人,就是在冒险、犯傻和犯大忌。然而,纪先生却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披星戴月,走村串屯,决意将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做到底。没有人说得清,他走上行医之路到底是因为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使命作用于内心,从而义无反顾;还是因为藏在生命中的某种神秘力量催促着他,从而执意前行。对于他的家人来说,他无疑是中了那几本发黄旧书的魔咒,“鬼迷心窍”,才抛家舍业,开始了那段无证游医的生涯。
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如日夜不息的江水,把人们生命里的一切冲淡、稀释。所有的痛苦、甜蜜、得意或失意都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淡薄、淡然。但旧事重提,仍会有一丝清晰而尖锐的痛,从纪先生的心头掠过。至今他也不愿相信,二十多年四处奔走施药行医的结果竟然是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然而,事实往往就是这样,出人意料又毋庸置疑。尽管他为那么多人医好了病患,又为那么多人接济过钱粮,却还是没能避免自己的妻子因贫病交加而抱憾辞世;尽管曾有那么多人因为重获生的希望而赞叹他是华佗转世,却还是没有阻止少数人认为他是江湖骗子误人性命,而把他告上法庭。当子女们因为无依无靠而投奔亲友的时候,当那一年零九个月的监禁之灾真正降临的时候,他应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委曲?悲伤?怨恨?失望或绝望?似乎一切都无从谈起。一年零九个月的监禁,仿佛一座神奇的丹炉,倒把他炼成了“火眼金睛”,世情与天理两把烈火在他的胸膛里反复灼烧,让他悟透了人性的脆弱、可悲和可怜。他不想与人争执和计较,只是想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到、做好。在知情人都为他的遭遇喊冤时,偏偏他自己不叫苦叫冤。如果有病痛在身的人通过看守人员相求,他仍然不在意自己的当与不当,二话不说就跟着看守人员去给人看病。功与过,于他来说,自有一个凡俗之外的尺度。
如同一开始就难以确定应该以怎样的罪名将纪先生羁押起来一样,最后,当地的执法者始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将纪先生无条件释放。一年零九个月,就像一场难辨真假的梦境一样,莫明其妙却有惊无险地过去了。在人们想象中,历经劫难之后的纪先生一定形容憔悴、神情沮丧,哀哀如丧家之犬;或满腔怨愤,摆出一副誓与某人或某些人势不两立、一拼到底的姿态;出人意料的是,显于人前的纪先生神情淡定、精神焕发,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沉和阴郁之气。当孩子们见到他的那一刻,都忍不住流下了委曲和心疼的眼泪,他却微笑着劝慰孩子们不要难过,说自己很好,一切都很好,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们也都很好。直至今天,对那些有负于他的人,他依然没露出半个怨字或半点仇恨,其中有一些人在他情况好转之后竟然向他伸手求助,他照样不计前嫌慷慨解囊,似乎从来没有人做过任何对不住他的事情。
纪先生遇到丁纪兰的时候,大约在五十岁左右的样子。这是一个唯一像他帮助别人那样无私帮助他的人,也是一个深信他的品行和能力的人。她不但资助纪先生买药行医,而且还把自己的房子腾出一部分让他当作行医的诊所。从那个简陋的诊所再起步,纪先生的人生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对于他的医术,依然是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他也依然如从前一样,看好了收钱,看不好不收钱,有能力支付的收钱,经济困难的分文不取。但从此,他的事业却一天天兴旺起来。有患者见纪先生只顾埋头看病,却顾不上考虑自己的事情,就主动为他申请了行医执照。然而,有证或无证,似乎对他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他依然穿着随意朴素,仍然不晓得自己赚了多少钱,唯一不同的是,从此在他脸上多了几分微笑和阳光。
说往事如烟,往昔的一切真的就会如轻烟一样散去,一切的阴霾与坎坷,仿佛就在某一个人生的转弯处瞬间消失。当纪先生把有生以来最大一笔积蓄7000元人民币投向松花江畔的哈达山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滨高地,却将他的事业及人生轻轻托起,并一步步推向新的高度和境界。有了地,他开始第一次大规模地“建山”,开山种药,辟地修屋。他亲自设计,亲自组织施工,建起的第一批房屋,除了腾出一间当诊室,其余的都让给前来就诊的病人免费居住。
来纪先生诊所看病的人,有一些病好离去之后,便口口相传,说松花江边有一个纪大胡子,医术高超,对于病太重治不好的人和贫困的人分文不取,还供吃供住。信息传向四面八方,便有更多的人闻息而至。于是,纪先生每天四点起床,为病人把脉调药,一直到晚上,最多一天要诊视400多病人,一年光抓药就得抓出去60余吨。这老先生也是奇怪,七十多岁的人,每天那么大的工作量,却从来没有累倒过,走起路来仍然脚下生风,每天上一次山,一些山上的年轻人都没有他脚力强。
一些原本生活无着或残疾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病好后,就不愿意再离开,恳求留在纪先生的诊所,帮纪先生种药或照料其他病人。对于这样的情况,纪先生的心总是很软,软得没有现实的理性和原则。“想留就留吧,权当家里多了一个吃饭的人。”这样的情景不断重演,几年时间,家里就多出了七八十号人,并且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完整的人,有的人缺手,有的人缺脚,有的人缺少正常人应该有的智商,也有的人缺少家庭的温暖和亲情,或鳏寡或孤独。看看这样的情形,纪老先生哈哈一笑,就把诊所改成了福利院。
纪先生建在哈达山的福利院在迁往鹰山之前,资产评估就已经达到了1100万元,但政府征地建设水利枢纽时,因为资金短缺却只给了240万元的补偿。对此,很多人建议纪先生坚持向政府索要,纪先生却摇头说算了,政府也不容易,有限的钱还要留着干大事儿。福利院挂牌儿的时候,也有人建议纪先生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获取合理的政策补助,同样被纪先生以相同的理由拒绝了。对于钱财的看淡和疏于管理,纪先生的子女们感触是最深的。早年家境贫寒时,他曾多次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粮食给了更加需要的人,而自己却无米下锅;也曾因为看不过别人贫病交加的处境,不仅无偿给人看病,还硬着头皮向朋友借钱去接济人家。经济状况好转之后,他更是坚持一个信条:不留钱留德。老家来的人、过去的朋友、困苦贫穷的陌生人、需要办学的或想修路的,只要向他张嘴求助,他也不去考查更不签合同,不用招标,直接给钱。老屯来的人说,孩子上不了学需要50万元修建校舍,他就叫财务直接拨款50万元;原来住过的广发屯说需要80万资金修路,他就直接把80万元交给村上,连个手续也不要;有人以合作办厂为名义来与他一起搞项目投资,一次次要钱,明知道那些钱很有可能有去无回,他仍然坚定不移地把钱拨去。子女、亲友说他傻,说他不懂程序、政策和法律,也不懂如何辨识真伪,他却笑而不怒。他有他的理念,他一直认为,钱多害人,人如果在钱上起贪念迟早会遭到报应。如果自己有钱不舍就是自己在钱上有了贪念,如果有人索取了不义之财,那人就犯了贪的罪。钱如流水,而罪却不会因为钱的去来而流来流去,罪一旦上了身,就会永远背负。这一套如咒语一样的逻辑,听起来很绕,但却成为他爽直行事,化简人生的信条和依据。
其实,鹰山的山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山,只有从松花江的江弯里看,视觉上才显出山形。如果从北边的平原过来,并看不到山,但沿那条曲曲弯弯的乡路前行,走着走着大地就沉了下去,沉到很低时再仰头,一座土山便映入眼帘,中有一道裂隙从土坡上开出,那就算是山门了,进了山门之后,才进了真正的山。第一次去过的人,没有人不会由衷地感慨自然的玄妙神秘。近一些年,每天都有各种颜色、各种品牌的车辆在城市和鹰山之间来往,站在平原上看去鹰山的车辆,感觉上一定是突然就在大地上隐没了,而出鹰山的车却如在地底突然冒出来一样。有时,就会有一辆白色的“捷达”冒出来或钻进去,那才是南鹰山真正的主人。纪先生的车除了车况老旧,看起来和其他的车辆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奇怪的,因为车上坐着的是纪老先生,所以,有时就会有一个令人感动或令人不解的故事随车回到南鹰山。纪先生的车走走停停,不但应邀去给一些有家有业有住址的病人看病,也给那些无力发出邀请的病人看病。有时在街上遇到了一个正在抽“羊角风”的孩子或一个脚趾因冻伤坏死的孩子,就下车相问,确认没有归属,就拉回家去诊治。治好后,孩子的父母来认领,当然就“物归原主”,如果因为某种原因那孩子再度遭到父母的遗弃,鹰山将再次成为他们的家。
当越来越多无家可归的人以鹰山为家或想以鹰山为家的时候,纪先生再一次进行大规模“建山”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与“杏林春暖”的先人董奉有所不同。董先人是居山不种,也不收留前来看病的患者,而是以杏易谷,以谷救人,做的是流水人情,人家是仙人嘛,自然多一份不似人间的超脱。相比之下,纪先生所做的一切就多了些人间烟火气,在济世的同时掺入了太多凡人情感,不但救人一时,还幻想着救人一世,不但在物质上接济,也在谋划着精神上的安抚。这就让他所做的事情变得有一点儿复杂、混沌、难以评判,说不清他所做的一切到底是那些人的需要,还是他自己的需要。也不知道他在社会伦理和社会规则之外所做这一切的真正用意和根本动力是什么。然而,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他就是执意要把一生的心血和钱财全部花在这南鹰山上。建造房屋,进一步扩大福利院的规模,一直建到可以容纳200人居住;开发药材料基地,40%的绿色中药来自于自己的药圃;利用每一块可利用的土地种植树木;为山上的人扩大福利,购置校车接送孩子到城里上学,为每一户山上的居民无偿提供房屋、电器、家具、衣物、粮油食盐和主要蔬菜。从他这里出去的孩子,提供大学的全部费用,如果毕业后回到福利院工作,就当作工人开正常工资,如果不回福利院工作,赠送2万元安家费……圣鹰福利院的费用支出名目繁多,却没有一项用于他自己以及子女身上。他自己始终坚持不住山上条件最好、最宽敞的房屋,穿着简单朴素甚至有一点儿寒酸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口袋里从来不揣一分钱,需要出诊时,就让他的大儿子用一辆破旧的“捷达”载他出行,但每一次出诊不管什么时间结束,必须返回江边的诊所。一方面,他这一辈子也没离开过水,每睡必临水而卧;另一方面,他恪守着不在外边的宾馆里过夜的习惯。他不但自己不花钱,也不让自己的子女花福利院的钱,一分钱都不可以。他对别人都可以不查、不问,甚至放任,但对自己的子女却格外地严格、严厉,他的每一个子女都要靠自己劳动赚取生活费用。他曾指着自己的子女们说:“福利院的钱都是山上的,是用在山上那些可怜人身上的,你们并不缺钱,就不要惦记和指望,将来有一天这些钱也不是你们的,我要把这个福利院交给国家,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们也和社会上那些人一样,心里生出贪念。你们回头看看吧,你们身后还有多少不如你们的人呢?”
75岁的时候,纪先生遭遇过一次煤烟中毒的“大难”。那个冬天的早晨,若不是山上有一个人死去,福利院里的人需要找他定事儿,已经深度中毒的他就不会被及时发现。再晚半个小时,他的寿命就只能定格在75这个数字上了。送到医院后,老先生在高压氧仓里呆了整整一周才算彻底脱离生命危险。劫后余生,他却从此没再开口说话。是因为这次意外打击让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还是他从此不再想说什么了?或许,人生进入了某一个阶段之后也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他要做的事情只是聆听、不动声色地观察和品味。世态、人情、真心或假意,统统让它们在眼前翻腾流转吧。如果他真的在那个早晨死去,这个时间正是人们对他一生的是非功过加以评价的时候,或为他身后诸事料理、纷争的时候。然而,他现在仍然还好好地活着,活着就不能看清人们真实的品性和情感吗?也许,这正是天意让他在奔忙中停下来,对自己大半程的人生之路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和盘点,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看到世界和人生的真实面貌。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他一言未发,对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事儿,全然没有任何评价、没有表情、也没有态度,他将自己的生命调适成江面上一条不行、不载的空舟,随时光之流起伏晃动,并感知每一次潮起潮落、每一个浪卷浪伏给一个处于静止状态的生命带来的那些细微的触动和震颤。
半年里,他也许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大半生的努力成果正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显露出价值和意义;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身边人们对他那份深厚的情感和由衷的敬爱;也隐隐地感受到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他的依恋、珍惜和不舍。当他76岁寿辰来临的时候,人们不约而同聚到了他的身边,为那个越来越难得的日子守候、庆祝。就在那一天,他第一次开口讲话,他说:“再给我五年时间吧,容我把鹰山建好。”76岁的老人,集聚了生命里全部能量和情感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泪水纵横,在场的人无不声泪俱下,一片唏嘘,很多人流着泪,慢慢跪在了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面前。
转眼之间,秋,一下子就深了。放眼鹰山,视野里已经不再有任何绿色。风,从北来,吹过生在江岸的蒙古栎,就有一部分宽大的叶子跌落至江中。经过一春一夏的奔流,江水已经带着几分倦意,明显放缓了前行的步履。蓝莹莹的江水里,蒙古栎金色的叶片如一只只载着阳光的小船,列着队顺流驶向远方。转过这个江湾,江就离开了鹰山,再过一些天,江面就要结冰,空阔的江面上,一切都将停止流动。雪落下来的时候,这北方的江就变成了江的往事或江的遗址。没有水。人们已无法猜测这江水曾经是清是浊是缓是急,这江里曾经流过什么,曾经承载了什么或埋藏了什么。然而,这一切自然有着无声的见证,岸边的蒙古栎知道,江里的鱼知道,夜夜悬在天空的星星也会知道。至于为什么知道,自然,到了这个地步,江自己也知道。但,一切任由猜测和评说吧,江就是那条江。
责任编辑/魏建军
- 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的其它文章
- 逐梦世界
- 母爱如山
- 我的第一个上级
- 解读福州人文精神的佳作
- 《板仓绝唱》一文发表后的社会反响
- 德江城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