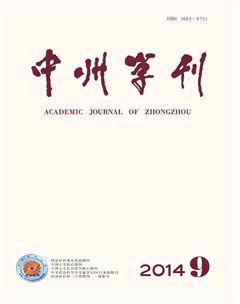诵诗的崛起与魏晋南北朝诗歌吟诵之风的形成
摘要:诗歌吟诵在魏晋南北朝迎来了一个高峰,其中原因有很多,如时代风尚对声韵的关注和佛经转读对美听的讲求等,但诵诗的崛起当为最根本的一个。一方面,随着诗、乐的分离,文人诵诗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其时,不但与音乐脱节的新的诗歌节奏需要吟诵来表现,而且获得了独立发展后的诗中之情意亦需要由吟诵来体味。另一方面,随着诵诗崛起的士人群体精神之独立,使得诗歌的主要功能由“兴”“观”而转为“群”“怨”。文人士子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礼教的性情抒发,同样刺激着诗歌吟诵的兴盛。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诵诗;兴盛;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9-0159-04
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产生、在先秦时代已出现的“吟诵”,在魏晋南北朝这个风流时代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其中原因有很多,如时代风尚对声韵的关注和佛经转读对美听的讲求等,但诵诗①的产生和崛起是最根本的一个。诵诗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是诗、乐的分离。诗、乐分离,造成了诗歌节奏与音乐节奏的脱节,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由此开始独立。伴随着士人精神的独立而发生的诗歌功能的转化,呼唤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礼乐形式的新的诗歌表现方式来适应新体诵诗的发展。于是,自产生之日起即伴随着诗歌节奏一起律动的吟诵,凭借着先天的优势,一跃而成为文人诵诗主要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诗歌吟诵的盛世亦由此开启。本文即希望通过对这些伴随着诵诗崛起的诸多因素之考察,探讨它们对其时吟诵之风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一、诗、乐脱节:吟诵兴起的契机
诗、乐的分离,根本上来说是诗歌节奏与音乐节奏的脱节,吟诵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表现诵诗节奏的需要。
诗歌作为一种时间艺术,节奏韵律是其重要特质和表现形式。这种节奏韵律最初是天然的,源于人类性情的自然吟咏,即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后来,诗歌被王官乐师采集而配上了音乐,这种节奏韵律就在音乐中被进一步强化了,亦即所谓“声依永,律和声”②。所以,在诗歌产生的早期,即诗、乐一体的《诗经》时代,吟诵作为诗歌的自然节奏,音乐作为诗歌“和声”协律的人工节奏,大体上是一致的,正所谓“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③。其时,节奏庄重简易的雅乐配合节奏固定简雅的《诗经》,正相适宜。后来,郑声兴起,雅乐渐废,《诗经》开始越来越多地以吟诵的方式流行传播。到了汉代,新一轮的采诗入乐活动开始,虽然其时新兴的音乐已较为繁复,但是语言亦处于不断的发展更新中。于是配合新乐而产生的五言乐府新诗,尚能保持着诗、乐节奏的一致性。
但是,随着里巷之曲与胡戎之乐的不断迭起更新以及二者与“雅乐”的不断交通融汇,音乐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节奏越来越繁复。而相比之下,语言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由语言节奏组合的诗歌节奏亦保持着固有的稳定性。因此,虽然中国的音乐在繁音促节中不断奔走,中国的诗歌却仍止步于由一、二、三音步组合而成的五言诗阶段。如此情形之下,二者的节奏自然不再相协。对于诗、乐从追逐到分离的过程,俞平伯在《诗的歌与诵》一文中曾做过更为详细的论述。他说:“自汉到隋有八百年……音乐早已变得认都不认识了;而我们可怜的伙伴(诗),不知走了多少路?他不过从四言而五言……依中国的老例,他俩该一起跑的,在前半段路程上跑得还差不多;到了后半段,他的伙计,耍着洋腔,跑得又快又乱,一眨眼就拉下这么一大节。”④诗乐“大有停止竞走之势”⑤。至此,诗、乐开始脱节、分工,朝着不同的方向迈进。一方面,脱离诗的乐,音乐性更加突出,有声无辞的纯乐得到发展,即器乐、舞乐。“相和歌”的发展过程即是如此。本来,“初期的相和歌,几乎全是来自‘街陌谣讴的‘徒歌与‘但歌”,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舞蹈、器乐演奏相结合,产生了‘大曲或称‘相和大曲。后来它又脱离歌舞,成为纯器乐合奏曲,称作‘但曲。大曲或但曲是相和歌的高级形式”⑥,著名的《广陵散》即是汉魏时期相和楚调但曲。由徒歌而配乐而至于器乐,相和歌的发展正展示了乐脱离诗的过程。另一方面,与乐分离的诗,语言特质更加突出,有辞无声的纯诗开始出现,即“不歌而诵”的“诵诗”。本来,“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但是,由于音乐、诗歌节奏渐不相协,所谓“声来被辞,辞繁难节”,虽然“闲于增损古辞”之乐工可以通过增损本辞来使之合声,以至“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不协”。但是,诗、乐之渐离,已为趋势,所以“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⑦。虽然这些不再协乐之“诵诗”依俗而被称作“乖调”,却正显示了诗脱离乐的必然趋势。
音乐既然不再适于表现诗歌节奏,新兴的诵诗,亟须另外一种传播方式来展示自身的节奏。于是,自产生之日起即伴随着诗歌节奏一起律动的吟诵,在此时独自担负起了表现诗歌节奏的使命。而且事实证明,相比于直读与歌唱,自诞生之初起即以表现诗歌节奏而存在的吟诵显然更适宜这个工作。于是,吟诵当仁不让地取代歌唱而成为诗歌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方式。关于诵之节奏更适宜于表现诗之节奏,前辈学者亦曾注意到。俞平伯先生即认为,“诵声虽以梵呗而变”⑧,“但并不和歌唱变得一样。……自西汉迄于中唐,诗体非但不受音乐胡化的牵制而旁出,反循这自然演变的轨道而直下。别的原因也有,‘诵却是串这戏的主角”⑨。郭绍虞先生亦言:“吟诵则与歌的音节显有不同……自诗不歌而诵之后,即逐渐离开了歌的音节,而偏向到诵的音节。”⑩至于“诵”之节奏为什么适宜于表现诗之节奏,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吟诵本身是作为诗歌节奏产生的,所谓“诗言志,歌永言”;二是吟诵一直以来的存在与定位即是为表现诗歌的节奏的,正所谓“以声节之”。只是在诗歌产生的初期,吟诵被节奏韵律更为显著的音乐抢了风头,待到诗、乐分离,音乐节奏不再适于表现诗歌节奏,吟诵与诗歌原本更为密切的关系才再次被发掘、显现出来。于是,吟诵终于在诵诗开启的时代迎来了自己的盛世。
二、由声而至辞:吟诵发展的条件
诗、乐分离,从消极方面来说,是诗歌节奏与音乐节奏的不再协调;从积极方面而言,则是诗歌作为语言艺术本身的独立。一方面,由于音乐节奏的日渐繁复,使得由稳固的语言文字组合而成的诗歌节奏与之脱节。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字意义内涵的发展和推进,使得由其组合而成的诗歌辞采意蕴更加丰富。因而,首次与音乐分离的诵歌,第一次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第一次开始将关注点由“声”转向“辞”,诗歌的文字及其背后的意义亦由此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随着诵诗的独立发展,不但与音乐脱节的诗歌节奏需要吟诵来表现,获得独立发展的诗歌之语言情意亦需要由吟诵来品味。
与音乐脱节后的诗歌,开始越来越关注文字本身所具有的辞采魅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诗歌之内韵情致,诗歌批评者们亦开始将诗歌品评标准转移至文辞。钟嵘《诗品》品评诗歌,只取五言,完全是从语言角度为诗歌分类的。并且他品评四言、五言之优劣曰:“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这里亦是以文字辨析文、意关系。而其称赏魏晋以来杰出诗人的诗作“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亦是以“文词”论英杰。可知,在钟嵘这里,是将语言文辞作为诗歌构成的重要素质以及诗歌品评的重要标准的。至于原因,则和钟嵘对诗的定义有关,他在《诗品序》中说:“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可知,在钟嵘看来,古今诗颂有别,古之诗颂“皆被之金竹”,今之诗颂则已“不被管弦”;“韵”“文”是相对的,古之诗颂因为被于管弦所以重在“音韵”,今之诗颂“既不被管弦”,所以不必取于“声律”,换而言之,专重文辞即可。所以,在钟嵘这里,品评今之诗颂,即是品评诗之文辞。
刘勰《文心雕龙》亦分列“明诗”“乐府”两篇,并于《乐府》篇末明确指出:“以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可知在当时,言“诗”即专指不合乐之“诵诗”,此已是共识。并且,《文心雕龙》还设专篇讲文字本身的辞采、声律之运用,以及吟诵品研之功效:“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而且,刘勰也同样非常重视文字辞采本身,其专列《练字》篇曰:“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他认为文字是表现语言的符号,为文学构成之基础。并且,《练字》之外,刘勰还列《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等多个专题来共同研讨文辞之运用,于此足见刘勰和时人对文辞之重视。不过,不同于钟嵘对声律之排斥,刘勰非常重视文学作品的声律,只是,刘勰所探讨的声律,已非音乐之声律,而是文字本身之声律。刘勰《声律》篇曰: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摘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
这里将音律分为“外听”与“内听”两种,“外听”者指音乐之声律,“内听”指语言之声律,他所讲求的诗歌之声律实为语言文字本身之声律。他认为,音律本自人声,语言为思想之枢纽,好作品,即是讲求唇吻间语言音韵协调之结果。
至于如何安排好语言文字,从而达到文意明了、文辞流利的效果,则需要寄之于吟诵,即所谓“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至于为什么需要寄之于吟诵,则在于“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即诗歌之滋味寄之于字句吟咏之中。诗歌之滋味何以寄之于字句吟咏,而非歌唱和直读?这是因为,相比于歌唱,吟诵因为没有音乐节奏的干扰,可以更好地品味文字本身的声律、辞采;相比于直读,吟诵由于品读的时间被拉长,欣赏过程和审美体验也一并被延长,从而能够更好地品味文字以及其中的滋味。因此,反复吟咏讽味诗歌之文辞,成为当时品读诗歌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颜氏家训·文章》即曰:“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因文采精妙而被反复讽味叹赏的例子在当时非常多。因此,由声至辞,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立以及由此形成的诗歌关注点之转移,都推动着吟诵的兴盛。
三、由“兴”“观”到“群”“怨”:吟诵兴盛的背景
与诗歌作为语言文学独立的过程相伴随的是诗歌功能由“兴”“观”向“群”“怨”的转化;而与此转化相伴随的是士人群体和个体精神的独立。
自魏晋始,与政权、礼教逐渐疏离的文人,开始由追求外在价值转向寻求内心价值,开始了对个体精神的执着坚守。抒发个人性情的文人五言诵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大量出现的。从笔者《魏晋:诵诗的崛起与歌诗的隐退》一文中所分析过的魏诗情形可知,相比于王公贵族所作的乐府歌辞和民间所作的无主名歌谣,诵诗基本上全为有主名诗歌。因此,有主名的文人诗歌对乐府、歌谣等歌诗在数量上的超越,不仅显示了诗歌形式的转移,更显示了创作群体的转移。诵诗的崛起所代表的是文人抒情诗的崛起。钟嵘《诗品序》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正是对这一盛况的描述。此时的诗歌创作,不再担负礼乐教化的重任,而是转为个人性情的吟咏。诗人从庙堂上走下来,独立的个体诗人和诗人群体开始出现。即使有朝廷赋诗,也不再是以往死板的合乐之作,而是风气所至,帝王与臣子即时即兴的雅兴吟咏。正如刘勰所言:“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些诗歌,所叙述的是个人恩宠荣耀之遭遇,所描绘的是集体交游宴饮之盛况,抒发的是激昂慷慨之个人志气,展示的是光明磊落之一己才情。与《诗大序》所言的诗人使命——“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已大不相同。此时的诗人,胸中更多喷薄洋溢的是个人之思致情感。
于是,所谓的“诗人之风”“顿已缺丧”。诗歌的主要功能逐渐由礼乐教化的宣扬转为个人情性的抒发,由“兴”“观”转为“群”“怨”。正如钟嵘所言: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无论是个人吟咏所洋溢的“怨”的基调,还是群体吟咏中所弥漫的慷慨悲凉之情致,无论是个人之痛,还是集体之伤,此时的诗歌所抒发的,更多是一往而深的悲情怨致,中国传统诗教中一直所强调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之诗风,在此个性张扬的时代,已被完全冲破,而屈原以来以悲怨为核心的骚体精神则得到了更多的继承与发扬。
也因此,其时盛大的诗歌吟咏之风多被正统的士大夫批评为背于礼教。如曾仕齐、周,历经离乱,终入隋为官的大臣李谔即以选才失中而上书隋文帝请革文体,对魏晋以来的吟咏之风大肆批判:“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他认为吟咏之风自魏之三祖开启后,“遂成风俗”,至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终至不识礼教,落得“文笔日繁,其政日乱”。但是,也正是这种不拘于礼教的性情之抒发,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士人精神最自由独立的时代,开启了中国文人诵诗的盛世。因此,由“兴”“观”到“群”“怨”,诗歌功能的转化,亦推动了当时诗歌吟诵的兴盛。
可以说,吟诵是伴随着诵诗的崛起而兴盛的,而这个过程,是伴随着诗乐脱离、诗歌作为语言文学的独立以及诗歌功能的转化而完成的。
注释
①本文所称“诵诗”者,即“不歌而诵”之诗歌,与以歌唱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歌诗”相对而言。因为“歌诗”可诵,而“诵诗”不可歌,因此吟诵乃诵诗的重要特质,取此称谓正可以突出其特点。这种产生于汉代的新体诗歌,在魏晋六朝兴起之后很快取代了传统“歌诗”而成为之后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有关“诵诗”的研究可参见公木先生的《歌诗与诵诗——兼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赵敏俐先生的《歌诗与诵诗: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功能分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等文章以及拙文《魏晋:诵诗的崛起与歌诗的隐退》(《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②③〔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疏,〔清〕徐养原校:《尚书正义》,见于〔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卷第三《虞书·舜典》,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页。④⑤⑧⑨俞平伯:《诗的歌与诵》,《清华学报》(自然科学版)1934年第3期。⑥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第43—44页。⑦〔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01—103、103、552、623、552、624、553、66页。⑩郭绍虞:《永明声病说》,《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4页。〔梁〕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3、203、12、28页。〔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文章》,中华书局,1993年,第295页。刘靓:《魏晋:诵诗的崛起与歌诗的隐退》,《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疏:《毛诗正义》卷第一,十三经注疏本,第271页。〔唐〕魏征等:《隋书·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