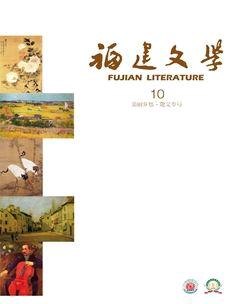野果
连江水
年年的七月半,都要回老家祭祖。祖厝旁,有棵老树,藤蔓附身,年年在此刻缀着一溜的果子,个个像小馒头。这时节,果子已翠绿不再,凝重得红紫,有的甚至裂开了口,泄露有关消息。满腹是它付于秋风的心情,其实未尝不是我们那年的往事。
它叫薜荔果,我们给它取了小名 ——“芋荞”。它小的时候,不会让人在意。色青皮厚味涩,一摘就是满手的乳汁,一沾,干时一大片洗不净的黑。五月以后可零星上手,扯去皮生吃,满嘴的沙沙与些许的滑腻,解馋可以,说不上可口。六七月以后,形势大转。皮去得容易了,掏出满腹褐色的果肉,放在纱布上,清水过滤,汁液入碗,澄清沉淀,紫褐色的凉粉浅卧碗底,清甜细腻润滑,激动着我们的唇齿与童心。
中药方里,它有个诗意而伤感的名字“王不留行”,很有古典诗词的意境。长大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而舌尖上的青涩的记忆却让我们流连忘返,“王孙自可留”啊。
家在戴云山脚下,清贫的岁月,就因满山的野果而鲜活多汁。
小的时候,水果这类奢侈品是买不上的,然而,父母自有疼哄我们的方式。大人外出干活,乖乖在家,常会有一些奖赏。常吃到的是“田瓜”。有时是青果,半生半熟的最佳,肉籽同样细嫩,放在嘴里,咔嚓一声,就是满嘴的清甜。有时是熟透的,红彤彤的,吃在嘴里糊腻腻的甜。美中不足,坚硬的瓜籽,不好下咽,且从父母口袋里掏出时,早已椭圆不再,不成糊也成饼了。大姐常会郑重地说:瓜籽不能吞下,会从鼻孔长出小“田瓜”的。所以,吃起来总特小心,绝不敢像猪八戒吃人参果。
到了自己能上山下地的时候,野果自是手到擒来。野孩子的那点心事,野果子最是知晓。
水田边常有五味子。本地俗称 “鸡母带球”,从形状上说极为贴切,果芯被一群小果粒包裹着,像老母鸡身上落满了无数的小鸡,那长长的果柄恰是仰起的鸡脖子。学名“五味子”,说的是它的味道,果芯清润多汁,果粒汁稠味杂。熟透的红果子晶莹得像红宝石,在草丛里分外耀眼。大人常说,芯不能吃啊,会耳聋的。小孩哪会听啊?
三四月的旱地准备着种甘薯,该除壁草了。这常常是小孩的差事,那时倒觉得是件乐事。不怕刺的话,野草莓,可以大把大把地摘,酸甜适宜,吃到牙齿嚼不动酸菜为止。现在吃的城里草莓,总觉得除了个大,味道其实不地道。其中有一种矮个子的,结的果子又红又大,像个小圆盆扣在枝头。我们叫它“蛇红泡”,胆小的不敢吃,说是蛇常吃过。据说,鲁迅笔下“覆盆子”指的就它了。
胡颓子也喜欢长在旱地边。我们称它为“奇胡”。它的果子没有熟透,青绿色的,外有银鳞,千万不能动它,不能入口的,苦涩得让你舌根麻木。熟透的小黄果,椭圆的,像小指尖一样。偶尔吃一点别有风味,入口一咬,浓汁滑出,酸在嘴里甜在舌根。大果核是要吐出的,纺锤形的,真正吃到肚子里的还真是没什么东西。不过,还是不少人喜欢它。“阿姑阿姑,爬树采奇胡,摔一倒啊,屁股糊赤土。”这顺口溜,溜的就这类人。
路边的盐肤木,成串的果子一旦铺上一层粉粉白白,就禁不住抓一把放在嘴里,舔了又舔。那果实不能嚼,要干干净净地吐掉,留在嘴里的是酸涩咸甜。有人亲眼见,猴子腌萝卜。一层盐肤木的果一层偷来的萝卜,埋在地下。听时,惊愕,而后微笑。原来,我只是那个年代的某只食不厌精的猴子。
真正有分量的野果子是山柿子。当它开出风扇形一样的小花时,不会有人太在意。顶多就是摘一两个,去除果蒂,用根山芒萁穿起,“呼”地吹口气,看着精致的小风车转啊转。一到了秋后,小伙伴们的眼球就开始寻寻觅觅了。山柿树的叶子变黄了,山柿子的果子也黄了。小的如大拇指,大的可比鸭蛋。小的藏在谷堆里,等它血红了,果蒂直接摘下就可入口了。大的最好去皮,晒成干,当成干粮甜点。当然,这个过程,最好每天放在掌心揉一揉,直至每粒黑实得铺上浅浅的白灰。
我八岁整才入学,野惯的人,校门是关不住的。何况当时的小学就一溜土疙瘩平房,根本没有校门。为一点吃的不去上课,冠冕堂皇。入秋以后,最好是下过一阵小霜,好多的野果就粉墨登场了。
我的小学在溪边,八九月是枯水期,可以跳跃着过一条小溪。明着是走近路,其实心里挂念的是溪边的赤楠。我们叫“街道籽”,单这名字,就让从没进城的野孩子浮想联翩了。这植物,现在街上卖的蓝莓,得认它本家。赤楠的果子,临溪的常是成串地长,而且肉厚多汁,简直可以吃个半饱。这是山上的石斑木的果粒所不能比的,即便味道还有形状相近,乃至吃完满嘴全牙的黑糊糊相似。那个石斑木的果粒——“虎眼珠”,说白了就只一层不能下咽的皮。现在偶尔也吃些蓝莓,常说不出它比赤楠果好在哪里。
溪边,常是一些藤蔓缠绕着我们的眼神。它就在我们常戏水的小水潭边。一大帮的孩子早早就盯上它了,只是大家彼此都不声张。它的学名叫“木通”,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都叫它“爆个”,也有人叫它“八月爆”。从紫色的小花看到成型,从青绿的果子等到浅紫,盼望着早一点开口爆裂,然后坐享其成,一人独吞。那满腹的香甜那满嘴的润滑……结果,常是哪一天望去只剩下孤独的藤蔓,而后是一群人大声的咒骂。
初中到镇上读书,大老远的路,常是走着来回。一条石拱桥,全石砌成,名叫“万顺桥”。桥上长有两棵树:一为楠木,一为枳椇。楠木虽为高贵的树木,长着红色的长果柄和绿色的吃不得的小圆果,不过,这些都与我们无关。一到冬天,枳椇叶子黄了落了,我们的眼睛就会直直地向那棵树望去。细瘦的枝梢,一勾勾一串串,像一个个的鸡爪,又似焦急时草草完成的字词。就是它了,叫做“万字梨”的果子。树老高老大的,上树费时。大多时候,就是捡一两块石头或一大节枯枝,狠狠地向最浓密的树梢掷去,砸下多少算多少,拾一截放进嘴里,含着酥脆与酸甜继续赶路。
高中进城,我很得意的事,是坐在一位天仙妹妹的前面。今天看来,她是典型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的综合体。父亲是学校有钱的领导。有年秋天,小心地谈起山上的“车籽”,引起了她无限的神往。说好周末一同前去采摘,害我忐忑了整个星期。不知何故她不能成行,要我帮她带点解解馋,失望之余自是尽力照办。本地人称的“车籽”,是短尾越橘的果实,有些地方称它为乌饭子或火烧子。形状跟乌饭差不多,略小。果实从绿到红,由红到紫,当紫得发黑,黑得扑上白粉的时候,最是让人唾津满溢。那年,有片山林被山火烧过,那小小的灌木丛就像发疯一样缀满“车籽”。我趁割稻谷之余向父亲请了小假,装了一大袋回来。回到学校,早早放在她的抽屉里,头也不敢回,脸红红地等着下课。后来怎么样,我们从没谈起。后来分班了,后来毕业了,后来没再联系,后来听说她嫁个有不良嗜好的老公,不怎么幸福。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老婆常说,她是被一个野孩子用野果子骗到手的。我承认有那么一点儿。深秋的戴云山描绘着五彩斑斓和五味杂陈,轻易地蛊惑了年轻驿动的心。经霜的山樱桃,叶色绯红,小果子成串成串的,猩红得像火烧云。她说:小的时候常吃这个。那果实,红润剔透,他们叫它“红籽”,跟那时的她娇容相似;酸中带甜,还有一点点的辣,我们叫它“爆辣籽”,这与婚后她的性情相仿。深秋的果实饱满而丰腴,我们的故事在和风细雨中慢慢演绎。
孕初的女子常爱吃酸。这在闽南语里称“病子”。闽南歌谣的《病子歌》唱的就是这个。 “……男:君今问娘啊喽,你爱吃什么。女:爱吃树尾咸酸甜喽。男:爱吃我来去摘,嗳唷老狗的喂。……”老婆孕初钟爱的是杨梅,还说,山杨梅的味道更为地道。“早梅四月三,晚梅五月节”,有插秧始红的,有的流连到五月锄草时节。近几年山上植被茂密,杨梅树已不再稀缺。上山时,轻易能辨别出传说中不同外形的杨梅。柴梅,个小,肉硬,像个难民,实在是无从下口。白梅,色浅红,个不大,味较甜。一般的红梅,个头只有市面上卖的小半大,然而酸甜适中,更为地道。山上也有海梅,个头与市场上的相仿,就是颜色红艳,从不黑紫,味道上佳,当然,能遇上是山里人的福分。那年,老婆吃得很满足,我也很开心。因为连府添丁了。
现在,我的小孩,已经长到六七岁了。想当年我这个年龄,已经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上山了。可他呢?城里长大的他,整天面对电脑电视,连闽南话都说不大来,你告诉他这是什么果子、这是什么树,他会一眼的茫然。可能长大后的他,会学到书上很多的知识。再跟他谈起山里的果子,那舌尖上的幸福,他给你的不止茫然,可能还有不屑。他哪里知道、有时,学再多的书本知识,远不及向富饶多姿的山里多望上几眼。
责任编辑 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