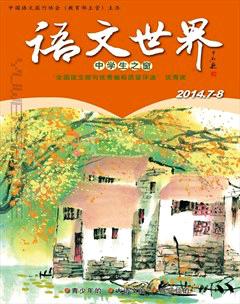大地的歌唱
鲍尔吉·原野
雏菊的披肩
雏菊是花里的孩子,秋天也不衰老,不生长皱纹和白发,它有一副鲜艳的披肩。
雏菊的披肩好像是英国都铎王朝的装束,花瓣从胸前环绕到后背,像防止吃饭洒汤的围嘴,像公鸡的颈羽。
雏菊开遍了原野,它的披肩盛满了阳光和露水。露水从花瓣流入花蕊时,雏菊再次称赞造物主给了它一副披肩。晨雾封锁了土地,好像天空的牛奶洒了,地面的乳汁比江河宽阔。雏菊闭上眼睛嗅白雾的气味,嗅不到牛奶味,只有潮湿的泥土的腥气,更不能用碗喝。阳光照下来,雏菊的花瓣像涂了显影液,慢慢从白雾里清晰,好像云里栽的花。
雏菊遍地开放,但每一朵都孤单。我看到一个孩子单独站立时,感到了他的孤单。我们愿意看到孩子和他的父母亲在一起,更愿意看到孩子的手被大人握在手里。可是谁领走雏菊呢?山峰领它走吗?小杨树领它走向河边?雏菊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小大人,它不怕孤单,它有披肩。
小时候,我把一片雏菊的花瓣揪下来,看到花朵露出巨大的豁齿。雏菊的长牙少了一颗。再揪一片,觉得它失去了下巴的胡子。摘掉一半花瓣时,它只剩一个朋克发式。揪掉了所有花瓣,雏菊全变成光头。花蕊浮肿般堆在面庞,草茎奇怪地支着这个没头发、没披肩、没有裙子的脸庞。孩子不懂得珍惜,更不懂雏菊是花里的孩子。他们摘光花瓣之后,把雏菊丢到尘土里扬长而去。孩子惯于残害花草、猫狗与玩具,从小就体会到破坏带来的成就感。一种美妙的什物,经过他们的折磨变得丑陋。正像他们长大之后要接受生活没完没了的折磨。他们不知道生活为什么要折磨他,就像花朵不知道孩子为什么残害它们。开花有什么不对吗?没有花瓣的花有什么好看?“文革”初期,遍街的景象给孩子们带来了突如其来的惊喜——单位的窗玻璃被砸碎,剃光头的人脖子上挂着牌子请罪。红色、黄色、绿色的油印传单被风刮进排水沟里。孩子们心情舒畅,可以不上学,可以看红卫兵打人。那时候孩子的父母给孩子说过关于悲悯、尊重等话题吗?没有,好多中国人的心里没这样的种子。现在的家长也会告诉孩子谦卑止暴吗?一些家长们只会说“成绩、分数、择校、大学、成功”这些话题。他们不知道,只要各方面条件俱全,当一个恶人,或者叫当一个集体无意识的恶人不是很难。
雏菊大多在2月份就开花了,花期很长,一直开到5月份,也有的在夏季开放,有的秋天还会再开一次花。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它好像跟音乐有关。雏菊跟音乐有什么关系?每次我这样问自己却答不上来。我仔细寻找线索——有哪一首歌曲的名字提到过雏菊?谁?舒曼和舒伯特写过这样的曲子吗?想不起来。我也想不起哪一首标题音乐提到过雏菊。接着,我猜想哪一个音乐家会给雏菊写一首歌或曲子。他们满怀童真,从雏菊的卑微中见到田野广袤的美,像见到穿民族服装的保加利亚姑娘跳玛祖卡舞。她们的裙子有玫瑰红的披肩。这个音乐家有可能是萧邦,他连“雨滴”都写了,为什么不写雏菊呢?这应该是一首跳跃的、晶莹的钢琴练习曲。德沃夏克也应该写雏菊。说起泥土气息的题材,我就想起德沃夏克。东欧比西欧土气,好像东欧的泥土比西欧多出好多,也厚,上面长玫瑰花、麦子、山毛榉树和雏菊。德沃夏克写的雏菊可以泡酒喝,不治病,就图酒瓶子里花瓣好看。没准也有疏肝理气之效,菊嘛。舒伯特能写出非常好听的描绘雏菊的曲子,如果他愿意写的话。描写雏菊跟描写儿童有什么不一样吗?一样的,哪块儿都一样,雏菊只比儿童多了一副披肩。我还喜欢猜想演奏这些乐曲的乐器与曲名,我觉得我适合想这些事。钢琴能表现所有题材,包括雏菊、矢车菊和杭白菊。吉他也行,但它描述的是西班牙田野的雏菊。小提琴不对味,雏菊不承载深婉的表达,它也没有沁人心脾的美。中提琴和大提琴当然也不适合,雏菊不厚重不回忆也不哲学。明亮的铜管不合适表现雏菊,它没那么坚定庞大,但圆号描绘田园时可以涵盖雏菊。木管太通透了,雏菊不是一条小溪也不是山峰上的积雪,用不上木管的通透。表现雏菊最好的样式是童声合唱,钢琴或木琴伴奏,配器加双簧管,背景加不多的竖琴旋律。孩子们唱这首(希望由舒伯特作曲)雏菊之歌时,身上戴着雏菊那样的彩色披肩。名字——给这么好的作品起名是累活——叫什么名字呢?《雏菊》《雏菊练声曲》《雏菊的早晨》?都不理想。这个事以后再说吧,不着急。
雏菊傻乎乎的单片花瓣挂在脖子上,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它的茎是细杆,带白绒。花瓣啪叽打开、一览无余的花都是傻花,对雏菊而言叫单纯,因为它是花里的儿童。你看中原的牡丹,最符合中国人的性格,搞不清它有多少层花瓣,欲舒又卷,花心纷繁似被水洇湿的手纸,可谓美得渊深。说它是国色没错,天香就有点夸张了。总之不会有人说牡丹是儿童。
雏菊在田野开放。大地涂满透明的余晖的黄颜料,雏菊赶着金黄的马车回家。夕阳的光里飘浮白色的颗粒,雏菊为此瞪大了眼睛,看微尘趴在蟋蟀的黑甲胄上,不知下落。
豆子
豆子是从娘肚子蹦出来的果实。娘胎虽好,但豆子在里边待不住了。它急躁,等不得像土豆那样被人从地里挖出来,或者像玉米那样被掰下来。豆子是谷物里的孙大圣,自己蹦到世界上。
豆子降生比人省事。人降生要住医院,当娘的哭天喊地,回肠九曲把孩儿生出来。光自己生不了,还要有医生帮着生,差一点就要命。人为此生而哭泣,豆子不哭。它天生一副圆脸,来到世上为欢乐,欢乐即在地上打滚儿,豆子乐观。
不乐观的谷物做不成豆浆、豆腐和豆皮。豆子——无论它叫大豆、黄豆、黑豆、红豆,都逗人乐。雪白的豆腐捧在人的手里颤颤巍巍,为什么会这样呢?豆子化成豆腐在乐呢。像有人不出声地笑,肩膀颤抖,和豆腐的颤动一模一样。豆子没想到它会变成整齐的方块,跟白玉没什么区别了。豆子听人在叫豆腐的时候说:松软啊、滑腻啊、可口啊、营养啊,豆子又颤悠悠笑起来,这都是谁发明的词?人类的嘴不光会吃,还会说。
豆子喜欢大地,最爱黑龙江的大地。别的地方的地只不过是地,而黑龙江的地是肥沃的土地。坐一宿火车,天亮时分窗外还是大豆的田地,大吧?广阔的大地让豆子性格豪放。把豆子放进铁锅里炒,豆子怎么样?它会跳起来骂娘。栗子、牛肉、羊肉、山药这些货,谁也没从铁锅里蹦过高,更没有“啪、啪”地叫骂。豆子不明白为什么把几百颗豆子放进铁锅里一起炒,盖上锅盖,豆子们在锅里打群架,拳打脚踢,拔枪互射,跟解放前东北土匪差不多。
豆子的婴儿床是豆荚。像浴盆一样的豆荚给每一粒豆子准备了塌陷式的光滑水床。水床的罩子当然也是浑圆的,就像人的眼皮。躺在床里,豆子看到绿色的天空,但没有云彩。豆子终于厌倦了绿色的天空,跳出来看到蓝天、白云和一帮说东北话的农民正在豆子地里打情骂俏。豆子喜欢清亮的渠水,喜欢像火柴棍一般瘦小的青草,它们头上顶一朵,有时是两朵小黄花,这太有意思了。豆子看到云彩从天边倾斜飞行,云彩如城楼一般飞向远方,豆子看见豆大的雨滴掉下来,不是一滴两滴,简直多不胜数,豆角的叶子啪啪敲鼓欢迎。雨滴到地面干什么呢?这都是豆子不明白的事。雨滴汇成溪流,灌满沟渠,豆子昏迷不醒,直至见到太阳。哪一样种子到世上不是惊心动魄?它们的童年比人类童年更有戏剧性。
在豆浆里,豆子看到了自己的白,牛奶也不过如此。它们在雪白的水里抓住其他豆子的小白手。昔日黄金化白雪,豆子们呼吸着豆的腥气。
豆子以其浑圆活泼赢得人类的好感,人用豆子为人和狗取名,以其小而圆,谓之可爱。豆的营养学定义是植物蛋白。但没人愿意起名叫蛋白,虽然蛋也白,但“豆”字更上口,与“逗”同音。豆子最逗的一件事就是当年它从娘肚子里蹦出来。
豆子的愿望是与其他豆子们走向远方,在荆棘地长成豆苗,与海边的白卵石结为邻居。豆子勇敢,在咣当咣当的列车轰鸣里,豆子和其他豆子躺在黑暗的麻袋里憧憬远方。它知道每一声“咣当”的下面都是土地,都可以生长青草、乔木与豆子的小苗。豆子后悔自己没长出一双脚,可能它从娘胎里跳出来太早了,还没来得及长出一双脚。豆子有了双脚之后情愿走到松林里,它仰望着高大的松树,在落叶松的松针里造一个房子,看松香怎样变成琥珀。豆子会走到花田旁边停下脚步,看花的露水从双鬓流到腮边,蜜蜂的轰炸机从云层俯冲下来在花朵面前嗡嗡哆嗦。豆子要去的地方太多,这些美事把它肚子撑得滚圆。豆子的豪迈让人类把它称为大豆,这可是尊称。制造白面的麦子也不过叫作小麦,豆子从小就成了大豆。